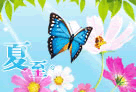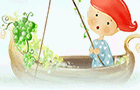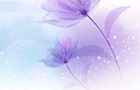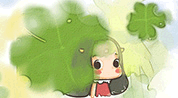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夜幕降临了,昏黄的街灯,稀疏的行人,断续的叫卖声就是旧时的东关街。儿时的我经常独自一人从大东门母亲上班的店里经过东关街回家,一路上,只要能瞥见一豆灯光,那怕它是昏黄的,微弱的,也都会立时给我以光明,温暖,振奋。 东关街,说是街道,其实并不宽,基本已经不成为街,道路的中央是石板铺陈的,多数已经松动,若是遇上一辆自行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立刻会发出吭咚吭咚的声音,你得小心翼翼地靠到街道的边上,以躲避车辆经过贱出的泥水。 东关街不算太长,满打满算,也就区区两公里,更何况还是一条直街。沿街的一些人家重新用起煤油灯,少数厚实的人家即使装了电表有了电灯也是使着只有一支光的节能泡。小小的灯泡插在一个扁园的镇流器上,有点不伦不类。到了掌灯时分,家家窗户上露出的亮光,朦胧、模糊,影影绰绰。街上是空空荡荡的,人烟稀少,偶有一两个路人走过,听那脚步声与咳嗽声,就可判断出此人的名姓来。 最初,每到傍晚,我家巷子口便挂出了万和客栈的灯笼,灯笼的亮光可以照到巷子的深处。后来,万和客栈没有了,便有了一位常年卖五香兔肉的老人,他脸上始终挂着慈祥与善良,让我感到亲切、温暖,尤其是那盏挂在挑担上的玻璃罩罩着的煤油灯,让我感到特别的温馨,因为那隐约的亮光仍旧伸向我家的巷子,让我转弯回家不觉害怕。有时我想,人生的道路上,如果一直有个这样的灯光指引该有多好,那怕这个灯光并不十分明亮。 到了我们上学的年代,鳞次栉比的商店普遍被公私合营,东关街已经没有什么店面,繁华也就此远去。记忆中,除了保留极少数半是住家半是杂货店的小门面,经营一些针头钱脑的生活必须品外,整条街只剩两间大众饭店、一个烧饼店、药店、邮政局、百货店,还的几家理发店、鞋铺。到了晚上,这些店面老式陈旧的木质柜台上,总是放着一盏罩子灯。灯罩有玻璃的,也有白纸圈成的:就是用一张纸糊成的圆筒,为的是怕灯盏被风吹灭,临时套上去的。还有简陋的油灯,灯不大,做工极其简单:一个墨水瓶,瓶盖上竖插着一个铁皮卷成的小筒,里面是一根棉花搓成的捻子。不少人家都在使用着这极其简陋方便的油灯,包括我家,虽然已经有了电灯,但是为了省钱,这种简陋的油灯居然长时间伴着我晚自习,直到下放后仍然伴着我刻苦自习。尽管它是那么普通、渺小,微不足道,发出的亮光也只能照亮几尺见方的空间,可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正是就着这煤油灯昏暗的光亮,我读了很多书,知道了世界的精彩。 下放所在的农场,四面环水,交通极其不便还没有电,除了鱼、虾便宜,就是蚊子特别的多,多得无法形容。每到傍晚时分,蚊子不请自来,黑麻麻一片、向你飞涌而来,将你团团围住,任凭你芭蕉扇如何挥舞也无济于事,蚊子叮在你膀上腿上自是岿然不动,以至,一巴掌下去至少会拍死一搓蚊子。面对排山倒海的蚊子大军,知青只能早早地拱进蚊帐。不用多久,每个人的帐子外面黑色一片,全被蚊子布满,真的好怕人。别人在蚊帐里聊天,我拱在蚊帐里看书、练字,并不时在与睡在上铺的吴晓平切磋。 为了看书,我用墨水瓶做了一个小小的油灯:用废马口铁皮卷一个管穿过瓶盖,再用几根手套线捻成一根粗芯,一盏油灯就成功了。然后我用铅丝绑在双人床的柱上,躺在蚊帐里面就着外面的微弱灯光看书。书,真是好东西,‘’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只有拼命读书,才能将一切烦恼抛弃身外。 一次,劳动过度,实在疲倦了,书看着看着,便打盹了,无意间,手将蚊帐顶了一下,蚊帐碰到了小油灯,帐子便烧了起来。上铺的吴晓平感觉下面一股热气,顿时惊醒,发现已经着火,拼命呼喊并下床帮忙灭火。此时,我也惊醒了,赶紧扯下蚊帐,用脚拼命地踩,所幸只烧了一张报纸那么大一个洞,没有酿成大火,否则,真的说不清楚了。 蚊帐有个大洞,蚊子可以长驱直入了,如何是好?新做一顶蚊帐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没有那个经济,即是有钱也没有布票。无奈,我找来几张报纸,将报披挂在被烧的洞口,然后用大头针将报纸别在蚊帐上。蚊子暂时是没有办法进来了,但是,蚊帐内的温度却更高了。好在,老书记陈立保知道了,亲自带我到农场招待所陈泽六那儿,翻出报废的破蚊帐,从中下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纱布,又请裁缝帮助接在我的蚊帐上,虽然顔色不同,但总算又有了一顶完整的单人蚊帐了。 陈立保当年在农场,是属于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行政十八级,仅次于十六级的书记刘长明、场长刘学良。然而,他丝毫没有领导者的架子。他调七大队担任支部书记以后,我开始有了自信、有了春天。他力排众议,让我帮助搞宣传,表示出对我的充分信任。他明明可以住在条件较好的大队办公室,但他坚持要与我同住一个宿舍。当时我的宿舍在大队部的河对面,房屋的条件极为简陋,他没有嫌弃我,我享受到父亲般的温暖。 他特别爱学习,一张简易的学桌案头总是摆放着很多政治书籍。然而,在这些政治书籍下面却藏着几本天天必看的农副业技术。他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读书,还规定我与他同时起身并指定我那天看完那一本书。当时唯一的照明,就是办公桌上放着的一盏罩子灯,灯罩与灯体都是用玻璃做成的,那样子与马灯一样的精巧、别致;灯体里灌着略微发黄的煤油,一根长长的白白扁扁的灯捻竖插在里面;玻璃灯罩上下小,中间鼓,大大的,与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相比,简直就是带有工艺的奢侈品了。为了让陈立保晚上看书尽量清楚一点。我每天傍晚都会认真地将灯罩灯盏擦得雪亮,同时,我还会将他的草席用清水擦一擦,将蚊帐里的蚊子驱净,放下帐门并压在席子底下。这并不是我对陈立保的刻意讨好,而是感觉到真的就是与自己的父亲住在一起。我小小年纪下放,很少享受过父爱,加上他大女儿陈和、大儿子陈平年龄都比我大,自然而然地我就将这份感情在陈立保面前尽情的表露。 准确地说,陈立保对我是比较偏爱的,可能是,看到我爱学习又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我每晚都要等他回来才睡,无论多迟,他入睡前都会与我说一会悄悄话。他说他上学的时间不长,只读过私塾,仅粗通文墨。他很重视子女的文化学习。他总是说,当多大官,挣多少钱,都不重要,多读书有本事,才最重要。他教导我说,无论如何,环境再困难,也要读书,能读到什么程度就读到什么程度,要读有用的书。照理说,他担任的是书记职务,应当整日里将空洞的政治挂在嘴上,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不着边际的政治术语。 如果说人生如远行,那么,在我蒙昩的和困惑的时日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陈书记案头的灯光。一次我回家,在县城购买了第二天早上回扬州的车票,当时,陈立保正好在县城开三级干部会,那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睡地铺,他就叫我睡在他的身边,而且对着我的耳朵,说了一些悄悄话,包括如何成家、如何立业,那都是一个父亲只能对儿子说的体已话。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四周已是一片鼾声,他突然小声对我讲,你争取入党吧。我一听这话,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知道,那时党的基层建设刚刚开始恢复。但是,这毕竟不是儿戏,我那样的出身,入党一事岂不是天方夜谭。但是陈立保是认真的。开往扬州的班车六点就发车了。天还没有亮我便起床动身了。出得门来,我从残破的窗口向睡了一晚的房间再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立在案头的,仍然是那盏油灯,灯罩没有人擦拭,蒙着灰尘,灯盏里的油,几乎熬干了,陈立保照例已经起来读书了。 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长途中,我经历过荒山的凶险和陋巷的幽曲,无论是黄昏还是深夜,只要发现远处有一豆灯光,将会想起陈立保案头的那盏煤灯,它熬了自己的生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振奋,那是我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