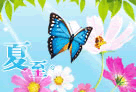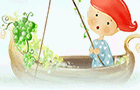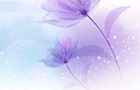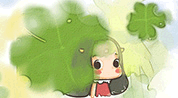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河的额上,石头以另一种方式云集 称着流水的重量 念经人点燃潮湿的火焰 水面上,彩虹成桥
皮筏成群,自上游而来 牛羊饮水,哀伤垒满山坡 塔影,在倒影里洗浴 新修的高铁,骑河穿山 谁还留心渡口的前世
风铃的喉咙里灌满方言 秋叶,被缝制成大地的婚被 被冬天迎娶回家的路上 黄昏已至,孤独的岸边 渡口,在风里摇手 像一杆芦苇,念念有词 ——《渡口》 流经平原,河流成了一个慢工状态下的裁缝,手执一把剪刀划过锦缎般的大地,裁剪出一道宽阔的、弯曲的水道,每一处渡口,就是河水裁剪累了休息的地方。 在平原,河流不像在峡谷里咆哮,它一直咧嘴微笑,沿岸古老的渡口就像两排曾经闪耀着辉煌的光芒、现在却老化、松动甚至跌落于河流视线之外的牙齿。就像人类和动物死亡上多年后,肉早已腐烂、头发早已氧化,但牙齿却能以化石的形式保存下来,成为研究古人类生活状况、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物证。对平原地区的大河而言,渡口就是陪伴过大河的化石,它们聆听过大河的丰水期的波涛里藏着的欢快;它们替河水之胃拒绝过硬邦邦的食物并让其变成了大河的营养;它们见证过大河成为贸易、交往甚至战争的通道;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激活大河,让后者变得忙碌、有活力;它们像探进岸边河水的温度计,测量着河流的忙碌程度,也像朝岸上张开的嘴巴,替河流向往来摆渡的人发出邀请或送别,……随着工业时代的桥梁架设,它们的归宿往往是静静躺在岸边的荒草中,附近的大桥就是它们的墓碑——“生看月涌大河流,死闻日落霞光曲”。让我们在河边找寻渡口,变成纯属寻找一种遗迹、一种回忆的行为,变成了对河流的另一种凭吊与追思。 渡口,激起两岸百姓的好奇、沟通、交往甚至征服的欲望,能从河流词典里嗅到水的芬芳,让隔河相望的人类产生去对岸看看的想法;渡口,是实现这些想法的基石,它们沉默着蹲在两岸,犹如秤盘,皮筏、木船、游艇等都是称量河流都的道具,它们有时能成全一个集市或村镇的梦想,有时能切断一场疲惫旅行后赶路者的睡眠。 渡口,是河流的的另一份赐礼,是长河发声的“嘴巴”或延伸的“长臂”,是对隔绝与遮蔽之地的干预,是替水向两岸百姓发出一道召唤,让他们交流、贸易、和亲,一不小心也会惹得双方隔水而战、跨河侵扰。渡口的嘴里,既能传出和平美好,也能搬弄出是非、挑逗来怒火!它们是人类以石头和土块在河流漫长、宽阔衣襟上缝制上的排扣,错落散漫地分居两岸。这排扣,扣好了,山河无恙中鸟语花香、五谷丰登,两岸百姓互递笑脸、通商结亲;扣不好的话,刀剑的寒气跨河而来、战争的烈火登上对岸的渡口,无论热冷都会导致大地生病、百姓遭殃! 渡口,这波浪奔走途中的驿站,这大河暗黑浪花迷路时的灯盏,我沿河而行时关注的一道消失的风景、一份久违的记忆! 黄河流进黑山峡后,在南北长滩附近开始一种交错状态,既完成对甘肃的长情告别,也开启对宁夏的深情投入,长滩渡,就是掩隐在峡谷中、连接两省之间的媒介。 《宁夏交通史》中,没有关于长滩渡的任何记载,我反而在《景泰县志》中找到了关于长滩渡口的记载:黄河流经景泰县110公里的水路,以长滩渡南岸为终点(北长滩往东,还有10多公里到大流水才算流出甘肃境内),长滩渡在景泰县被列为全县八个黄河渡口之一。1949年以前,这八个渡口中只有四只摆渡木船,长滩渡因为地处峡谷内,湍急的水流让这里无法使用木船;两岸百姓的交往只能用皮筏,1990年底,景泰县八个渡口中总共有三十副羊皮、胶轮内胎做的皮筏,其中北长滩就有一副。生活在长滩渡北岸、属于景泰县翠柳村的罗广智,他的祖上一直靠羊皮筏摆渡为生,他摆渡生活中的高光时刻是用四个皮筏子链起来,把一辆手扶拖拉机载运到河对岸的南长滩。罗广智的讲述,让我想起一幅拖拉机主体部位端坐在皮筏上、后车轮浸在水中渡河的画面,由于拖拉机太沉,靠人力划筏是无法渡运过去的,罗广智把拖拉机发动后,利用后轮在水中转动产生的力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惊险渡运,我想,那或许是万里黄河上唯一的一幅“拖拉机坐羊皮筏”的画面。 峡谷里的黄昏是金黄色,随着星月升空,水面上渐渐生出一缕缕淡淡的雾气,犹如画笔般给峡谷涂抹着新的色彩,紧邻岸边的山石笼罩在浓浓的湿气中,水汽沿着堤坝漫上来,像一群群醉汉在岸边游荡,穿行在乱石、树梢、屋舍和庄稼间。整个峡谷沉浸在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幸福感中,渡口、河岸、水草、村庄、庄稼以及泊在水里的铁船,都被河水深情地瞅着:这些大河的孩子。那个露宿北长滩渡的夜晚,我聆听着罗广智聊渡口的故事,因渡口衍生出的人情风俗、传奇故事仿佛蚌中的珍珠,逐渐从一层时光的大雾里露出。篝火映照着罗广智那大半辈子被河风吹得黑里透红的脸,那才是一河流水在一个大河之子脸上的底色;那双曾让划板自如地出没在水中的大手,不时挥舞着,由于常年握皮筏划板,那双手有些半握状,似乎不愿放弃攥在指缝间的、来往于长滩南北渡口间的岁月溜走。1998年,南长滩的农民李进武出资,让他的姐夫罗广智和周世成前往上游的靖远县三滩乡购买了一条闲置的铁船,运到长滩渡口,靠空中拉起来的一条索道拉船摆渡,它的到来和运营,让这片和外界几近隔绝的峡谷两岸百姓张大了嘴:我的天呀,那么大的铁墩子,竟然能凫在水上。 船是皮筏的掘墓者,船影来回在大河上时,两岸的渡口犹如一双睁大的眼睛,看着千年来皮筏渡人的河上景致消失。渡口又像是两个隔河相望的嘴,它们的感叹漂浮在河面上:这大地的舞台上,只要是人工制造的,哪里有什么永恒?就像渡口附近的那辆水车,是当地的财主胡政教出资安装的,在长滩留下了“过了五龙漩,瞅着胡政教的小铜罐”的民谚,水车和皮筏一样,最终也被抽水泵替代。皮筏像失控的风筝消失了,水车就像曾奔忙于岸边田垄间的农具钝化后躲在屋檐下的角落里,孤独地停滞在岸边。渡口依然存在,和年年岁岁照亮峡谷的明月、朝阳、星辰一样,陪伴着大河与两岸的百姓。 就像长滩渡附近的这段黄河,既是甘肃段的终结,也是宁夏段的开启,罗广智既是长滩渡最后一位筏工,也是第一个在长滩渡经营渡船的人,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旧职业,也像新栽一颗树般地给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以河为生的职业,他是两岸百姓中唯一“吃河饭”的人。 那条终结皮筏的铁船,成了来回于长滩渡的摆钟,像旧时岸边百姓的生活,在日出而摆、日落而停的工作状态中摆运了18年后,被一条体积更大、能同时摆渡6辆小汽车的海蓝色大铁船取代,长滩那古老的黄河镜面上,开始漂浮一道蓝色的音符。 随着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中年人增多,一些青年妇女也因孩子去城里上学去陪读、做饭,两岸村子变得像主人变瘦了的、有些空荡荡的袖筒,晨昏时间爬过屋脊的炊烟日渐稀少,村巷里出牧收牧时的羊群咩叫声和那股村民们感到亲切的粪骚味日渐少了,摆渡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罗广智因为年纪大不能胜任在河面上的摆渡工作,李进武像是一个长跑运动员,从罗广智手中接过划船的接力赛棒,守着铁船来回摆动在长滩的南北渡口间。如今,长滩渡就剩下李进武一个摆渡人了,“守渡人”的独角戏,他独自演了27年,成了长滩人嘴里称赞的“老把式”,大河是默默的观众。当我把“守渡人”这个词讲给村民时,他们很是诧异:“李进武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长滩,怎么一下气成了‘首都人’?” 宁夏从甘肃省分划出去时,甘肃和宁夏两省的水运部门联合确定黄河水运界限,将罗广智经营的北长滩渡口作为两省水运的分界点。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现象,南岸属于宁夏的长滩渡在这个分界点的上游,北岸属于甘肃的长滩渡却在这个分界点的下游,当地农民戏称这个现象是“甘肃人喝着宁夏的水,宁夏人坐在甘肃地盘上”。一道行政指令,在两岸百姓心中划上了一道看不见的线,好在他们自古亲如一家,这边的女儿嫁给对岸,对岸的女婿来这边干活,并不在意行政区别。 望山跑死马,隔水看穿眼。黄河水之隔和必须经过甘肃境内方能进入,让南长滩无疑成为宁夏最偏远的地方。渡口,为遮蔽和隔绝的南长滩长出了一个呼救的嘴巴、一条触摸外界的手臂。 大河是舞台,铁船和皮筏一样,唱完属于自己的戏后就退出舞台,作为观众的渡口看见一艘更大船被运来,那是由负责帮扶南长滩的大武口热电厂等单位出资打造的轮船。南长滩的村民陈建中和孟作军被村里派往沙湖景区学习摆渡、水上急救等知识,成了南长滩现代意义上的摆渡人。年轻时曾划着羊皮筏子顺河漂流、运送物资到中卫的陈建中,就此和另外三个村民轮流摆渡值班,由于这艘渡船较大且为了前往南长滩的游客能乘车进入村里,南长滩的村民将原来的渡口往上游方向挪了几公里,并在新渡口所在的岸边竖立了一个“宁夏黄河第一渡”的标志,外地来的人都将它当做长滩渡,很少有人去关注李进武在对岸守着的老渡口。 再长的故事也有句号,那个我聆听罗广智和周世成讲述长滩渡的夜晚,篝火终于灭熄,谈话终于结束。罗广智和周世成离开后,我打开头灯,整理着采访内容,回味着从夜色中缓缓走出的各种传说、真事,我从河的子民口里谛听到了河流的絮语和秘密,这些靠水生存的人,是黄河的舌头和嘴唇,制造并传播着黄河的秘密; 是黄河的花香,一直等着采访者如蜜蜂一般飞临;是黄河的耳朵,一直探听着沿河而来的消息,并将他们锻造成以河为桌布的餐食。 夜的腹地,水色如一块生铁镶嵌在两岸间,散发着暗暗的光,这些细碎如木屑般的光,在亿万年的奔流中,诞生、记录了多少故事,又遗漏、带走多少故事?让两岸贫瘠、干枯的群山褶皱间,野草般生出了多少生机与趣味,让一条大河花变得斑斓、丰富。 那一夜,我以涛声为枕,听凭夜间的流水声,像桃花穿过春天一般淌过梦境! 第二天早上,我被树边枝头上的鸟鸣声唤醒,钻出帐篷重新点燃干树枝,烧好水冲好一杯咖啡,坐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朝对岸的南长滩望去。古村身披晨光,像是一只刚睡醒的金色之猫,袅袅升起的炊烟是它的呵欠,那是从黄泥屋脊上生长出的烟蓝色庄稼,承续着一种古老生活气息中隐藏的文化,连接着滨河村庄的田园风光和峡谷造成的、当地戏称的“屁股蛋大的天”。在青藏高原的河谷,炊烟是牧民敬献给佛祖的哈达,眼前黄土高原的河谷里淡淡飘舞的炊烟,是村民向晨光中洗漱的河流送去的问候。一些早起的妇女在沿河的蔬菜地里摘菜,出牧的村民跟在从圈里急匆匆往外跑的羊群后面;也有人要出门进城去,开着三轮车往渡口这边而来,一个被朝气塞满的小村子,正打开她美丽的口腔与身体,坐迎日出,目送村民们在晨曦里的各种繁忙。后来在村子里的驻留,我也看到日落时分有村民们自田间而来,穿行在炊烟弥漫的古老街巷中,带着暮归时因劳作而带来喜悦或疲倦,走进晚饭的香味中;也有出牧的人跟在羊群后面,从村子南边的山坡上缓缓下来,偶尔还会有一两嗓子的秦腔响起在羊群的咩哞声之上。放学归来玩耍的村童交给村子的嬉闹声、村妇门依着大门呼儿唤女回家吃饭声、羊群走进巷子里的碎步声、劳作困乏的毛驴偶尔嘶叫出划过村庄上空的声音,构成一个滨河村子的黄河合奏曲。这些声音的发出者,犹如一个个轮换上台的歌唱演员。不远处,峡谷里的河涛,是台下默默伴奏的乐队。 渡船,借助河水冲力斜着头缓缓向对岸冲去,与河水互相比赛着耐性,互相成就着对方。陈建中介绍说,有时一天过不了几个人,按照村上的规定,他们每天必须给村上上交10元,而渡船费用规定单人每人2元,三轮车5元,汽车10元;单人和三轮车基本都选择去老渡口,汽车只能选择来新渡船上。渡船靠岸后,手机信息开始提醒我,到宁夏地界了,那块矗立在河边的“宁夏黄河第一村”为这种提醒做着补充。 随着南长滩村这些年打造梨花观赏盛会和炒作西夏王朝的皇室后裔逃难至此,使长滩渡声名鹊起。和以前我来这里的时间不同,这次来时,梨花盛会结束了,几天前满树的梨花,陈旧银子般地撒落一地,就像上午阳光洒在河面上发出的光一样,它们,都是大河伸出的舌尖,试图舔到的、时间的味道。 【作者简介:唐荣尧,诗人、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银川文学院院长。先后出版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散文集《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西夏史》《西夏陵》《西夏帝国传奇》《王族的背影》《西夏王朝》《神秘的西夏》等;人文地理专著《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大河远上》《一滴圣蓝》《中国新天府》《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散文集《月光下的微笑》《青草间的信仰》《沸腾的西海固》《出入山河》《小镇,时间酿造的故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