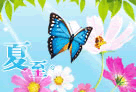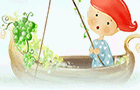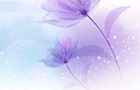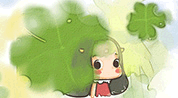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推荐语 久居繁华都市郊区的“我”,此际正为来自北方老家的高中同学李常父女在古镇设席洗尘。江南初秋的夜在三人举杯言谈中徐徐铺展,河岸边,月明灯亮,人语款款中,故土乡情,父兄姐妹,师友轶事,失意荣光,三十年人事在悠长对话中一一浮现。小说以一个美好的夜晚来回溯一代人的数十年人生,这个关于信仰与奋斗、坚持与妥协的悲悯故事,以从容洗练之笔触,勾勒出那些漂泊者的心灵样貌,在亦真亦幻中向我们呈现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和生活现实。 人语驿边桥 □ 王 咸 一 临近九月,气温一直维持在三十度左右,没有几个高温天,风一吹,脸颊上都有点秋凉的感觉了。眼看着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我心里空落落的。昨天一大早天气突然闷热起来,待在房间里有了那种被烘烤的感觉,我倒是觉得安稳了。 当时到了十点多,我起床到书房先抽了一支烟,心定以后找到两块饼干,然后开了胶囊咖啡机,放好胶囊咖啡等着出咖啡,看着外面白花花的阳光,我先拉上了书桌边上东窗户上的窗帘,然后又去拉南窗户上的窗帘。我拉上了,又拉开了。我看到前面邻居家的屋脊上停着一只巨大的黑鸟。它拢着翅膀,像披着蓑衣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屋脊上,头朝着我这边。邻居家的屋顶铺的是蓝色琉璃瓦,但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呈现一片耀眼的白光。 我愣怔了片刻,赶紧回头找相机。上海郊区这边,多的是麻雀、白头翁,还有一种比麻雀体型还小的极度灵活的鸟,我叫不出名字,飞起来像弹射一样。大一点的鸟,斑鸠、白鹭时有所见。苏州河边树林里可以看到很多黑鸟,体型比鸽子略小,好像是乌鸫。说乌鸫鸟叫声婉转,有时像笛声,有时像箫韵,我只见到它们飞,没听到过它们叫。这只白头黑身子的鸟,有贵宾犬这么大了,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偶尔有几次,夜里我看到头顶上一个硕大的黑影掠过,张开的两只翅膀仿佛有一臂长,呼扇呼扇慢慢地飞过去,似乎能听到翅膀扇动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鸟,白天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鸟。 我拿着相机又回到窗边,那只鸟还在,几乎没有挪动过位置,好像等着我拍照似的。我先是隔着窗户拍了两张,然后又慢慢地拉开窗玻璃,把相机固定在窗台上,调到200mm长焦处。等镜头稳下来,我发现这只鸟并不是很黑,而是深褐色,每只羽毛的边缘颜色就浅一些——头顶上却是秃的,裸露着红色的肉,像被拔了毛的鸡头。尖喙勾勾着,跟头顶一样肉红色,只在顶端成了白色,全身就这一点白,像戴了一个白口罩。它的头顶像一个骷髅,鼻孔裸露在外面,看不到眼睛,该是眼睛的地方黑乎乎的。我抬起头,看看它,又看看镜头里的它,我感觉它那没眼睛的头好像看到了我似的。我看了它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这可能就是常说的秃鹫了。我只是在电影电视上见到过秃鹫,在动物园里也见过,在日常生活中却从未见过。想到秃鹫锐利的眼睛可以“无细不睹”和它专吃腐尸的习性,我突然打了一个冷颤,胳膊上眼看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手机铃响起来的时候我惊了一下,回到书桌边拿起手机一看,发现是个陌生号码,但号码所在地却是我熟悉的。我犹豫着接通了电话。 “兄弟,是我,我是李常。”对方说。 “李常?”我脱口问道,但很快就后悔了,立刻弥补道,“这么稀罕啊?” “呵呵,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兄弟。”李常说。 “什么问题?”我说。 “从东方明珠到外滩怎么走啊?”李常说。 “到外滩?”我问。 “是的,从东方明珠到外滩。”李常说。 “东方明珠……这样,先找到滨江大道,然后往南走,一直走到轮渡码头,乘轮渡过去。”我说。 “好嘞。”李常说。 “轮渡很便宜,大概几块钱,还可以在黄浦江上游一游。”我说。 “好嘞,兄弟。谢谢了。”李常说。 李常挂断了电话。 我跑到窗边去看那只秃鹫,秃鹫不见了。望过屋顶,蓝天上静静地浮着一团白云。我愣愣地看着那团似乎在融化的白云,急忙又回到书桌前,拿起手机,拨通了李常的手机。 “李常,你到上海来了?”我说。 “呵呵,兄弟,是的。” 我啊了一声。 “孩子快开学了,我带他出来玩玩。”李常说。 “哦。”我说,“你找到滨江大道了吗?” “找到了,兄弟。”李常说。 李常的手机里传来乱糟糟的人声,还有隐隐的汽车喇叭声。我们没有挂断电话,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从东方明珠这里过去,大概得走一刻钟。”我说。 “好嘞,兄弟。”李常说。 “好嘞。”我说,“差不多要一刻钟。” “好嘞,我们好像快到你说的滨江大道了。”李常说。 “好的。”我说。 然后我们的电话就断了。我拿着手机看着,一直没有放下,然后又拨通了李常的手机。 “兄弟,我们已经在滨江大道了。”李常抢先说道,“这里也不错啊。” “是,那里也不错,要是下午就更好了,夕阳照过来,比外滩还有景。你们住几天啊?”我说。 “兄弟,移步换景,美不胜收啊。我们大概住上几天,还没定。”李常说。 “你们是怎么安排的?”我说。 “没有什么安排,看完外滩,我想再逛逛南京路。” “好的。”我说,“世博园要去吗,听说《清明上河图》的动画版还没撤。” “兄弟觉得值得一去吗?” “值得,带孩子去看看,很好的。”我说。 “好嘞。”李常说,“我估计今天看不成了。” “要不这样吧,你们明天上午去逛世博园,下午,我早点下班,开车带你们去朱家角玩玩。”我说。 “朱家角是什么?”李常说。 “一个古镇。”我说。 “好嘞,我听你的安排。魔都繁华之地,对我来说像迷宫,不过有兄弟的指引,我就当闲庭信步了。”李常说。 打完电话,我又去南窗边看,再也没见到那只罕见的大鸟,好像它就是监督我接听李常的电话似的。任务完成了,它就飞走了。我盯着蓝色琉璃瓦反射出的白光,脑子里也白花花一片,过了好久,我才听到周围挖掘机轰隆轰隆震天的响声。这种声音已经持续半年了,因为城市开发,周围的村子正在变为一个废墟。前面邻居已经谈好了拆迁条件,搬空了,窗户、门都砸了,变成了洞。有时候我会看到里面有人走动,可能是捡垃圾的。挖掘机在村子里奔突,但前面这幢房子一直没动,可能是担心推倒它会把我的房子震塌。因为特殊原因,我拆迁的事儿一直搁浅着,我也就一直在这儿住着。周围变空了,空气流通,即使夏天高温,只要稍微有点风,房间里也是比较凉快的。晚上有一点孤零感,不过挖掘机经常会工作到深夜,开始觉得吵,后来反而成了一种令人欣慰的“烟火气”了。 我短暂地想了一下是否要请李常到家里来住,但转眼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二 我们坐在靠河的一个座位上。天还没黑透,淡蓝色的天空中,一抹暗红色的晚霞慢慢地没进淡蓝色里。河两边店家的灯都亮了,但是在天光笼罩下还显得不够明亮。左边是高高拱起的放生桥。桥上满是人,有站着看河的,看河中的摇船慢慢划过来划过去;有倚在石栏上拍照和自拍的。过桥的人要么停一下等着拍照完毕,要么迅速跑过去。 我们能听到桥上人的说话声,听不清说什么,嗡嗡的。偶尔有人高声说一句什么,就在我们耳畔响起,在黄昏里却显得很遥远。 “这地方——真不错啊。”李常搓着双手感叹道,“有一首诗可以形容现在这个场景,怎么说?哦,是一首词,‘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皇甫松的《梦江南》是吧?” 我冲他点点头,心里放松了一些。他是第一个从老家来在我面前提到诗的人。除了家人亲戚,我很少单独接待老家来的人,都是另外几个同学接待,顺便把我叫去陪着。 “你又拽词了。哪里‘雨萧萧’?”他女儿小芸嗔他说。 “呃,难道你不觉得很美吗?”他扬起手,他的手像一把蒲扇,指着河,指着河一溜灯火的对岸,又着重指了指高高拱起的放生桥,“当然,你批评得对,没有雨,也不是梅子熟的时候,这个桥也不是驿站旁边的桥,只桥边人语对得上,我接受你的批评。但是——” 小芸噗了一下嘴,表示“服了”,说:“得,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景真是很美,但这都要感谢董叔叔啊,要不是董叔叔,我们就看不到这么美的地方了。” 老板娘把两份菜单啪嗒放到我们的桌子上就另外忙去了。李常顺手拿起一份,然后愣住了,抬起头看他的女儿:“你说什么?” 小芸说:“我说要感谢董叔叔。” 李常认真地说:“对,你说得很对,但是,这个还要说吗?” 小芸说:“当然要说了。” 李常好像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词了,像思考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一样想了一会儿说:“也对。从你的角度讲,出于礼貌,是应该说。虽然有点俗套。” 小芸争辩说:“我这不是俗套,是真心的。” 李常用一只大手掌止住女儿争辩的势头说:“我这里的俗套不是贬义词,我的意思是……” 小芸说:“叔叔,我爸小时候是不是就这么啰嗦啊?” 我笑着摇摇头,说:“这不是啰嗦,是认真。” 李常说:“好吧,我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今天可以喝酒吗?” 小芸抿着笑意看着他。 李常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情景不喝酒可惜了。” 小芸说:“你跟董叔叔这么久才见一面,当然应该喝一点。” 李常朝女儿拱了拱手。 我说:“我开车,不能喝。不过,我可以陪你喝一杯。” 李常呃了一声,身子一挺,一只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说:“哎呀,开车没办法。要不咱兄弟俩真应该喝个一醉方休。你说是不是应该啊,三十年没见了吧?” 小芸说:“喝醉就算了,还是悠着点。叔叔,你不知道他的身体——” 我犹豫了一下说:“高中毕业后好像就没见了?你的身体——” 李常面露讪笑,身子一塌,拍拍自己的右腿说:“喝坏的。”语气却是骄傲的。 我熟悉这种骄傲,在家乡男人们唯一时常表露出来的骄傲就是一场一场的大醉,因为大醉在野地里睡了一晚上,骑车掉进了河里,甚至出了车祸,都是值得骄傲的,也是别人喜欢的谈资,即使因此丢了命,也比别的原因丧命来得体面。 吃过午饭,我开车到延安西路和富民路路口等他们。他们从浦东坐地铁赶过来。我坐在车里从远处盯着幽暗的地铁出口看,我担心我会认不出他来,他在电话里给我留下的印象完全是另一个人。幽暗的地铁口,好像一个时光隧道,他们不是要从浦东赶过来,也不是从老家赶过来,是从高中时光赶过来,某一刻我会觉得这不像真的,我都有点探险的心理了,当然,如果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昨天只是一个玩笑,他根本没有来上海……即使我已经等了半天了,我也更愿意接受这个玩笑。但是当他从地铁口冒出来的一瞬间,一切显得很真实,我简直不是“认出了他”,就是“相见”了。倒不是因为他的特征太明显,一米九的个头,在哪里都很显眼,而是三十年前的神情还是隐现——不,是凸显在他变胖变粗糙的脸上,其他倒是隐现了。他比我想象的还壮硕。等我下车,站在路上迎接他的时候,他的高大身材远远地就让我有压抑感了。他走出地铁口,站在路口张望时,我没有发现——等他看到我,疾步走过来时,我才看到他走得一高一低。 他走过来停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举起右手,竖起食指说:“你真没变,还是那么潇洒。”还没等我说话,他又说,“我也没变,哈哈,除了瘸了一条腿。” “怎么回事?”我问,我尽可能离他远一点,使他低头的动作幅度小一些。以他的个头肯定能看到我微秃的头顶。我特意看了他的头发,还是像以前一样浓密,而且黑,没有看见一根白发。即使我满头黑发的时候也从没有人用“潇洒”形容过我,但是他说我“潇洒”的时候一点没有虚假,他从小就执拗地认为我会是一个大人物,我考上大学后,他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上明目张胆地写着“祝未来的歌德元旦快乐”,时间竟然没有改变我们这种隐秘的关系。 “没事。”他爽朗地说,“急了也能跑。” 我在他后面寻找他的孩子,他拉过身后的一个大姑娘,说:“这就是董叔叔。” 这个“孩子”有点大,头发染了几绺褐色,穿着高跟鞋,个头比我还高,端庄地冲我点点头,问了一声好。年纪应该有二十四五岁了。 “小芸。”李常说。 “草字头加个云。”小芸主动补充。 我笑着点点头,我真没想到“开学前的孩子”这么大了。 考虑到李常的块头,三个人我点了六个菜,其中两个冷菜,外加一个咸肉冬瓜汤。李常没说什么,只是不停地看我,好像还没认清我似的。我拿出烟来递给他,他摇了摇手说戒了。我自己点了一根抽起来。 “头发白了不少啊!”他说,“教书很辛苦吧?” 我摸了一下自己的头,他这样一说,我觉得也不用解释什么了。 小芸说:“董叔叔的白发,看上去很有学者范儿。” 李常突然伸手摸住了我的头,像摸自己的头一样,在我的头上转了两圈,然后,嘿嘿一笑。 这举动真是又陌生又熟悉,我没有觉得突兀,倒是小芸张开嘴巴,做出受惊的样子。 李常说:“真的,是真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摸他的头的。” 小芸说:“可现在不是小时候了。” 李常说:“不,现在就是小时候。”然后,他伸出舌头,左右快速地摇动着,还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神情异常的欢快。 小芸有点嫌恶地别过脸去,李常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转头对我说:“来一箱?” 小芸立刻发话说:“先要三瓶就行了,叔叔又不能喝。” 李常看了我一眼:“好好好,听你的。” 酒来了,他麻利地抢过开瓶器,打开一瓶啤酒,先给我斟满。 我抱歉地说:“我就这一杯,陪你到底了。” 他一愣,突然想起来似的,说:“对对对,你开车。”然后又给女儿倒酒。女儿用手盖住玻璃杯。 他说:“没关系,你也喝一点,你董叔叔开车没办法,你陪我喝一点。” 小芸慢慢地把手拿开了,抬眼看了他一下,笑眯眯的。 他拿过小芸的杯子,微微倾斜着,把啤酒慢慢地倒进去,啤酒泡沫一边形成一边破裂,一直倒到杯满,没有溢出一滴。 “来。”他说,“为我们三十年后的相聚干杯。” 好像斟满一杯酒的时间,天彻底暗了,河对岸的灯火明亮起来,红灯笼挂在一家家的屋檐下。河边的餐桌坐满了人,觥筹交错,言笑晏晏。河里一条光带,随波晃荡。这情景我原本是熟悉的,今天却觉得特别有梦幻感。我不是暂时用了李常的视角看着这一切,而是好像两个人搅和在了一起,还有时光的倒流,我也仿佛刚从北方到了“江南”,而且还是从小时候过来的。对着这已经很熟悉的场景,我也觉得确实“很美”了。 三 一艘游船慢慢地从放生桥下驶出来,冲开的波浪泛着光从河当中往两边扩散,不久,这波浪便到了脚边,响起哗啦哗啦的水声。 他们两个盯着游船看,一直到游船消失在远处的暗影里。 李常突然坐直了身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怎么样,兄弟,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吧?” 我小心翼翼地说:“就这样,还可以吧。” “在做什么课题?” “没做什么课题。” “嗯。”李常说,“这情景让我想起朱自清先生的文章《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 我也舒了一口气,笑说:“这条河可比不上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李常冲着小芸背诵起来,然后殷勤地问道:“还记得这篇课文吗?” 小芸说:“当然记得。你最喜欢上这篇课文了。” 李常说:“我上得怎么样?” 小芸伸出右手的大拇指。 李常哈哈大笑起来,指着我说:“让你董叔叔见笑了。” 我说:“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你不是学的历史吗?” 李常愣了一下说:“我专科学的是历史,后来自学的中文系本科。” 我说:“哦。我记得特别清楚,你当时学历史,连课本下面的注都能背下来。” 李常说:“这个倒是真的。” 小芸说:“你真的很棒,这节课上得特别好。” 李常说:“谢谢你,我干一杯。”然后又转头对我说,“虽然我知道这是恭维,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我笑着看父女两个,小芸低头弄了一下领口。她画了睫毛,画得比较浓,看上去应该有二十四五岁了。他电话里说带着孩子来玩,我还以为他的孩子是个高中生呢。 我说:“难怪我们都老了。” 李常说:“是啊,孩子都这么大了。”顿了一下,又说,“没想到三十年后,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见面。” 我说:“是啊。” 李常又对着小芸说:“这都是主的安排啊。” 小芸说:“呃?” 李常说:“难道不是吗?” 小芸说:“你们还是叙叙旧吧。” 我盯着李常看。 李常脸色忽然严肃起来,说:“你看,你董叔叔这个号码还是五年前我找周理叔叔要的,存在我的通讯簿里,一直没打过,昨天一打就通了。这难道不是有点奇妙吗?” 小芸说:“呵呵。” “还有一件奇妙的事,”李常转过头对我说,“我昨天给你打完电话,你告诉我从东方明珠那里怎么去乘摆渡船到对岸外滩,我正打听路线呢,一个人从我们旁边经过,也不看我们,说了句‘去外滩跟我来’,就一直把我们带到了船上,带到了外滩。”他又转头对小芸说,“当然,你可以理解为这是雷锋精神,我也会同意你。” …… (全文详见《江南》2023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