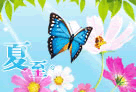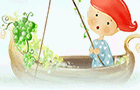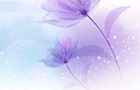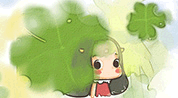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1 这里除了一座小佛塔,几乎没有固定的建筑。交错的车轮在稀疏浅草与灰白泥石中碾出的印痕,显示这是一条交通要道。远处浓淡相间的山脉层次分明,如水墨晕染。风疾速,时而匍匐时而腾飞。山石静默。山上生长着密密麻麻、永不开花的碎石。灰蒙蒙的天空,没有鸟飞过。随风而动的只有尘灰烟雾。一辆越野车刺穿苍茫的帷幕,跌跌撞撞,扭着屁股驶向荒凉深处,黄尘炸散中,隐约可见车身印着国徽,以及“流动法庭”的藏汉双语。污渍斑驳的汽车带着一股模糊的正义与肃穆的气息。 “流动法庭”在一片开阔平坦的地方停了下来。山岚在远处挽紧了手,无云的天幕扣在头顶。这里已经聚集了一些牧民,神情和远景一样苍茫,他们像山岚围住平地般围住了流动法庭。车门打开了,身穿蓝色制服的女法官措果先下车,脑后绾着一个发髻,她转身从书记员手中接过三岁的女儿,两个法警随后,最后下来的是一个浑身上下全是兜的纪录片导演——那就是我。我有一半藏族血统,会藏汉两种语言,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便利。我是以拍摄西藏野生动物为主的,得知流动法庭要在羌塘办案,处理一件家喻户晓的案子,我突发奇想,决定拍一拍人的故事。 他们打开后备箱搬行李,着手搭建流动法庭——一个白色的帐篷。女法官措果叉开腿,双手擎住缆绳与劲风拔河,好几次连帐篷带人几乎要被吹上天去。她娇小的身躯灵活且顽强,有足够的经验对付风。书记官将最后一根铁钎钉进泥石地,流动法庭生下根来,但依旧随风摇摆,时瘪时鼓,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小的、充满悲伤的灵堂。一切按法庭模式布置妥当,桌子上面铺了绣着“流动法庭”的朱红绒布,电脑、打印机、法槌等必需物品,均摆放在合适的位置。最后,女法官措果认真地在两扇假窗间挂上了国徽,她的样貌并不威严,就像初中的班主任老师正准备上普通一课。 2 事情要追溯到五月的某个上午,我们面色黑红的原告次旺那张阔嘴正贴着牦牛屁股后面的器官使劲吹气,这头名叫梅朵的白色母牦牛可能是产后抑郁,影响了乳汁分泌,一点奶水都没有。它鼓着眼睛淡然地盯着某处,似乎对生子哺乳这类琐事毫无兴趣,它甚至都没去舔一下小牛崽,也许它的心里隐藏着人类不懂的更宏伟的志向。次旺偏爱梅朵,梅朵健硕美丽,肌肉像公牛一样结实,一身白毛被次旺梳理得顺滑飘逸,整个儿看上去洁净高贵。 有一个人影走进了梅朵的瞳孔,阴影渐渐放大,很快就覆盖了梅朵的眼睛。那正是我们的单眼皮被告贡布,他把马拴在树桩上径直走进来,高大结实的身板挡住了光线。贡布轻轻友好地拍着梅朵的脑门,像是对畜生说道: “忙着催奶哪?吃一些大豆兴许更管用。” “这个办法目前是最经济实惠的。”我们面色黑红的原告次旺擦掉嘴边糊着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说完话依旧将脸埋进牛屁股,仿佛在操作一台箱式照相机,或是饶有兴味地观看西洋镜。 我们的单眼皮被告贡布看着脸部消失的次旺,神情犹豫不决,像是由于自己帮不上忙而感觉尴尬。静静的过了半晌,这才开口说道:“你卖给我的农用车电瓶有问题。” “什么有问题?”许是吹气用力过度,次旺脸上的红色部分涨得薄亮,黑色像油画的底色隐隐透显出来。 “是电瓶有问题。” “昨天你开回去时不是挺好的吗,有什么问题?” “我也说不清,总之是不好使了。”贡布底气不足,但他素有快刀斩乱麻的理智,于是横下心来说道,“我想还是退货吧,电瓶可是车的心脏啊。” 我们黑里透红的原告次旺听了之后没说话,继续在牛屁股后忙碌。贡布的要求让他感到不快,同时也感到十分为难。买卖这种事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应该出尔反尔。但是车款不是小数目,邻里乡亲,反悔交易,他也得讲点情面。可是车子卖掉时,电瓶是正常工作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没准是贡布操作不当,损坏了电瓶,好车出售,退回一台坏车,这也是他想不通的。更何况,妻子央真已经拿着卖车的钱带岳母进城看病去了,可怜的老妇人腹中胀气,排便困难,肚子憋得鼓鼓的了,偏方也不管用。 次旺鼓起腮帮子大力吹气,好像贡布并不在场。这时候距贡布使劲压价,最终带着胜利的愉悦开车回去不过二十四小时。他和妻子央真还处在无奈出售爱车的伤感之中,他们一直非常爱惜那台车,经常保养,到处擦得放光放亮,像极了他们的人生态度。人们说,假使他们有一个孩子的话,也不会超出他们对车子的用心。 贡布也没走开,等着次旺的回答。远处是灰蒙蒙的山脉。放眼看不到一顶帐篷。他骑马到这里来之前,妻子拉姆叮嘱他态度要诚恳,但不能低声下气;意志要坚决,但不要居高临下,要显得不卑不亢,要让次旺接受退货,避免让他觉得是他们损坏了电瓶,占人便宜。不过她也满脑子疑问,电瓶到底是怎么坏的?难道在他们买车时它已是濒死状态,直到行驶完十公里山路后才寿终正寝?如果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次旺卖车的行为,也许是他意识到电瓶已经有问题了,才急于脱手。但拉姆也嘱咐贡布这种话千万不能说,这会挑起矛盾,使退车的事变得更为棘手。 我们的单眼皮被告贡布正要再次张嘴快刀斩乱麻的时候,次旺的弟弟格桑和妻子白玛赶着马车唱着歌儿到来了,他们放下草料和牛奶,说了句祝母牛和小牛平安健康,就甩着鞭子唱着走了,简直像一阵风打了个旋。令贡布晕头转向的不是这阵风,想到某年的赛马节上,次旺带着辫子长长的白玛,介绍说这是他的妻子。“也许是我记错了。”贡布望着马车上那对男女的背影,为自己的糊涂沮丧。 “这样吧,你弄好电瓶,我就同意退货。”我们黑里透红的原告阔嘴次旺突然说道,“但我手上没有这么多钱,只能分两次给你。” 梅朵眨了眨眼睛。 “行,那就这么定了。”贡布点了头。 3 我们的单眼皮被告贡布在谈判的成功中没欢喜多久,就为电瓶的事伤起神来。县城太远,去一趟要耗掉大半天,买新电瓶要花一笔钱,平白无故地损失这些,莫说妻子不能接受,他自己这会儿也是越想越懊悔。为什么次旺从牛屁股后面抬起脸来那么一说,自己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呢?为什么他不咬定电瓶质量问题,坚持要无条件退货呢?他只需耐着性子站在那儿,静静地抽着烟,望望天空,瞧瞧远方,让在牛屁股后面劳动的次旺明白,要是不退货,他就会原地生根。 贡布的心思和他的生活一样的简单,他想不了多远。马慢腾腾地走着,他的身体一颠一颠,脑子里只剩下电瓶的模样。那匹棕色牝马似乎颇通人性,自作主张来到一个海子前面,刨蹄子打响鼻。单眼皮被告贡布翻身下马,伸出一双大手,捣碎天幕,掬水洗颈抹脸,经凉水刺激,脑子里的电瓶顿时与村长家的电瓶合二为一,于是精神抖擞,快马加鞭,回到妻子拉姆身边。 “我去的时候,次旺正在吹牛×。”我们的单眼皮原告贡布向妻子描述退车情况,“我说电瓶坏了,他没有觉得奇怪,好像他知道电瓶原本就有问题。” “我猜到了吧,他就是急于脱手这台烂车。”妻子拉姆身上鼓胀,脸上栗褐色,眼角和嘴边刻了几道“劳苦”,“平时顶诚实的一个人,没想到也坑起别人来了。”退车的附加条件让她心里有点不痛快,但要是次旺不同意退货,他们买台烂车,吃了哑巴亏,心里会更难受。拉姆并不懦弱,遇事不慌,通常息事宁人,一旦钻进牛角尖,也不太拉得出来。她也知道村长家有的是闲得发慌的电瓶,于是催促丈夫:“赶紧去借,快快把这事了了。”贡布刚一转身,拉姆便叫住了他,端给他一碗甜茶,顺势在他脸上啄了一嘴。拉姆胸前的果实熟透了,再熟就要掉下来烂在地上了,平时贡布总像是与地心引力争夺熟果似的,随时都想干点什么,此刻要不是急着去借电瓶,他真想躺下和拉姆腻一觉。 我们的单眼皮被告贡布带着对妻子醉醺醺的肉欲,骑着摩托车在弯弯扭扭的山路上盘绕了二十分钟到达村长家里,村长穿戴整齐,正准备骑马出门赴寿宴,听说要借电瓶,二话没说就开了仓库门。我们的单眼皮被告贡布第二天一大早开着换了电瓶的农用车,一路上车轮滚滚,轰轰烈烈,碎石欢蹦乱跳。我们的黑里透红的原告次旺这一次没有在吹牛×,而是用奶嘴给小牦牛喂奶,显然他的科学实践遭遇了失败。村长正是这个时候脑梗倒地的,来不及抢救。在寿宴席上帮忙的村民自动转到村长家,帮忙料理村长的丧事。村长的妻子哭得十分响亮,儿子扎西的眼睛一直是红的,他有点后悔没让父亲看到他结婚生子。 4 我们黑里透红的阔嘴原告次旺接了丈母娘出院。在医院待了十多天的妻子央真身上也有股药水味,但这股药味又仿佛是她高兴的情绪散发出来的,因为母亲康复了,车子不用卖掉了,回到家一眼看见它乖巧地趴在墙垛边,像一只养亲了的小动物,就忍不住伸出瘦长的双臂先抱了抱它。 “电瓶好用。”好像妻子问了什么似的,我们黑里透红的阔嘴次旺露出憨厚的笑容,“比我们自己的那个还好用。”央真一听,清瘦的脸上立刻变得严肃,她叮嘱丈夫不能这么说话,因为那听起来好像是占了贡布的便宜。接着从布袋子里拿出一些现金,说钱还剩了一些,部分医药费可以报销,尽快凑齐了还掉车款。次旺微笑点头,显示出对妻子的温情与信任。 有天下午扎西过来了,拎着青稞酒和牦牛肉,他是来向次旺讨教练习马术的。次旺曾经获得过赛马冠军,扎西想从他这里学点绝活,为了村里最美的姑娘,他要赢得比赛,父亲的突然离世,使他想到要让***妈早点抱上孙子。次旺待人诚实,教起来不遗余力。马儿来回奔驰,扬起沙尘和草屑。人和马累得气喘吁吁。喝酥油茶休息时,扎西看到农用车,很惊讶,因为这桩买卖是他牵的线。次旺就将贡布买车反悔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说他也正是考虑到扎西是中间人,才同意贡布弄好了电瓶退的车。 “我认得这电瓶。”扎西看了一眼电瓶,说道,“我说呢,原来是贡布偷了我家的电瓶。” 我们黑里透红的阔嘴原告次旺惊呆了,他半晌没有说话,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情自己也有责任,是他把贡布逼作了贼,他请扎西不要戳穿贡布偷电瓶的事,那会让他的生活变得难堪,而且贡布平时也不是这种偷摸成性的人,想必这次也是迫不得已。扎西同意假装此事没发生过,保全贡布的尊严,但是没过多久,关于贡布偷东西的事仍在村里流传开来,这就像某人出了轨,人尽皆知,唯独那个做丈夫(妻子)的蒙在鼓里。 出事是在杂货铺门口,男人们抽烟、打桌球,谈论赛马节上诞生的英雄,称赞谁的技术了不得。有人说次旺在赛场上表现得像匹种马。“不能生小马驹的种马,这可是自相矛盾的。”贡布阴阳怪气的话正巧被买茶叶的央真听到,她当场指出贡布是个偷东西的贼。贡布受不得这种抹黑与侮辱,伸手往央真的脸上打了一拳,央真倒在地上。杂货铺门口瞬间乱成一团。 此时次旺正在下村观看斗牦牛,听说妻子挨了打,打人者竟然是贡布,立刻意识到这事和电瓶有关系,当即骑了摩托车风驰电掣赶到现场,看到眼角瘀青的妻子,一句话没说,就冲上去和贡布拼命,两个男人像愤怒的牦牛,抵着头,叉开腿,都想将对方撂倒,但势均力敌,状态胶着,围观者沉浸于这场角力与争斗中。不久次旺失败倒地,贡布欲施以拳脚,央真扑了上来,被贡布猛然推开,摔倒在乱砖石上。央真的失血终止了这场战斗,次旺带妻子到县医院治疗,同时着手将贡布告上流动法庭,要求他赔偿一笔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失费。 以上就是开庭前我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5 我选了一个最佳角度架好摄像机。穿深蓝色制服的法庭工作人员坐在条桌后,措果居中,胸别着一枚国徽,她没戴帽子,风撩动她散落额前的头发。左右两侧的条桌呈“八”字状分布,分别坐着次旺夫妻和贡布夫妻。年轻的措果眉头紧锁,因为她事先知道这桩案子中,原告和被告像两头牦牛顶上了角,村里多次出面调解,但都没能和解,双方都很轴,明里暗里动员家族势力,扩大战斗阵容,做出最终决斗的准备,如果事情真发展到那一步,势必会出现两败俱伤的惨局,这会使法院失去公信力,措果本人面临良心和职业上的双重麻烦。措果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女儿几乎是在这辆“流动法庭”上长大的。开庭前,我看见措果带着女儿在不远处摘花,用草根打架拔河,在草地上打滚。 我将镜头推移到原告席,黑里透红的次旺有一张阔嘴但沉默寡言,他穿朱红色衣服与黑袍,戴着一顶宽檐卡其布帽,绳子紧紧地系在下巴底下,就算是八级台风也不能从头顶上刮走它。他的妻子央真一身五颜六色,满脑袋长时间没打散过的小辫子,凌乱蓬松的碎发像野草,她身上挂满装饰品,发带、腰带、佛珠,耳朵、脖子、手指上都是蜜蜡、玛瑙、绿松石之类的东西。她挨着丈夫坐着,眼里有股笃定与淡然。从镜头里看过去,这对夫妻脸上并没有显露出那种你死我活的刚烈性格。被告席上的那对夫妻几乎是盛装出席,贡布穿着白衣,戴着白礼帽,蓝围袍,拉姆浑身华丽的刺绣与银饰,头顶披着一条夕阳一样绚烂的头巾,边沿悬垂肩头,头巾外戴着一顶奇怪的像簸箕的空顶帽,帽子上镶着符纹。拉姆有一种有理走遍天下的自信,她一直在说话,当措果宣布开庭的时候,她也没有停下来。她的语速极快,快到我都不太明白她的藏语。这时候帐篷里也挤进了旁听的牧民,他们交谈、抽烟,说着与案件无关的话,这个流动法庭,一时间就像村里开会一样。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次旺、央真和贡布、拉姆两家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首先我要说,在这里,村民们不要再继续传谣言,更不要相信那些关于迷信的传言,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迷信。”措果大声说道,“村长死亡是偶然事件,是脑溢血,与拉姆无关,拉姆不是巫婆,她也没有能力咒死别人。原告不应再提供这些不科学的无依据的材料。” “你怎么证明拉姆不是巫婆,怎么证明村长的死与拉姆无关?”次旺不同意措果的话。 拉姆非常生气,挥舞着手大声反驳次旺的污蔑,身上饰品叮叮当当的响。她的嘴像一架机关枪,对准原告席突突突突地扫射,她说她要是有那样的本事,就会咒他立刻闭嘴。 “次旺,拉姆是不是巫婆,与本案无关。我们现在是来协调关于打人,以及赔偿医药费用的纠纷。”措果耐心地提醒,她已经习惯了流动法庭这种纷乱的场面,她知道这也是一个供牧民发泄情感的场地,很多时候原告被告双方在互相宣泄过后,梳理了自己的思绪,从而迅速达成和解,或至少有助于顺利结案。 措果给予双方充分的时间陈述、辩驳,她不打断任何人,耳朵朝向他们,眼睛从窗口望着草地上的女儿,她正在和新认识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孩子这些天似乎长大了不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措果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她打算在这个案子了结之后,带孩子去海洋公园。虽然没法去大海,但看一看从海里来的动物,对孩子也是一种弥补。 一队褐色喇嘛经过,念着经文。 最前面转着转经轮的喇嘛扭头注视着流动法庭。措果的目光落在这张轮廓分明的脸上。村里人都认得,他是大堪布多杰才仁。 原告和被告之间的争执越来越激烈——不对,应该是说拉姆一个人的辩论越来越高昂。戴簸箕帽的拉姆看上去像一条眼镜蛇吐着红芯子,既盲目又充满攻击性。她说贡布的手指被次旺打折了,腰也扭伤了,他们已经花了几千元的医药费。她现在要告次旺打人,告央真污蔑毁谤,损害了她和丈夫的个人名誉,要求公开道歉,也要经济赔偿。拉姆高分贝的吼叫震落了国徽,发出“哐当”的声响。 这引发一阵哄笑。措果弯腰捡起国徽,一边吹掉尘灰,一边用戴白手套的手擦拭,并重新挂好。镜头聚焦措果面部,我看见她眼里有晶莹的东西闪烁。她心里藏着一个悲伤的故事,故事的脉搏就在这山间里震颤,故事的余温还残留在她的指尖。 我将摄影镜头对准次旺,他的阔嘴沉默着,面色流露出对流动法庭的怀疑,并试图将这怀疑的讯息传递给妻子。事情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妻子被打的正义还未得到伸张,诉诸法庭的正义性反受到了挑战,更荒唐的是,他和妻子瞬间还成了被告。次旺不相信能从这里得到他们应得的补偿,他做好了遵循古老的传统解决纷争的准备。 我们的单眼皮被告贡布像个绅士,神色平静,似乎时刻小心地维护着一身白衣不被脏污。他们家的火力全集中在拉姆嘴里,他无须发射一粒子弹,他们便由被告转为原告,占了上风。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引起了新的混乱。 “我宣布……暂且休庭二十分钟。”措果重重地敲了一下法槌。 6 上半场以拉姆毫无中心目标的机关枪发射为主,作为被告情绪得到了充分的发泄与反驳,气势上也压倒了对方,贡布和拉姆在中场休息时显得分外轻松。下半场伊始,央真便以一种深思熟虑的从容夺取了阵地。她总结了上半场被告的种种荒唐言论,不讲道理,东拉西扯地瞎胡闹,弄掉国徽,破坏法庭的威严,将案件审判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她说贡布的手指如果骨折了,那也是打到她央真的脸上骨折的,充分证明了被告出手凶狠;如果贡布的腰扭伤了,那是因为他将央真当铅球甩出去,因此误伤了自己的腰,总言之,贡布身上的伤,恰好是他打人的佐证。 “但是,现在我们不告他打人了,”央真话锋一转,对措果说道,“我要告他偷窃。他偷东西,犯了偷窃罪。” 拉姆站起来尖声说道:“你竟敢在法庭公然进行污蔑……你能不能拿出证据来。” “他偷了村长家的电瓶。”央真不急不躁。“这电瓶现在在我家里。” “胡说!”单眼皮贡布说道,“电瓶是我找村长借的,不信你去问……” “问村长?谁能叫死人出来作证?明摆着是抵赖了。”央真摇摇头,仿佛被告开了一个拙劣的玩笑。“村长的儿子扎西早就确认了这件事,只不过为了保护你们的尊严,我们都没去揭穿。但是你们自己好像并不觉得丢脸,那就索性公开了吧。因为人干了坏事,如果不受到惩罚,就会干越来越多的坏事。” “不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没有偷电瓶,”拉姆说道,“那天下午,还是我催促丈夫去村长家借电瓶的……我不得不说,是他们心肠坏,将坏的农用车卖给我们,开回家电瓶就烂了,还不肯退货,一定要我们把电瓶弄好……我们是吃了哑巴亏……” “真是好人做不得呀,你们买了车,好好的开回去,第二天又要退货,我们念在邻里乡亲,不计较你们的出尔反尔,怎么反咬我们一口了?”次旺解开下巴上的绳子,一把抓下帽子,拍在桌子上。 “车开回来就坏了,你们隐瞒了车子的问题,做人要诚实,不能欺骗……”拉姆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开始了对次旺他们的道德批判。 “贡布,你是当事人,”措果打断了拉姆,“你从头至尾讲一讲,你当时找村长借电瓶的情形,一定要有更多的细节,包括村长当时的反应,以及他说了什么话等等。” 雪白的贡布就从次旺在牛屁股后面给母牛催奶说起了电瓶的故事,也说出了自己在返程路上的一系列心理活动: “次旺正在吹牛×……当我说电瓶坏了时,他一点都不奇怪……我不想把人想得太坏,只要车退了就好了。他好歹同意了退货,前提是得弄好电瓶……去县里买一个新电瓶不划算,我想到村长家有多余的电瓶,就回去和妻子商量,结果我俩想到一块去了。那天下午我本想和拉姆睡一觉的,但是电瓶的事情要紧,我就骑摩托车去了村长家。村长当时正在刷马毛装马鞍,准备骑着那匹油光放亮的黑马去赴寿宴,他老婆和儿子扎西都不在家。我说村长,我是来借电瓶的。村长二话没说就打开了仓库门,一没问我借去做什么用,二没问什么时候还……” “村长当时穿的什么衣,穿的什么鞋,戴的什么帽?”措果问道,“你是否记得他用了一副什么样的马鞍?” “村长当时穿的一身紫色和红色,喜气洋洋的,刮过胡子,没戴帽子,头发往后梳得溜光的,像一个嫖客……至于马鞍什么样子,我没留意。” “法官大人,一个贼在偷东西时,随便躲在什么地方也能观察到这些情况。”聪明的央真意识到措果的用意,“只等屋主人一走,贼就能顺利下手了……” “而且我们并不知道电瓶是他‘借’来的,这是对我们的欺骗。‘借’的东西是要还的,他们显然并没打算还……这要是有人说我们偷了电瓶,我们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 “你后来为什么不把借电瓶的事告诉村长的家人?”措果问道,然后扭头吩咐,“请把扎西叫来……” 有人应声,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去。 “不管怎么样,电瓶不是偷的,我可以对天发誓。”贡布拨弄着手中那串珠子,“我们的清白绝不容这么玷污,这是污蔑,这是毁谤。我们会不惜一切来维护这种清白。” 措果低声与身边的法警交谈。我的摄像机在他们之间移动,捕捉每个人细微的表情变化,拍下了很多朴实的、人性的瞬间。我观察到他们之间没有撒谎者,每个人都是真实的,像石头、像花草一样真实。 扎西很快赶到现场,身上穿着射击的服装,手里还握着一张弓,看得出他正在为赛马节夺冠苦练。 “扎西,你家是否丢了电瓶?” “是的。我在次旺家的农用车里发现了我家的电瓶。” “贡布说,电瓶是他向你父亲借的,你父亲生前是否提起过这件事?” “没有,没提过。” “有没有证据表明,贡布偷了你家电瓶?” “没有。就像他没证据证明他没偷电瓶一样。” “贡布有没有偷窃的历史?” “没听说过。” “你父亲赴寿宴那天,是不是一身紫色和红色,”措果照着前边贡布的供词描述,“……喜气洋洋的,刮过胡子。没戴帽子,头发往后梳得溜光的,像一个……咳咳……是不是这副……行头?” “是的。没错。我父亲骑马到达时,正是这副装扮。” “谢谢你,扎西。你可以走了。” “法庭不冤枉好人,也别放过坏人。赛马节见。”扎西颇具英雄气概地撩开帐篷门,消失在法庭外。 气氛松动了。似乎可以结案了。书记员的手指头在键盘上飞舞。 “法官大人,现在,我倒要告诉你一桩真正的犯罪,”贡布的声音突然冒出来,“次旺和央真是重婚,他们犯了重婚罪。” 帐篷里顿时鸦雀无声。只听见外面传来小孩子的嬉笑打闹。 “次旺真正的老婆是白玛,但白玛又是他弟弟格桑的老婆;央真是他弟弟格桑真正的老婆,但同时却又是次旺的老婆。”贡布差点把自己也绕晕了,“他们犯了重婚罪。” “重婚罪?你可真会随便扣帽子。”央真拉长了脖子说道:“我和次旺在一起更快乐,格桑和白玛在一起更幸福,我们四个人都觉得这样更好。我们不偷不抢,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碍你什么事了?你何不先把电瓶的事说清楚?别人的道德问题能洗干净你身上的脏污吗?” “我妻子说得没错。”阔嘴次旺露出羞涩的黑里透红的微笑,“我们觉得这样更合适。生活都很顺利。” “而且,白玛一直想当母亲,她和格桑在一起,才完成了这一心愿。而我对于生不生孩子无所谓,只要我和次旺两个人在一起日子过得舒心,有更多的时间到处旅游,看看不同的风景。” “听听,听听呀,都生了孩子了,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拉姆尖声说道,“他们应该马上去坐牢。” 法庭气氛瞬间到了巅峰。更多的人钻进了帐篷。人们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是犯罪,不觉惊讶与紧张,他们迫切地想知道两兄弟三兄弟共用一个老婆算不算犯罪;一个男人有两个老婆这类情况是不是犯法;一个有妇之夫和一个有夫之妇偶然睡过一觉,会不会判刑? 现场一阵骚动。人们议论纷纷。一名法警走到次旺身边,询问着什么,次旺摇了两次头。法警回到座位,对措果说了几句话,措果微笑着点了点头。 “次旺,你们去做过婚姻登记吗?”措果问。 “登记什么?” “结婚和离婚都要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没有。” “一次都没去过?” “一次都没去过。” “那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这样的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只要不犯法就行了。” “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也没有生育孩子,只能算同居关系。构不成重婚罪。”措果这话是对次旺和央真说的,更是告知贡布和拉姆,“不过,应该尽快到民政部门完成婚姻登记手续。” 案子审了大半天,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这时已经没有人提出新的控告。空气里有股疲惫与茫然。 措果朗读结案陈词。 人们仿佛进入电影赞助鸣谢的谢幕阶段,边议论边往外走,没有谁再瞧一眼大屏幕。 “……经过充分了解与协调……本庭现在作出裁决,判原告与被告双方互赔对方两千元……了结此案。”随着一声脆响,措果用法槌把自己的话钉在了桌子上。 流动法庭被拆掉了重新塞进车尾箱,车歪歪扭扭地开出很远,原告和被告的人马仍然聚在原地没散。在灰蒙蒙的云空下,风撩舞人们的衣摆、腰带和头发,撕扯着那些七嘴八舌、愤愤不平的交谈声。 “自从堪布多杰才仁打这里经过,法官大人的心思就不在法庭上了……那副眼巴巴的样子,恨不得跟着他去。” “她心里一定在等着多杰才仁回家。” “那不见得。当年她是百分之百支持丈夫出家的,她从来没有为这事哭哭啼啼。” “一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心里总归还是孤独、心酸的吧。” “我觉得,她把个人的情感问题带到了工作中,影响了审判,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判决,毫无公平公正可言。” “判决无效,我们不同意。” “要决斗,用咱们最传统的方式决斗。” 7 羌塘深处,最好的夏天,植被也是浅短稀疏,呈现营养不良的枯黄色,到九月刚染秋意,就更是早早地投降缴械了。大地上越来越了无生机,一派绵延不绝的苍茫。次旺并没有注意到自然的变化,或者说对于这季节迭换已经习以为常,心思全在与贡布的决斗约定上。不能输给贡布。妻子央真是这么说的。但是要从家里选一头牦牛去和贡布家的牦牛决斗,次旺很伤脑筋。因为贡布家那条叫多金的黑色种牦牛,是令牦牛们闻风丧胆的家伙,而且清心寡欲,对母牛十分挑剔,很难动情。它曾经是斗牛节上的冠军,一天斗赢十五头牛,自己毫发无损。次旺清楚地记得那畜生如同野牦牛一样四肢强壮,凶猛善战。它犄角粗长,比一般的牛角长出一大截,腹部长毛垂地,像穿着毛裙。它的舌头上有肉齿,舔食时发出刀一样的刮擦声,吼叫起来像猪,怒目圆睁时能让人不寒而栗。 次旺仔细盘点了自家的牦牛,他清楚每一头牦牛的性格与力量,养得体格健壮,却一个比一个温驯,缺乏争强好斗的野心,虽说偶尔也会为了维护自身尊严而与别的牛顶角较劲,但只要对方表现出顽强凶猛的势头,就会调头离开。 “一生总要有放手一搏的时候啊。”次旺在牛群中走来走去,与其说是在开导牦牛,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当别人打了你的老婆,还骑到你脖子上,公然嘲笑你,污蔑你,你就得拼了命拿出点颜色来给别人瞧瞧,是不是?”次旺停在梅朵面前,抚摸着它额前的毛发,“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要是退一步便是悬崖呢?你也会选择前进的吧。” 梅朵扫了扫尾巴,眨着清澈的大眼睛,鼻孔里重重地喷出一口气。 “你这头倔牛,有的是力气、好胜心,还有坚强的意志,”次旺捏走梅朵身上的一根小草屑,摸着它的毛发,继续说,“贡布家的多金不过是头笨牛,靠的就是一股死牛劲。你多聪明啊,一定能把多金打得落花流水……唉,可惜你是一头母牛。” “母牛怎么了?”央真端着一盆喂小牛的粥糠,头巾角一飘一飘的,“花木兰还替父亲从军作战呢。” “哪里有用母牛参加决斗的呢。”次旺说道。 “那是性别歧视。”央真把饲料盆放在小牦牛面前,“甭管是公牛还是母牛,只要是牛,都有权利参加决斗,母牛也应该有获得荣耀的机会。咱们就派梅朵上阵,前几天它不是还打败了一群公牛吗?对付多金这种只知道用角死顶的笨牛,咱们灵活的梅朵就是它的克星。” 梅朵用脑袋蹭次旺,次旺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雪山下的小矮人。他从来没怀疑过梅朵的力量,只不过因为梅朵的性别而限制了想象。他了解梅朵的性格,它不是一头只懂得交配、生育、哺乳的普通的母牛,它好战,有野心,它常常放眼辽阔的草原,注视太阳升起的地方。 央真开始给梅朵缝制专用的决斗服装。她从箱子底下翻出了珍贵的五彩丝绸和秃鹫皮,把蓝天和白云绣进去了,把希望和荣誉绣进去了,一同绣上去的,还有次旺家族的尊严。次旺受妻子影响,决定放手一搏。按照传统做法,在梅朵的食物中加入牛血、青稞酒、蝎子粉、红糖、牛奶、奶渣……甚至把梅朵单独圈起来,让它养精蓄锐。给梅朵试斗牛装的时候,英姿飒爽且斗志昂扬的梅朵美得让次旺说不出话来。他同样惊讶妻子的手艺和审美。他知道这是梅朵一生中的第一次决斗,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决斗,也许它会胜利,也许它会战死。 8 这天阳光明媚,白雪耀眼。大朵大朵的白云聚集在盆地上空,俯瞰着即将上演的决斗。我是在最后一刻打听到地址赶过来的,一个藏族小伙用摩托车载着我一路颠簸狂奔,寒风刺骨。到达时决斗双方已经到齐,彼此相距百米远,人和牛都已经摆好了阵形。雪白的梅朵温驯地挨着次旺站着,望向远方,悠闲地摆动它的绸缎长尾,华丽的披挂使它看上去雍容华贵。次旺一手拽着牛绳,一只手抚摸着梅朵的头,远看庞大的多金,心里紧张。他知道,自从定下决斗时间,贡布家里经常发出“霍尔霍尔”的磨角声,多金的牛角已经磨得锐利无比。 多金骄傲地站立,脑袋大幅度地摆动,眼睛鼓着,眼圈红红的。它裙边似的黑毛不太洁净,沾着土色和草屑,贡布并没有打扮它,除了一件简单的旧披挂,没做任何别的装饰,这暴露了贡布内心的骄傲与对对手的蔑视。妻子拉姆穿得像过节似的,一身五颜六色,与央真质朴的藏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未完,全文见《小说月报·原创版》2023年第9期) 盛可以,湖南益阳人。著有《北妹》《水乳》《野蛮生长》《女佣手记》《息壤》等十部长篇小说,以及《福地》《怀乡书》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及散文绘画作品集。作品被翻译成十五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