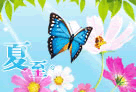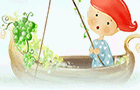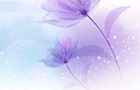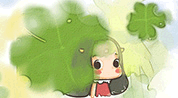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1 “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现在是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不过,我得事先对您说,如果您不对我说我们这里处于战争状态,如果您还敢袒护这个基督的敌人(我确乎相信,他是一个基督的敌人)的种种卑劣行径和他一手造成的灾祸,那么我就不再管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您就不再是,如您所说的,我的忠实的奴隶。啊,您好,您好。我看我正在吓唬您了,请坐,讲给我听。” 一八○五年七月,遐迩闻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在欢迎首位莅临晚会的达官显要瓦西里公爵时说过这番话。安娜·帕夫洛夫娜一连咳嗽几天了。正如她所说,她身罹流行性感冒(那时候,流行性感冒是个新词,只有少数人才用它)。清早由一名红衣听差在分别发出的便函中,千篇一律地写道:“伯爵(或公爵),如您意下尚无任何可取的娱乐,如今日晚上这个可怜的女病人的症候不致使您过分惧怕,则请于七时至十时间莅临寒舍,不胜雀跃。安娜·舍列尔。” “我的天,大打出手,好不激烈!”一位进来的公爵答道,对这种接见丝毫不感到困惑,他穿着绣花的宫廷礼服、长统袜子、短靴皮鞋,佩戴着多枚明星勋章,扁平的面部流露出愉快的表情。 他讲的是优雅的法语,我们的祖辈不仅借助它来说话,而且借助它来思考,他说起话来带有很平静的、长辈庇护晚辈时特有的腔调,那是上流社会和宫廷中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独具的语调。他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跟前走来,把那洒满香水的闪闪发亮的秃头凑近她,吻吻她的手,就心平气和地坐到沙发上。 “亲爱的朋友,请您首先告诉我,身体可好吗?您让我安静下来,”他说道,嗓音并没有改变,透过他那讲究礼貌的、关怀备至的腔调可以看出冷淡的、甚至是讥讽的意味。 “当你精神上遭受折磨时,身体上怎么能够健康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令有感情,又怎么能够保持宁静呢?”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我希望您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儿,好吗?” “英国公使的喜庆日子呢?今日是星期三,我要在那里露面,”公爵说道,“我女儿顺便来接我,坐一趟车子。” “我以为今天的庆祝会取消了。Je vou savoue quet out esces fete set tous ces feuxd’arti fice commen centa deveni rin Bsipides.”① “若是人家知道您有这种心愿,庆祝会就得取消的。”公爵说道,他俨然像一架上紧发条的钟,习惯地说些他不想要别人相信的话。 “Neme tourmen tezpas.Ehbienqu’a-t-ond é cid é par rapportà ladépê che de Novosil zoff?Vous savezt out.”② “怎么对您说好呢?”公爵说道,他的语调冷淡,索然无味。 “Qu’a — t — ond é cid ê ?Onad é cid ê que Buona partea brúlé sesvais seaux,et jecrois quenous somme sent rainde bruler lesno tres.”③ -------- ①法语:老实说,所有这些庆祝会、烟火,都令人厌恶极了。 ②法语:请您不要折磨我。哦,他们就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情报作出了什么决议?这一切您了若指掌。 ③法语:决定了什么?他们决定:波拿巴既已焚烧自己的战船,看来我们也要准备这样做。 瓦西里公爵向来是慢吞吞地说话,像演员口中道出旧台词那样。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虽说是年满四十,却反而充满活力和激情。 她满腔热情,使她取得了社会地位。有时她甚至没有那种希冀,但为不辜负熟悉她的人们的期望,她还是要做一个满腔热情的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流露的冷淡的微笑,虽与她的憔悴的面容不相称,但却像娇生惯养的孩童那样,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微小缺点,不过她不想,也无法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把它改正。 在有关政治行动的谈话当中,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心情激昂起来。 “咳!请您不要对我谈论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是奥地利从来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战争。它把我们出卖了。唯独俄罗斯才应当成为欧洲的救星。我们的恩人知道自己的崇高天职,他必将信守不渝。这就是我唯一的信条。我们慈善的国君当前需要发挥世界上至为伟大的职能。他十分善良,道德高尚,上帝决不会把他抛弃,他必将履行自己的天职,镇压革命的邪恶势力;他如今竟以这个杀手和恶棍作为代表人物,革命就显得愈益可怖了。遵守教规者付出了鲜血,唯独我们才应该讨还这一笔血债。我们要仰赖谁呢?我问您……散布着商业气息的英国决不懂得,也没法懂得亚历山大皇帝品性的高尚。美国拒绝让出马耳他。它想窥看,并且探寻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什么话?……什么也没说。他们不理解,也没法理解我们皇帝的奋不顾身精神,我们皇帝丝毫不贪图私利,他心中总想为全世界造福。他们许诺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们的许诺,将只是一纸空文!普鲁士已经宣布,说波拿巴无敌于天下,整个欧洲都无能同他作对……我一点也不相信哈登贝格·豪格维茨的鬼话。Cet te fameu seneu trali téprus sienne,cen’estqu’unpiège.①我只相信上帝,相信我们的贤明君主的高贵命运。他一定能够拯救欧洲!……”她忽然停了下来,对她自己的激昂情绪流露出讥讽的微笑。 “我认为,”公爵面露微笑地说道,“假如不委派我们这个可爱的温岑格罗德,而是委派您,您就会迫使普鲁士国王达成协议。您真是个能言善辩的人。给我斟点茶,好吗?” “我马上把茶端来。顺带提一句,”她又心平气和地补充说,“今天在这儿有两位饶有风趣的人士,一位是Levi comtede Mostmart,ilestal liéaux Montmoren cyparles Rohans,②法国优秀的家族之一。他是侨民之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佼佼者。另一位则是L’abbeMorio.③您认识这位聪明透顶的人士么?国王接见过他了。您知道吗?” “啊!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公爵说道,“请您告诉我,”他补充说,仿佛他方才想起某件事,显露出不经心的神态,而他所要问的事情,正是他来拜谒的主要鹄的。“L’im pérat rice- mère④想委派斗克男爵出任维也纳的头等秘书,真有其事吗?C’estun pauvre si re,cebaron,àcequ’i lparait,⑤”瓦西里公爵想把儿子安插到这个职位上,而大家却在千方百计地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为男爵谋到这个职位。 -------- ①法语:普鲁士的这种臭名昭著的中立,只是个陷阱。 ②法语:莫特马尔子爵,借助罗昂家的关系,已同蒙莫朗西结成亲戚。 ③法语:莫里约神甫。 ④法语:孀居的太后。 ⑤法语:这公爵似乎是个卑微的人。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阖上了眼睛,暗示无论是她,或是任何人都不能断定,皇太后乐意或者喜欢做什么事。 “Monsieur lebaronde Funkea é térecommand é à L’impératrice-mère par sa soeur,”①她只是用悲哀的、冷冰冰的语调说了这句话。当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到太后的名字时,她脸上顿时流露出无限忠诚和十分敬重的表情,而且混杂有每次谈话中提到她的至高无上的庇护者时就会表现出来的忧悒情绪。她说,太后陛下对斗克男爵beaucoupd’estime,②于是她的目光又笼罩着一抹愁云。 公爵不开腔了,现出了冷漠的神态。安娜·帕夫洛夫娜本身具备有廷臣和女人的那种灵活和麻利的本能,待人接物有分寸,她心想抨击公爵,因为他胆敢肆意评论那个推荐给太后的人,而同时又安慰公爵。 “Maisà propos devotre famille,”③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女儿抛头露面,进入交际界以来,faitle sdé licesde toutlemonde,Onla trou vebel le,comme Lejour.”④ -------- ①法语:斗克男爵是由太后的妹妹向太后推荐的。 ②法语:十分尊重。 ③法语:顺便谈谈您的家庭情况吧。 ④法语:她是整个上流社会的宠物。大家都认为她是娇艳的美人。 公爵深深地鞠躬,表示尊敬和谢意。 “我常有这样的想法,”安娜·帕夫洛夫娜在沉默须臾之后继续说道,她将身子凑近公爵,对他露出亲切的微笑,仿佛在表示,政界和交际界的谈话已经结束,现在可以开始推心置腹地交谈,“我常有这样的想法,生活上的幸福有时安排得不公平。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除开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不喜欢他),”她扬起眉毛,断然地插上一句话,“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这么两个顶好的孩子呢?可是您真的不珍惜他们,所以您不配有这么两个孩子。” 她于是兴奋地莞然一笑。 “Quevoulez- vous?Lafater aurait ditque jen’ai paslabos sedela pater nité,①”公爵说道。 “请不要再开玩笑。我想和您认真地谈谈。您知道,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对这些话请别介意,就在我们之间说说吧(她脸上带有忧悒的表情),大家在太后跟前议论他,都对您表示惋惜……” 公爵不回答,但她沉默地、有所暗示地望着他,等待他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一阵眉头。 “我该怎样办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为教育他们,我已竭尽为父的应尽的能事,可是到头来两个都成了desim B beciles,②伊波利特充其量是个温顺的笨蛋,阿纳托利却是个惴惴不安的笨蛋。这就是二人之间唯一的差异。”他说道,笑得比平常更不自然,更兴奋,同时嘴角边起了皱褶,特别强烈地显得出人意料地粗暴和可憎。 -------- ①法语:怎么办呢?拉法特会说我没有父爱的骨相。 ②法语:笨蛋。 “为什么像您这种人要生儿女呢?如果您不当父亲,我就无话可责备您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Jesuisvotre①忠实的奴隶,etàvous seule jepuisl’avou- er,我的孩子们—— ce sontlesen traves demonexis B tence,②这就是我的苦难。我是这样自我解释的。Quevou lezvous ?…… ”③他默不作声,用手势表示他听从残酷命运的摆布。 -------- ①法语:我是您的。 ②法语:我只能向您一人坦白承认。我的孩子们是我的生活负担。 ③法语:怎么办呢? 安娜·帕夫洛夫娜陷入了沉思。 “您从来没有想到替您那个浪子阿纳托利娶亲的事么?据说,”她开口说道,“老处女都有lamaine desmariages,①我还不觉得我自己会有这个弱点,可是我这里有一个pe ti te per sonne,②她和她父亲相处,极为不幸,她就是博尔孔斯卡娅,uneparenteanous,uneprinces se.”③尽管瓦西里公爵具备上流社会人士固有的神速的颖悟力和记忆力,但对她的见识他只是摇摇脑袋表示要加以斟酌,并没有作答。 “不,您是不是知道,这个阿纳托利每年都要花费我四万卢布。”他说道,看来无法遏制他那忧悒的心绪。他沉默了片刻。 “若是这样拖下去,五年后那会怎样呢?VoilàL’avantageà’ètrepère。④您那个公爵小姐很富有吗?” -------- ①法语:为人办婚事的癖性。 ②法语:少女。 ③法语:我们的一个亲戚,公爵小姐。 ④法语:这就是为父的益处。 “他父亲很富有,可也很吝啬。他在乡下居住。您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博尔孔斯基公爵早在已故的皇帝在位时就退休了,他的绰号是‘普鲁士国王’。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可脾气古怪,难于同他相处。Lapauvrepe ti tees tmal heureuse,commeles pierres,①她有个大哥,在当库图佐夫的副官,就在不久前娶上了丽莎·梅南,今天他要上我这儿来。” “Ecoutez,chèreAnnette,②”公爵说道,他忽然抓住交谈者的手,不知怎的使它稍微向下弯。“Arrangez- moicet teaffaire et jesui svotre③最忠诚的奴隶àtout jam ais (奴辈,commemon村长m’écritdes④在汇报中所写的)。她出身于名门望族,又很富有。这一切都是我所需要的。” 他的动作灵活、亲昵而优美,可作为他的表征,他抓起宫廷女官的手吻了吻,握着她的手摇晃了几下,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抬起眼睛向一旁望去。 “Attendez,”⑤安娜·帕夫洛夫娜思忖着说道,“我今天跟丽莎(Lafem medu jeune博尔孔斯基⑥)谈谈,也许这事情会办妥的。Cese radan svotre famille,que je fe raim onap Bprentis sage devieil lefille.⑦” -------- ①法语:这个可怜的小姐太不幸了。 ②法语:亲爱的安内特,请听我说吧。 ③法语:替我办妥这件事,我就永远是您的。 ④法语:正如我的村长所写的。 ⑤法语:请您等一等。 ⑥法语:博尔孔斯基的妻子。 ⑦我开始在您家里学习老处女的行当。 ------------------ 2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渐渐挤满了来宾。彼得堡的有名望的显贵都来赴会了,就其年龄和性情而言,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就其生活的社会而言,却是相同的。瓦西里公爵的女儿——貌美的海伦前来赴会了,她顺路来接父亲,以便一同去出席公使的庆祝大会。她佩戴花字奖章,身穿舞会的艳装。知名的、年轻的、身材矮小的叫做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Lafem me laplus séduisantede Pétersbourg①,也来赴会了;她于去冬出阁,因为怀胎,眼下不能跻身于稠人广众的交际场所,但仍旧出席小型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随同他所举荐的莫特马尔也来赴会了;此外,前来赴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父和许多旁的人。 “我还没有见过(或者:您和Matante②不相识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各位来宾说,又一本正经地把他们领到小老太太跟前,她头上束着高高的蝴蝶结,当宾客快要到来时,便从另一个房间从容平稳地走出来;安娜·帕夫洛夫娜喊出一个个来客的名字,同时把目光慢慢地从客人移到matante身上,之后她就走开了。 -------- ①彼得堡的迷人的女人。 ②法语:我的姑母。 各位来宾都向这个谁也不熟悉、谁也不感兴趣、谁也不需要的姑母行礼问安。安娜·帕夫洛夫娜显露出忧郁而庄重的神态,聆听他们的问候,心中默默地表示赞许。matante用同样的言词对每位来宾谈论到他们的情形,谈论到她自己和太后的健康情形,“谢天谢地,太后今朝有起色。”各位前来叩安的客人,为着要讲究礼节,都不表露出仓忙的神色,但都怀着履行艰巨职责之后的轻快的感觉离开老太太,整个夜晚再也不到她身边去了。 年轻的名叫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来了,她随身带着一个金线织的丝绒袋子,内中装有针线活儿。她那长有略带黑色绒毛的令人悦目的上唇,翘起来,露出了上牙,正因为这样,上唇启开时,就显得愈加好看,有时候上唇向前伸出或者搭在下唇上,就愈益好看了。她的缺点——翘嘴唇、微微张开的口——似乎已构成她的特殊的美。无论谁看见这个身体健壮、充满活力、即令是怀胎,依然一身轻快的、长相十分好看的未来的母亲,都感到无比喜悦。老年人和阴郁而烦闷的年青人,设若和她在一块待上片刻,聊聊天,就好像变得和她一个模样了。谁和她聊过天,看见她每说一句话都会露出来爽朗的微笑,看见她那雪白的、闪闪发亮的牙齿,就会感到今天受宠若惊,飘飘然。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浮现出这种想法。 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手上提着一个装有针线活的袋子,迈着急速的碎步,蹒跚地绕过桌子,愉快地弄平连衣裙,便在银质茶炊旁的长沙发上坐下来,仿佛她无论做什么事情,对她本人和她周围的人,都是一件partiedeplaisir。①“J’aiapportémonouvrage,”②她打开女用手提包,把脸转向大家说道。 “您瞧吧,Annette,neme jou ez pasun mauvais′tour,”她把脸转向女主人说话。“Vousm’avez é crit,quec’é tai tune tou tepeti tesoirée;vo ye zcom me jesui sat tifée.”③ -------- ①法语:开心事。 ②法语:我把针线活儿随身带来了。 ③法语:不要恶毒地跟我开玩笑,您写给我的信上说,你们举行一个小型的晚会。您瞧,我已经围上披肩了。 她于是两手一摊,让大伙儿瞧瞧她那件缀上花边的雅致的灰灰色的连衣裙,前胸以下系着一条宽阔的绸带。 “So yez tranquil le,Lise,vousserez tou joursla plus joli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 “Voussavez,monmarim’abandonne。”她把脸转向一位将军,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下去,“ilvase fairetuer.Ditesmoi,pour quoicet tevilai neguer re,”②她对瓦西里公爵说道,不等他回答,便转过身来和公爵的女儿——貌美的海伦谈话。 “Quel led é licieuseper sonnequecet tepetite princes se!”③瓦西里公爵轻言细语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 ①法语:丽莎,请您放心吧,您毕竟比谁都漂亮。 ②法语:您知道,我的丈夫要把我抛弃了。他要去拼死卖命。请您告诉我,这种万恶的战争是为了什么目的啊! ③法语:这个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是个多么讨人喜欢的人啊! 紧随那矮小的公爵夫人之后,有一个块头大的、略嫌肥胖的年轻人走进来了、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一付眼镜,穿着一条时髦的浅色裤子,那衣领显得又高又硬,还披上一件棕色的燕尾服。这个略嫌肥胖的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在位时一位大名鼎鼎的达官、而目前正在莫斯科奄奄一息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工作过,刚从外国深造回来,头一次在社交场合露面。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鞠个躬,表示欢迎,平素她也同样地对待自己沙龙中的下级人员。虽然这是迎接下级的礼节,但一看见皮埃尔走进门来,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就表现出惊惶不安的神情,有如看见一只不宜于此地栖身的巨大怪物似的。皮埃尔的身材确实比沙龙里其他男人魁梧些,但这种惊惶的表情只可能由于他那机灵而又畏怯、敏锐而又焦然,有别于沙龙中其他人的目光而引起的。 “C’estbienaimableàvous,monsieur Pierre,d’et revenu voi rune pauvre ma lad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道,把他带到姑母面前,惊惶失措地和她互使眼色。皮埃尔嘟哝着说了一句令人不懂的话,继续不停地用眼睛探寻着什么。他欢快地微微一笑,像对亲密的朋友那样,向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鞠躬行礼,接着便向姑母面前走去。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惊惶失措的神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皮埃尔还没有听完姑母讲太后的健康情形,便从她身旁走开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心慌意乱地用话阻拦他。 -------- ①法语:皮埃尔先生,您真是太好了,来探望一个可怜的女病人。 “您不知道莫里约神父吗?他是个很有风趣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过有关他所提出的永久和平的计划。这真是十分有趣,不过未必有可能……” “您有这样的想法?……”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本想随便聊聊,再去做些家庭主妇的活儿,但是皮埃尔竟然做出一反常态的缺少礼貌的举动。原先他没有听完对话人的话就走开了,此刻他却说些闲话来拦住需要离开他的对话人。他便垂着头,叉开他两条大腿,开始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证明,他为何认为神父的计划纯粹是幻想。 “我们以后来谈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流露出一丝微笑。 她摆脱了那个不善于生活的年轻人之后,便回过头来去干家庭主妇的活儿,继续留心地听听,仔细地看看,准备去帮助哪个谈得不带劲的地方的人。像一个纺纱作坊的老板,让劳动者就位以后,便在作坊里踱来踱去,发现纺锤停止转动,或者声音逆耳,轧轧作响、音量太大时,就赶快走去制动纺车,或者使它运转自如——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她在自己客厅里踱来踱去,不时地走到寂然无声或者谈论过多的人群面前,开口说句话或者调动他们的坐位,于是又使谈话机器从容不迫地、文质彬彬地转动起来。但是在她这样照料的当儿,依然看得出她分外担心皮埃尔。当皮埃尔走到莫特马尔周围的人们近旁听听他们谈话,后来又走到有神父发言的那一群人面前的时候,她总是怀着关切的心态注视着皮埃尔。对于在外国受过教育的皮埃尔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这次晚会,是他在俄国目睹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在这里集会,他真像个置身于玩具商店的孩童那样,看不胜看,眼花缭乱。他老是惧怕错失他能听到的深奥议论的机会。他亲眼望见在这里集会的人们都现出充满信心而又文雅的表情,他老是等待能听到特别深奥的言论。末了,他向莫里约面前走去。他心里觉得他们的谈话十分有趣,他于是停了下来,等待有机会说出自己的主见,就像年轻人那样,个个喜欢这一着。 ------------------ 3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像纺车一般动起来了。纺锤从四面匀速地转动,不断地发出轧轧的响声。只有一位痛哭流涕的、面容消瘦的、渐近老境的太太坐在姑母身旁,在这个出色的社交团体中,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除姑母而外,这个社交团体分成了三个小组。在男人占有多数的一个小组中,神父是中心人物。在另外一个小组——年轻人的小组中,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瓦西里公爵的女儿和那矮小的名叫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是中心人物,公爵夫人姿色迷人,面颊绯红,但年纪尚轻,身段显得太肥胖了。在第三个小组中,莫特马尔和安娜·帕夫洛夫娜是中心人物。 子爵心地和善、待人谦让,是个相貌漂亮的年轻人。显然,他认为自己是个名人,但因受过良好教育,是以恭顺地让他所在的社团利用他,摆布他。很明显,安娜·帕夫洛夫娜借助他来款待来客。假如你在污秽的厨房里看见一块牛肉,根本不想吃它,可是一个好管家却会把它端上餐桌,作为一道异常可口的美味;今天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做法也是这样,她先向客人献上子爵,然后献上神父,把他们作为异常精致的菜肴。莫特马尔那个小组立刻谈论到杀害昂吉安公爵的情形。子爵说,昂吉安公爵的死因,是舍己为人,而波拿巴的怨恨是有特殊原因的。 “Ah!voyons Contez- nous cela,vicomt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高兴地感到“Contez-nouscela,vicomte”这句话àlaLouisⅩⅤ②的腔调。 -------- ①法语:啊,是真的呀!子爵,请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吧。 ②法语:像路易十五。 子爵鞠躬以示顺从,彬彬有礼地微露笑容。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子爵身边让客人围成一圈,请大家听他讲故事。 “Levicomtea é téper son nel lement connudemon B seig neur, ①”安娜·帕夫洛夫娜轻言细语地对一位来客说道。 “Levicomteestunparfaitconteur,”②她对另一位来客说道。 “CommeonvoitL’hommedelabonnecompagnie,”③她对第三位来客说道。可见子爵像一盘撒上青菜的热气腾腾的干炒牛里脊,从至为优雅和对他至为有利的方面来看,他好像被端上餐桌献给这个团体的人们。 子爵想开始讲故事,脸上流露出机灵的微笑。 “请您到这边来吧,chèreHélène.”④安娜·帕夫洛夫娜对长相俊美的公爵小姐说道。公爵小姐坐在稍远的地方,她是另一个小组的中心人物。 -------- ①法语:子爵本人和那位公爵相识。 ②法语:子爵是个令人惊讶的善于讲故事的大师。 ③法语:一下子就看得出是位上流社会人士。 ④法语:亲爱的海伦。 名叫海伦的公爵小姐面带笑容,站了起来,她总是流露着她走进客厅以后就流露的美女般的微笑。她从闪到两边去让路的男人中间走过时,她那点缀着藤蔓和藓苔图案的参加舞会穿的洁白的衣裳发出刷刷的响声,雪白的肩膀、发亮的头发和钻石都熠熠生辉,她一直往前走去,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身边走去,两眼不看任何人,但对人人微露笑容,宛如她把欣赏她的身段、丰满的肩头、装束时髦的、完全袒露的胸脯和脊背之美的权利恭恭敬敬地赐予每个人,宛如她给舞蹈晚会增添了光彩。海伦太美了,从她身上看不到半点娇媚的表情,恰恰相反,好像她为自己坚信不疑的、诱惑力足以倾到一切的姿色而深感羞愧,好像她希望减少自己的美貌的诱惑力,可是无能为力。 “Quellebellepersonne!”①凡是见过她的人都这样说。当她在子爵面前坐下,照常地微微发笑,使他容光焕发的时候,仿佛有一种非凡的力量使他大为惊讶,他于是耸了耸肩,垂下了眼帘。 “Madame,jecrainspourmesmoyensdevantunpareil auditoire.”②他说道,低下头来,嘴角上露出微笑。 公爵小姐把她那裸露的肥胖的手臂的肘部靠在茶几上,她认为无须说话,面露笑容地等待着。在讲故事的当儿,她腰板挺直地坐着,时而瞧瞧轻松地搁在茶几上的肥胖而美丽的手臂,时而瞧瞧更加美丽的胸脯,弄平挂在胸前的钻石项链,她一连几次弄平连衣裙的皱褶,当故事讲到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时候,她回过头来看看安娜·帕夫洛夫娜,立时现出和宫廷女官同样的面部表情,随后便安静下来,脸上浮现出愉快的微笑。矮小的公爵夫人也紧随海伦身后从茶几旁边走过来了。 “Attendez-moi,jevaisprendremonouvrage,”③她说,“Voyons,àquoi pensez-vous?”她把脸转向伊波利特公爵说。“Apportez- moi monri di cule.”④ -------- ①法语:多么迷人的美女啊! ②法语:我的确担心在这样的听众面前会拿不出讲话的本领来。 ③法语:请等一下吧,我来拿我的活儿。 ④法语:您怎样啦?您想什么啦?请您把我的女用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微露笑容,和大家交谈的时候,她忽然调动坐位,坐下来,愉快地把衣服弄平,弄整齐。 “现在我觉得挺好,”她说,请人家开始讲故事,一面又做起活儿来了。 伊波利特公爵把女用小提包交给她,跟在她身后走过来,又把安乐椅移到靠近她的地方,便在她身旁坐下来。 这位LecharmantHippolyte①长得俨像他的美丽的妹 妹,真令人诧异,二人虽然相像,但他却十分丑陋,这就更令人诧异了。他的面部和他妹妹的一模一样,但他妹妹那乐观愉快的、洋洋自得、充满青春活力、朝夕不变的微笑和身段超人的古典美,使她容光焕发,倾城倾国;反之,哥哥的长相却显得愚昧昏庸,总是表现出十分自信和不满的神态,他身子既瘦且弱,疲软无力。眼睛、鼻子和口挤在一起,很不匀称,仿佛已变成缺乏表情的、闷闷不乐的鬼脸,而手足笨拙,总是做出生硬的姿势。 “Cen’estpasunehistoirederevenants?”②他说道。他坐在公爵夫人近侧,赶快把那单目眼镜戴在眼上,好像缺少这副工具他就无法开腔似的。 “Maisnon,moncher.”③讲故事的人大吃一惊,耸耸肩,说。 “C’estquejedétesteleshistoiresderevenants.”④伊波利特公爵用这种语调说,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先说这句话,然后才明了这句话有什么涵义。 -------- ①法语:可爱的伊波利特。 ②法语:这是不是关于鬼魂的故事? ③法语:亲爱的,根本不是。 ④法语:问题就在于,我很讨厌鬼魂的故事。 他说话时过分自信,谁也领悟不出,他说的话究竟是明智呢,抑或是愚昧之谈。他上身穿一件深绿色的燕尾服,正如他自己说的,下身穿一条cuis se denymp he ef fray é e①颜色的长裤,脚上穿一双长统袜和短靴皮鞋。 Vicomte②十分动听地讲起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则趣闻。昂吉安悄然抵达巴黎,去与m-lleGeorge③相会,在那里遇见亦曾博得这位女演员好感的波拿巴,拿破仑在和公爵见面之后,出人意料地昏倒了,他于是陷入公爵的势力范围,公爵并没有藉此机会控制他,但到后来拿破仑却把公爵杀害,以此回报公爵的宽厚。 这故事十分动听,饶有趣味,尤其是讲到这两个情敌忽然认出对方的时候,太太们心中似乎都觉得激动不安。 “Charmant,”④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一面回过头来用疑问的目光望望矮小的公爵夫人。 -------- ①法语:受惊的自然女神的内体。 ②法语:子爵。 ③法语:名叫乔治的女演员。 ④法语:好得很。 “Charmant,”矮小的公爵夫人轻言细语地说,把一根针插在针线活上,好像用以表示,这故事十分有趣,十分动听,简直妨碍她继续做针线活儿。 子爵对这沉默的称赞给予适度的评价,他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后又继续讲下去,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不时地看看使她觉得可怕的那个年轻人,这时她发觉他不知怎的在和神父一同热烈地、高声地谈话,她于是赶快跑去支援那个告急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皮埃尔竟然和那神父谈论政治均衡的事题,看来那神父对这个年轻人的纯朴的热情发生兴趣,他于是在他面前尽量发挥地那自以为是的观点。二人兴致勃勃地、真诚坦率地交谈,聆听对方的意见,这就使得安娜·帕夫洛夫娜有点扫兴了。 “臻致欧洲均势与droitdesgens①,是一种手段,”神甫说道,“只要俄国这个以野蛮残暴著称于世的强国能够大公无私地站出来领导以臻致欧洲均势为目标的同盟,那就可以拯救世界了!” -------- ①法语:民权。 “您究竟怎样去求得这种均衡呢?”皮埃尔本来要开腔,安娜·帕夫洛夫娜这时向他跟前走来,严肃地盯了皮埃尔一眼,问那个意大利人怎样才能熬得住本地的气候,意大利人的脸色忽然变了,现出一副看起来像是和女人交谈时他所惯用的假装得令人觉得委屈的谄媚的表情。 “我有幸加入你们的社会,你们的社会,尤其是妇女社会的那种优越的智慧和教育,真叫我神魂颠倒,因此我哪能事先想到气候呢。”他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不放走神父和皮埃尔,为着便于观察起见,便叫他们二人一同加入普通小组。 这时候,又有一个来宾走进了客厅。这位新客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矮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博尔孔斯基公爵个子不大,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青年,眉清目秀,面部略嫌消瘦。他整个外貌,从困倦而苦闷的目光到徐缓而匀整的脚步,和他那矮小而活泼的妻子恰恰相反,构成强烈的对照。显然,他不仅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他们都使他觉得厌烦,甚至连看看他们,听听他们谈话,他也感到索然无味。在所有这些使他厌恶的面孔中,他的俊俏的妻子的面孔似乎最使他生厌。他装出一副有损于他的美貌的丑相,把脸转过去不看她。他吻了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随后眯缝起眼睛,向众人环顾一遭。 “VousvousenroAlezpourlaguerre,monprinc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LegénéralKoutouzoff,”博尔孔斯基说道,像法国人一样,说库图佐夫一词时总把重音搁在最后一个音节上,“abiBenvoulu demoi pouraide- de- camp……”② “EtLise,votrefemme?”③ “她到农村去。” “您从我们身边夺去您的漂亮的太太应该吗?” “Andve,”④他的妻子说道,她对丈夫说话和对旁人说话都用同样娇媚的腔调,“子爵给我们讲了一则关于名叫乔治的小姐和波拿巴的故事,多么动听啊!” -------- ①法语:公爵,您准备去打仗吗? ②法语:库图佐夫将军要我做他的副官。 ③法语:您的夫人丽莎呢? ④法语:安德烈。 安德烈公爵眯缝起眼睛,把脸转过去。安德烈公爵走进客厅之后,皮埃尔便很欣悦地、友善地望着他,一刻也没有转移目光,皮埃尔向前走去一把拉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没有掉过头来看看,他蹙起额角,做出一副丑相,心里在埋怨碰到他的手臂的人,但当他望见皮埃尔含笑的面庞,他就出乎意外地流露出善意的、愉快的微笑。 “啊,原来如此!……你也跻身于稠人广众的交际场中了!”他对皮埃尔说道。 “我知道您会光临。”皮埃尔答道,“我上您那儿吃夜饭,” 他轻声地补充一句话,省得妨碍子爵讲故事,“行吗?”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含笑地说道,一面握住皮埃尔的手,向他示意,要他不必多问。他还想说些什么话,但在这当儿瓦西里公爵随同他的女儿都站起来,退席了,男士们也都站起来让路。 “我亲爱的子爵,您原谅我吧,”瓦西里公爵对法国人说,态度温和地拉住他的衣袖往椅子上按一下,不让他站起身来。 “公使举办的这个不吉利的庆祝会要夺去我的欢乐,并且把您的话儿打断了。离开您这个令人陶醉的晚会,真使我觉得难受。”他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他的女儿——名叫海伦的公爵小姐,用手轻轻地提起连衣裙褶,从椅子之间走出来,她那漂亮的脸盘上露出更愉快的微笑,当她从皮埃尔身旁走过时,皮埃尔惊喜地盯着这个美女。 “很标致。”安德烈公爵说。 “很标致。”皮埃尔说。 瓦西里公爵走过时,一把抓住皮埃尔的手,把脸转过来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请您教导教导这头狗熊吧,”他说道,“他在我家中住了一个月,我头一次在交际场所碰见他了。对一个青年来说,没有任何事物像聪明的女人们的社交团体那样迫切需要的了。” ------------------ 4 安娜·帕夫洛夫娜微微一笑,她答应接待皮埃尔,安娜知道瓦西里公爵是皮埃尔的父系的亲戚。原先和姑母坐在一起的已过中年的妇女赶快站起来,在接待室里赶上瓦西里公爵。原先她脸上假装出来的兴致已经消失了。她那仁慈的、痛哭流涕的面孔只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 “公爵,关于我的鲍里斯的事,您能对我说些什么话呢?”她在接待室追赶他时说道。(她说到鲍里斯的名字时,特别在字母“U”上加重音)。“我不能在彼得堡再呆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我能给我那可怜的男孩捎去什么信息呢?” 尽管瓦西里公爵很不高兴地、近乎失礼地听这个已过中年的妇人说话,甚至表现出急躁的情绪,但是她仍向公爵流露出亲热的、令人感动的微笑,一把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走掉。 “您只要向国王替我陈词,他就可以直接调往近卫军去了,这在您易如反掌。”她央求道。 “公爵夫人,请您相信。凡是我能办到的事,我一定为您办到,”瓦西里公爵答道,“但是向国王求情,我确有碍难。我劝您莫如借助于戈利岑公爵去晋见鲁缅采夫,这样办事更为明智。” 已过中年的妇人名叫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出身于俄国的名门望族之一,但是她现已清寒,早就步出了交际场所,失掉了往日的社交联系。她现在走来是为她的独子在近卫军中求职而斡旋。她自报姓氏,出席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其目的仅仅是要拜谒瓦西里公爵,也仅仅是为这一目的,她才聆听子爵讲故事。瓦西里公爵的一席话真使她大为震惊,她那昔日的俊俏的容貌现出了愤恨的神态,但是这神态只是继续了片刻而已,她又复微露笑意,把瓦西里公爵的手握得更紧了。 “公爵,请听我说吧,”她说道,“我从未向您求情,今后也不会向您求情,我从未向您吐露我父亲对您的深情厚谊。而今我以上帝神圣的名份向您恳求,请您为我儿子办成这件事吧,我必将把您视为行善的恩人,”她赶快补充一句话,“不,您不要气愤,就请您答应我的恳求吧。我向戈利岑求过情,他却拒之于千里之外。Soyezle bonen fant que vou sa vez ètè,”①她说道,竭力地露出微笑,但是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 ①法语:请您像以前那样行行善吧。 “爸爸,我们准会迟到啦,”呆在门边等候的公爵小姐海伦扭转她那长在极具古典美肩膀上的俊美的头部,开口说道。 但是,在上流社会上势力是一笔资本,要珍惜资本,不让它白白消耗掉。瓦西里公爵对于这一点知之甚稔,他心里想到,如果人人求他,他替人人求情,那末,在不久以后他势必无法替自己求情了,因此,他极少运用自己的势力。但是在名叫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这桩事情上,经过她再次央求之后,他心里产生一种有如遭受良心谴责的感觉。她使公爵回想起真实的往事:公爵开始供职时,他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她的父亲。除此之外,从她的作为上他可以看到,有一些妇女,尤其是母亲,她们一作出主张,非如愿以偿,决不休止,否则,她们就准备每时每刻追随不舍,剌剌不休,甚至于相骂相斗,无理取闹,她就是这类的女人。想到最后这一点,使他有点动摇了。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说道,嗓音中带有他平素表露的亲昵而又苦闷的意味,“您希望办到的事,我几乎无法办到;但是,我要办妥这件不可能办妥的事,以便向您证明我对您的爱护和对您的去世的父亲的悼念,您的儿子以后会调到近卫军中去,您依靠我吧,我向您作出了保证,您觉得满意吗?” “我亲爱的,您是个行善的恩人!您这样做,正是我所盼望的。我知道您多么慈善。” 他要走了。 “请您等一等,还有两句话要讲。Unefoispasseaux gardes……①”她踌躇起来,“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的交情甚厚,请您把鲍里斯介绍给他当副官。那时候我就放心了,那时候也就……” 瓦西里公爵脸上流露出微笑。 -------- ①法语:但当他调到近卫军中以后…… “我不能答应这件事。您不知道,自从库图佐夫被委任为总司令以来,人们一直在纠缠他。他曾亲自对我说,莫斯科的夫人们统统勾结起来了,要把她们自己的儿子送给库图佐夫当副官。” “不,您答应吧,否则,我就不放您走,我的亲爱的恩人。” “爸爸,”那个美人儿又用同样的音调重复地说了一遍,“我们准要迟到啦。” “啊,aurevoir①,再见吧,您心里明白她说的话吧?” “那末,您明天禀告国王吗?” “我一定禀告。可是我不能答应向库图佐夫求情的事。” “不,请您答应吧,请您答应吧,Basile”②,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跟在他身后说道,她脸上露出卖俏的少女的微笑,从前这大概是她惯有的一种微笑,而今它却与她那消瘦的面貌很不相称了。 显然,她已经忘记自己的年纪,她习以为常地耍出妇女向来所固有的种种手腕。但是当他一走出大门,她的脸上又浮现出原先那种冷漠的、虚伪的表情。她已经回到子爵还在继续讲故事的那个小姐那儿,又装出一副在听故事的模样,同时在等候退席离开的时机,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妥了。 “可是,近来面世的dusacredeMilan③那幕喜剧,您认为如何?”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Etlanouvel lecom é diedes peu plesde Gêneset de Lucques,qui vien nent pré senter leursvoeuxà M.Buonapar te,M,Buonaparteas sissurun Trone,ete xaucant lesvoeux desnations!Adorable!Non,maisc’estàen devenirfol le!Ondi rait,que lem ondeen tieraper dulatete.④” -------- ①法语:再见。 ②法语:瓦西里。 ③法语:《米兰的加冕典礼》。 ④法语:还有一幕新喜剧哩:热那亚和卢加各族民众向波拿巴先生表达自己的意愿。波拿巴先生坐在宝座上,居然满足了各族民众的愿望。呵!太美妙了!这真会令人疯狂。好像了不起似的,全世界都神魂颠倒了。 安德烈公爵直盯着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脸,发出了一阵冷笑。 “DieumeLadonne,gareàquilatouche,”他说道(这是波拿巴在加冕时说的话),“Onditqu’ilaététrèsbeauenprononcantcesporoles,①”他补充说,又用意大利语把这句话重说一遍,“Diomiladona,guaiachilatocca.” “J’espéreenfin,”安娜·帕夫洛夫娜继续说下去,“quecaaétélagoutted’eauqui fera deborder lever re.Lessou Bverain sne peuvent plus supporter cethomme,quime na ce tout.”② “Lessouverains?JeneparlepasdelaRuisie,”子爵彬彬有礼地,但却绝望地说道,“Les souve rains,madame! Qu’ontilsfaitpourLouisⅩⅤⅡ,pour lareine,pour ma dame Elisabeth? Rien,”他兴奋地继续说下去,“Etcroyez-moi,ils subis sent lap uni tion pour leur tra hison dela causedes Bourbons.Lessou ve rains?I lsen voient desam bas Bsadeurs complimenterl’us ur pateur③.” -------- ①法语:上帝赐予我王冠,谁触到王冠,谁就会遭殃。据说,他说这句话时,派头十足。 ②法语:他已恶贯满盈,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我希望这是他的最后一桩罪行,各国国王再也不能容忍这个极尽威胁之能事的恶魔了。 ③法语:各国国王吗?我不是说俄国的情形。各国国王呀!他们为路易十七、为皇后、为伊丽莎白做了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做。请你们相信我吧,他们因背叛波旁王朝的事业而遭受惩处。各国国王吗?他们还派遣大使去恭贺窃取王位的寇贼哩。 他鄙薄地叹了一口气,又变换了姿势。伊波利特戴上单目眼镜久久地望着子爵,他听到这些话时,忽然向那矮小的公爵夫人转过身去,向她要来一根针,便用针在桌子上描绘孔德徽章,指给她看。他意味深长地向她讲解这种徽章,好像矮小的公爵夫人请求他解释似的。 “Batondegueules,engrêlédegueulesd’azuz— maison Condé,”①他说道。 公爵夫人微露笑容听着。 “如果波拿巴再保留一年王位,”子爵把开了头的话题儿继续讲下去,他讲话时带着那种神态,有如某人在一件他最熟悉的事情上不聆听他人的话,只注意自己的思路,一个劲儿说下去!“事情就越拖越久,以致不可收拾。阴谋诡计、横行霸道、放逐、死刑将会永远把法国这个社会,我所指的是法国上流社会,毁灭掉,到那时……” 他耸耸肩,两手一摊。皮埃尔本想说句什么话,子爵的话使他觉得有趣,但是窥伺他的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话打断了。 “亚历山大皇帝宣称,”她怀有一谈起皇室就会流露的忧郁心情说,“他让法国人自己选择政体形式,我深信,毫无疑义,只要解脱篡夺王位的贼寇的羁绊,举国上下立刻会掌握在合法的国王手上。”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尽量向这个侨居的君主主义者献殷勤。 “这话不太可靠,”安德烈公爵说。“Monsieurlevicomte②想得合情合理,事情做得太过火了。不过,我想,要走回原路,实在太难了。” -------- ①法语:孔德的住宅——是用天蓝色的兽嘴缠成的兽嘴权杖的象征。 ②法语:子爵先生。 “据我所闻,”皮埃尔涨红着脸又插嘴了,“几乎全部贵族都已投靠波拿巴了。” “这是波拿巴分子说的话,”子爵不望皮埃尔一眼便说道,“眼下很难弄清法国的社会舆论。” “Bonapartel’adit,”①安德烈公爵冷冷一笑,说道。(看起来,他不喜欢子爵,没有望着子爵,不过这些话倒是针对子爵说的话。) “Jeleuraimontrélechemindelagloire,”他沉默片刻之后,又重复拿破仑的话,说道,“ilsn’enontpasvoulu,jeleuraiouvertmesan ticham bres,ils sesont pré ci pi te sen foule…… Jene sais pasa quel pointilaeu ledro it de le dire.”② “Aucun,”③子爵辩驳道,“谋杀了公爵以后,甚至连偏心的人也不认为他是英雄了。Si me me ca aétéunhé ro spourcer taines gens,”子爵把脸转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depuisl’as sasinat dudu cil yaun marty rde plus dans leciel,un héros dem oins surla ter re.”④ -------- ①法语:这是波拿巴说的话。 ②法语:“我向他们指出了一条光荣之路,他们不愿意走这条路;我给他们打开了前厅之门,他们成群地冲了进来……”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权利说这种话。 ③法语:无任何权利。 ④法语:即令他在某些人面前曾经是英雄,而在公爵被谋杀之后,天堂就多了一个受难者,尘世也就少了一个英雄。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其他人还来不及微露笑容表示赏识子爵讲的这番话,皮埃尔又兴冲冲地谈起话来了,尽管安娜·帕夫洛夫娜预感到他会开口说些有伤大雅的话,可是她已经无法遏止他了。 “处昂吉安公爵以死刑,”皮埃尔说道,“此举对国家大有必要。拿破仑不怕独自一人承担责任,我由此看出,这正是他精神伟大之所在。” “Dieu!mondieu!”①安娜·帕夫洛夫娜以低沉而可怖的嗓音说道。 “Comment,M.Pierre,voustrouvezquel’assas sina test grand eurd’a Ame ?”②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她一面微微发笑,一面把针线活儿移到她自己近旁。 “嗬!啊呀!”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Capital!”③伊波利特公爵说了一句英国话,他用手掌敲打着膝头。子爵只是耸耸肩膀。 -------- ①法语:天哪,我的天哪! ②法语:皮埃尔先生,您把谋杀看作是精神的伟大吗? ③英语:好得很! 皮埃尔心情激动地朝眼镜上方瞅了瞅听众。 “我之所以这样说,”他毫无顾忌地继续说下去,“是因为波旁王朝回避革命,让人民处在无政府状态,唯独拿破仑善于理解革命,制服革命,因此,为共同福利起见,他不能顾及一人之命而停步不前。” “您愿不愿意到那张桌上去?”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可是皮埃尔不回答,继续讲下去。 “不,”他愈益兴奋地说,“拿破仑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高踞于革命之上,摒除了革命的弊病,保存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公民平等呀,言论出版自由呀,仅仅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赢得了政权。” “是的,假如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不滥用政权来大肆屠杀,而把它交给合法的君王。”子爵说,“那么,我就会把他称为一位伟人。” “他不能做出这等事。人民把政权交给他,目的仅仅是要他把人民从波旁王朝之下解救出来,因此人民才把他视为一位伟人。革命是一件伟大的事业,”皮埃尔先生继续说道。他毫无顾忌地、挑战似地插进这句话,借以显示他风华正茂,想快点把话儿全部说出来。 “革命和杀死沙皇都是伟大的事业吗?……从此以后……您愿不愿意到那张桌上去?”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话重说了一遍。 “《Contratsocial》,”①子爵流露出温顺的微笑,说道。 -------- ①法语:《民约论》——卢梭著。 “我不是说杀死沙皇,而是说思想问题。” “是的,抢夺、谋杀、杀死沙皇的思想。”一个含有讥讽的嗓音又打断他的话了。 “不消说,这是万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但全部意义不止于此,其意义在于人权、摆脱偏见的束缚、公民的平等权益。 拿破仑完全保存了所有这些思想。” “自由与平等,”子爵蔑视地说,好像他终究拿定主意向这个青年证明他的一派胡言,“这都是浮夸的话,早已声名狼藉了。有谁不热爱自由与平等?我们的救世主早就鼓吹过自由平等。难道人们在革命以后变得更幸福么?恰恰相反。我们都希望自由,而拿破仑却取缔自由。” 安德烈公爵面露微笑,时而瞧瞧皮埃尔,时而瞧瞧子爵,时而瞧瞧女主人。开初,安娜·帕夫洛夫娜虽有上流社会应酬的习惯,却很害怕皮埃尔的乖戾举动。但是一当她看到,皮埃尔虽然说出一些渎神的坏话,子爵并没有大动肝火,在她相信不可能遏止这些言谈的时候,她就附和子爵,集中精力来攻击发言人了。 “Mais,moncherm-rPierr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一个大人物可以判处公爵死刑,以至未经开庭审判、毫无罪证亦可处死任何人,您对这事作何解释呢?” “我想问一问,”子爵说道,“先生对雾月十八日作何解释呢?这岂不是骗局么?C’est unes camo tage,quine res sem blenul le men tàlamani è red’agird’ungrand hom me.”②“可他杀掉了非洲的俘虏呢?”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这多么骇人啊!”她耸耸肩膀。 “C’estunroturier,voussurezbeaudire,”③伊波利特公爵说道。 -------- ①法语:可是,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 ②法语:这是欺骗手法,根本不像大人物的行为方法。 ③法语:无论您怎么说,是个暴发户。 皮埃尔先生不晓得应该向谁回答才对,他朝大伙儿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一阵微笑。他的微笑和他人难得露出笑容的样子不一样。恰恰相反,当他面露微笑的时候,那种一本正经、甚至略嫌忧愁的脸色,零时间就消失了,又露出一副幼稚、慈善、甚至有点傻气、俨如在乞求宽恕的神态。 子爵头一次和他会面,可是他心里明白,这个雅各宾党人根本不像他的谈吐那样令人生畏。大家都沉默无言了。 “你们怎么想要他马上向大家作出回答呢?”安德烈公爵说道,“而且在一个国家活动家的行为上,必须分清,什么是私人行为,什么是统帅或皇帝的行为。我认为如此而已。” “是的,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皮埃尔随着说起来,有人在帮忙,他高兴极了。 “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从拿破仑在阿尔科拉桥上的表现看来,他是一位伟人,拿破仑在雅法医院向鼠疫患者伸出援助之手,从表现看来,他是一位伟人,但是……但是他有一些别的行为,却令人难以辩解。” 显然,安德烈公爵想冲淡一下皮埃尔说的尴尬话,他欠起身来,向妻子做了个手势,打算走了。 忽然,伊波利特公爵站起身来,他以手势挽留大家,要他们坐下,于是开腔说话了: “Ah!aujourd’huionm’aracontéuneanecdote moscovite,charmante:il faut que jevousenr é ga le.Vousm’e xcusez,vi com te,ilfautque jeravconte enrus se.Autrementon ne sentirapasle sel del’his toire①” 伊波利特公爵讲起俄国话来了,那口音听来就像一个在俄国呆了一年左右的法国人讲的俄国话。大家都停顿下来,伊波利特公爵十分迫切地要求大家用心听他讲故事。 “莫斯科有个太太,unedame②,十分吝啬。她需要两名跟马车的valetsde pied③,身材要魁梧。这是她个人所好。她有unefemmedechambre④,个子也高大。她说……” 这时分,伊波利特公爵沉思起来了,显然在暗自盘算。 “她说……是的,她说:婢女(àlafemmedechambre),你穿上livrée,⑤跟在马车后面,我们一同去fairedesvisBites.⑥” -------- ①法语:嗬!今天有人给我讲了一则十分动听的莫斯科趣闻,也应该讲给你们听听,让你们分享一份乐趣。子爵,请您原谅吧,我要用俄国话来讲,要不然,趣闻就会没有趣味了。 ②法语:一个太太。 ③法语:仆人。 ④法语:一个女仆。 ⑤法语:宫廷内侍制服。 ⑥法语:拜会。 伊波利特公爵早就噗嗤一声大笑起来,这时,听众们还没有面露笑容,这一声大笑产生的印象对讲故事的人极为不利。然而,也有许多人,就中包括已过中年的太太和安娜·帕夫洛夫娜,都发出了一阵微笑。 “她坐上马车走了。忽然间起了一阵狂风。婢女丢掉了帽子,给风刮走了,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长发显得十分零乱……” 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发出了若断若续的笑声,他透过笑声说道: “上流社会都知道了……” 他讲的趣闻到此结束了。虽然不明了他为何要讲这则趣闻,为何非用俄国话讲不可,然而,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其他人都赏识伊波利特公爵在上流社会中待人周到的风格,赏识他这样高兴地结束了皮埃尔先生令人厌恶的、失礼的闹剧。在讲完趣闻之后,谈话变成了零星而琐细的闲聊。谈论到上回和下回的舞会、戏剧,并且谈论到何时何地与何人会面的事情。 ------------------ 5 客人们都向安娜·帕夫洛夫娜道谢,多亏她举行这次charmantesoirée①,开始散场了。 -------- ①法语:迷人的晚会。 皮埃尔笨手笨脚。他长得非常肥胖,身材比普通人高,肩宽背厚,一双发红的手又粗又壮。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他不熟谙进入沙龙的规矩,更不熟谙走出沙龙的规矩,很不内行,即是说,他不会在出门之前说两句十分悦耳的话。除此而外,他还颟颟顸顸。他站立起来,随手拿起一顶带有将军羽饰的三角帽,而不去拿自己的阔边帽,他手中拿着三角帽,不停地扯着帽缨,直至那个将军索回三角帽为止。不过他的善良、憨厚和谦逊的表情弥补了他那漫不经心、不熟谙进入沙龙的规矩、不擅长在沙龙中说话的缺陷。安娜·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脸来,抱有基督徒的温和态度,对他乖戾的举动表示宽恕,点点头对他说道: “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我希望再能和您见面,但是我也希望您能改变您的见解。”她说道。 当她对他说这话时,他一言未答,只是行了一鞠躬礼,又向大家微微一笑,这微笑没有说明什么涵义,大概只能表示,“意见总之是意见,可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好、多么善良的人。”所有的人随同安娜·帕夫洛夫娜,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个感想。 安德烈公爵走到接待室,他向给他披斗篷的仆人挺起肩膀,冷淡地听听他妻子和那位也走到接待室来的伊波利特公爵闲谈。伊波利特站在长得标致的身已怀胎的公爵夫人侧边,戴起单目眼镜目不转睛地直盯着她。 “安内特,您进去吧,您会伤风的,”矮小的公爵夫人一面向安娜·帕夫洛夫娜告辞,一面对她说。“C’estarrèté①,” 她放低嗓门补充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和丽莎商谈过她想要给阿纳托利和矮小的公爵夫人的小姑子说媒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我信任您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放低嗓门说道,“您给她写封信,再告诉我,comment le péreenvis Bagerala chose.Au revoir②。”她于是离开招待室。 -------- ①法语:就这样确定了。 ②法语:您父亲对这件事的看法。再会。 伊波利特公爵走到矮小的公爵夫人近旁,弯下腰来把脸凑近她,轻言细语地对她说些什么话。 两名仆人,一名是公爵夫人的仆人,他手中拿着肩巾,另一名是他的仆人,他手上提着长礼服,伫立在那里等候他们把话说完毕。他们听着他们心里不懂的法国话,那神态好像他们懂得似的,可是不想流露出他们听懂的神色。公爵夫人一如平常,笑容可掬地谈吐,听话时面露笑意。 “我非常高兴,我没有到公使那里去,”伊波利特公爵说道,“令人纳闷……晚会真美妙,是不是,真美妙?” “有人说,舞会妙极了,”公爵夫人噘起长满茸毛的小嘴唇道,“社团中美貌的女人都要在那里露面。” “不是所有的女人,因为您就不出席,不是所有女人,”伊波利特公爵说,洋洋得意地大笑,他霍地从仆人手中拿起肩巾,甚至推撞他,把肩巾披在公爵夫人身上。不知是动作不灵活还是蓄意这样做(谁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肩巾还披在她身上,他却久久地没有把手放开,俨像在拥抱那个少妇似的。 她一直微露笑容,风度优雅地避开他,转过身来望了望丈夫。安德烈公爵阖上了眼睛,他似乎十分困倦,现出昏昏欲睡的神态。 “您已准备就绪了吧?”他向妻子问道,目光却回避她。 伊波利特公爵急急忙忙地穿上他那件新款式的长过脚后跟的长礼服,有点绊脚地跑到台阶上去追赶公爵夫人,这时分,仆人搀着她坐上马车。 “Princesse,aurevoir①.”他高声喊道,他的舌头也像两腿被礼服绊住那样,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 ①法语:公爵夫人,再会。 公爵夫人撩起连衣裙,在那昏暗的马车中坐下来,她的丈夫在整理军刀,以效劳作为藉口的伊波利特公爵打扰了大家。 “先生,请让开。”伊波利特公爵妨碍安德烈公爵走过去,安德烈公爵于是冷冰冰地、满不高兴地用俄国话对他说道。 “皮埃尔,我在等候你。”安德烈公爵用那同样温柔悦耳的嗓音说道。 前导马御手开动了马车,马车车轮于是隆隆地响了起来。伊波利特公爵发出若断若续的笑声,站在门廊上等候子爵,他已答应乘车送子爵回家。 “呵,亲爱的,您这位矮小的公爵夫人十分可爱。十分可爱。简直是个法国女人。”子爵和伊波利特在马车中并排坐下来,说道。他吻了一下自己的指头尖。 伊波利特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您知不知道,您那纯真无瑕的样子真骇人,”子爵继续说下去,“我为这个可怜的丈夫——硬充是世袭领主的小军官表示遗憾。” 伊波利特又噗嗤一声笑了,透过笑声说道: “可是您说过,俄国女士抵不过法国女士。要善于应付。” 皮埃尔先行到达,他像家里人一样走进了安德烈公爵的书斋,习以为常地立刻躺在沙发上,从书架上随便拿起一本书(这是凯撒写的《见闻录》),他用臂肘支撑着身子,从书本的半中间读了起来。 “你对舍列尔小姐怎么样?她现在完全病倒了。”安德烈公爵搓搓他那洁白的小手走进书斋时说道。 皮埃尔把整个身子翻了过来。沙发给弄得轧轧作响,他把神彩奕奕的脸孔转向安德烈公爵,露出一阵微笑,又把手挥动一下。 “不,这个神父很有风趣,只是不太明白事理……依我看,永久和平有可能实现,但是我不会把这件事说得透彻……横直不是凭藉政治均衡的手段……” 显然,安德烈公爵对这些抽象的话题不发生兴趣。 “我亲爱的,你不能到处把你想说的话一股脑儿说出来,啊,怎么样,你终究拿定了什么主意?你要做一名近卫重骑兵团的士兵,还是做一名外交官?”安德烈公爵在沉默片刻之后问道。 “您可以想象,我还不知道啦。这二者我都不喜欢。” “可你要知道,总得拿定主意吧?你父亲在期望呢。” 皮埃尔从十岁起便随同做家庭教师的神父被送到国外去了,他在国外住到二十岁。当他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父亲把神父解雇了,并对这个年轻人说道:“你现在就到彼得堡去吧,观光一下,选个职务吧。我什么事情都同意。这是一封写给瓦西里公爵的信,这是给你用的钱。你把各种情况写信告诉我吧,我会在各个方面助你一臂之力。”皮埃尔选择职务选了三个月,可是一事无成。安德烈公爵也和他谈到选择职务这件事。皮埃尔揩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他必然是个共济会会员。”他说道,心里指的是他在一次晚会上见过面的那个神父。 “这全是胡言乱语,”安德烈公爵又制止他,说道:“让我们最好谈谈正经事吧。你到过骑兵近卫军没有?……” “没有,我没有去过,可是我脑海中想到一件事,要和您谈谈才好。目前这一场战争,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假如这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那我心中就会一明二白,我要头一个去服兵役。可是帮助美国和奥地利去反对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人……这就很不好了。” 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这种稚气的言谈只是耸耸肩膀而已。他做出一副对这种傻话无可回答的神态,诚然,对这种幼稚的问题,只能像安德烈公爵那样作答,真难以作出他种答案。 “设若人人只凭信念而战,那就无战争可言了。”他说。 “这就美不胜言了。”皮埃尔说道。 安德烈公爵发出了一阵苦笑。 “也许,这真是美不胜言,但是,这种情景永远不会出现……” “啊,您为什么要去作战呢?”皮埃尔问道。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应当这样做。除此而外,我去作战……”他停顿下来了,“我去作战是因为我在这里所过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不合乎我的心愿!” ------------------ 6 女人穿的连衣裙在隔壁房里发出沙沙的响声。安德烈公爵仿佛已清醒过来,把身子抖动一下,他的脸上正好流露出他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客厅里常有的那副表情。皮埃尔把他的两腿从沙发上放下去。公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穿着另一件家常穿的,但同样美观、未曾穿过的连衣裙。安德烈公爵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把一张安乐椅移到她近旁。 “我为什么常常思考,”她像平常那样说了一句德国话,就连忙坐在安乐椅上,“安内特为什么还不嫁人呢?先生们,你们都十分愚蠢,竟然不娶她为妻了。请你们原宥我吧,但是,女人有什么用场,你们却丝毫不明了哩。皮埃尔先生,您是个多么爱争论的人啊!” “我总会和您的丈夫争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作战。”皮埃尔向公爵夫人转过身来毫无拘束地(年轻男人对年轻女人交往中常有的这种拘束)说道。 公爵夫人颤抖了一下。显然,皮埃尔的话触及了她的痛处。 “咳,我说的也是同样的话啊!”她说道,“我不明了,根本不明了,为什么男人不作战就不能活下去呢?为什么我们女人什么也下想要,什么也不需要呢?呵,您就做个裁判吧。我总把一切情形说给他听:他在这里是他叔父的副官,一个顶好的职位。大家都很熟悉他,都很赏识他。近日来我在阿普拉克辛家里曾听到,有个太太问过一句话:他就是闻名的安德烈公爵吗?说真话!”她笑了起来,“他到处都受到欢迎。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当上侍从武官。您知道,国王很慈善地和他谈过话。我和安内特说过,撮合这门亲事不会有困难。您认为怎样?” 皮埃尔望了望安德烈公爵,发现他的朋友不喜欢这次谈话,便一言不答。 “您什么时候走呢?”他发问。 “哦!请您不要对我说走的事,您不要说吧!这件事我不愿意听,”公爵夫人用在客厅里和伊波利特谈话时的那种猥亵而任性的音调说道,看来,这音调用在皮埃尔仿佛是成员的家庭中很不适合,“今天当我想到要中断这一切宝贵的关系……然后呢?安德烈,你知道吗?”她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向丈夫示意,“我觉得可怕,觉得可怕啊!”她的脊背打颤,轻言细语地说。 丈夫望着她,流露出那种神态,仿佛他惊恐万状,因为他发觉,除开他和皮埃尔而外,屋中还有一个人,但是他依然现出冷淡和谦逊的表情,用疑问的音调对妻子说: “丽莎,你害怕什么?我无法理解。”他说道。 “算什么男人,男人都是利己主义者,都是,都是利己主义者啊!他自己因为要求苛刻,过分挑剔,天晓得为什么,把我抛弃了,把我一个人关在乡下。” “跟我父亲和妹妹在一起,别忘记。”安德烈公爵低声说道。 “我身边没有我的朋友们了,横直是孑然一人……他还想要我不怕哩。” 她的声调已经含有埋怨的意味,小嘴唇翘了起来,使脸庞赋有不高兴的、松鼠似的兽性的表情。她默不作声了,似乎她认为在皮埃尔面前说到她怀孕是件不体面的事,而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我还是不明白,你害怕什么。”安德烈公爵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子,慢条斯理地说道。 公爵夫人涨红了脸,失望地挥动双手。 “不,安德烈,你变得真厉害,变得真厉害……” “你的医生吩咐你早点就寝,”安德烈公爵说道,“你去睡觉好了。” 公爵夫人不发一言,突然她那长满茸毛的小嘴唇颤栗起来;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耸耸肩,从房里走过去了。 皮埃尔惊奇而稚气地借助眼镜时而望望他,时而望望公爵夫人,他身子动了一下,好像他也想站起来,但又改变了念头。 “皮埃尔先生在这儿,与我根本不相干,”矮小的公爵夫人忽然说了一句话,她那秀丽的脸上忽然现出发哭的丑相,“安德烈,我老早就想对你说:你为什么对我改变了态度呢?我对你怎么啦?你要到军队里去,你不怜悯我,为什么?” “丽莎!”安德烈公爵只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既含有乞求,又含有威胁,主要是有坚定的信心,深信她自己会懊悔自己说的话,但是她忙着把话继续说下去: “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病人或者对待儿童那样。我看得一清二楚啊。难道半年前你是这个模样吗?” “丽莎,我请您住口。”安德烈公爵愈益富于表情地说道。 在谈话的时候,皮埃尔越来越激动不安,他站了起来,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看来他不能经受住流泪的影响,自己也准备哭出声来。 “公爵夫人,请放心。这似乎是您的想象,因为我要您相信,我自己体会到……为什么……因为……不,请您原谅,外人在这儿真是多余的了……不,请您放心……再见……” 安德烈公爵抓住他的一只手,要他止步。 “皮埃尔,不,等一下。公爵夫人十分善良,她不想我失去和你消度一宵的快乐。” “不,他心中只是想到自己的事。”公爵夫人说道,忍不住流出气忿的眼泪。 “丽莎,”安德烈公爵冷漠地说道,抬高了声调,这足以表明,他的耐性到了尽头。 公爵夫人那副魅人的、令人怜悯的、畏惧的表情替代了她那漂亮脸盘上像松鼠似的忿忿不平的表情;她蹙起额角,用一双秀丽的眼睛望了望丈夫,俨像一只疾速而乏力地摇摆着下垂的尾巴的狗,脸上现出了胆怯的、表露心曲的神态。 “Mondieu,mondieu!”①公爵夫人说道,用一只手撩起连衣裙褶,向丈夫面前走去,吻了吻他的额头。 “Bonsoir,Lise.”②安德烈公爵说道,他站了起来,像在外人近旁那样恭恭敬敬地吻着她的手。 -------- ①法语: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②法语:丽莎,再会。 朋友们沉默不言。他们二人谁也不开腔。皮埃尔不时地看看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用一只小手揩揩自己的额头。 “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叹一口气说道,站立起来向门口走去。 他们走进一间重新装修得豪华而优雅的餐厅。餐厅里的样样东西,从餐巾到银质器皿、洋瓷和水晶玻璃器皿,都具有年轻夫妇家的日常用品的异常新颖的特征。晚餐半中间,安德烈公爵用臂肘支撑着身子,开始说话了,他像个心怀积愫、忽然决意全盘吐露的人那样,脸上带有神经兴奋的表情,皮埃尔从未见过他的朋友流露过这种神态。 “我的朋友,永远,永远都不要结婚;这就是我对你的忠告,在你没有说你已做完你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前,在你没有弃而不爱你所挑选的女人以前,在你还没有把她看清楚以前,你就不要结婚吧!否则,你就会铸成大错,弄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当你是个毫不中用的老头的时候再结婚吧……否则,你身上所固有的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都将会丧失。一切都将在琐碎事情上消耗殆尽。是的,是的,是的!甭这样惊奇地望着我。如果你对自己的前程有所期望,你就会处处感觉到,你的一切都已完结,都已闭塞,只有那客厅除外,在那里你要和宫廷仆役和白痴平起平坐,被视为一流……岂不就是这么回事啊!……” 他用劲地挥挥手。 皮埃尔把眼镜摘下来,他的面部变了样子,显得愈加和善了,他很惊讶地望着自己的朋友。 “我的妻子,”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是个挺好的女人。她是可以放心相处并共同追求荣誉的难能可贵的女人之一,可是,我的老天哪,只要我能不娶亲,我如今不论什么都愿意贡献出来啊!我是头一回向你一个人说出这番话的,因为我爱护你啊。” 安德烈公爵说这话时与原先不同,更不像博尔孔斯基了,那时,博尔孔斯基把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安乐椅上,把眼睛眯缝起来,透过齿缝说了几句法国话。他那冷淡的脸部由于神经兴奋的缘故每块肌肉都在颤栗着,一对眼睛里射出的生命之火在先前似乎熄灭了,现在却闪闪发亮。看来,他平常显得愈加暮气沉沉,而在兴奋时就会显得愈加生气勃勃。 “你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他继续说下去,“要知道,这是全部生活史。你说到,波拿巴和他的升迁,”他说了这句话后,虽然皮埃尔并没有说到波拿巴的事情,“你谈到波拿巴;但当波拿巴从事他的活动,一步一步地朝着他的目标前进的时候,他自由自在,除开他所追求的目标而外,他一无所有,他终于达到了目标。但是,你如若把你自己和女的捆在一起,像个带上足枷的囚犯,那你就会丧失一切自由。你的希望和力量——这一切只会成为你的累赘,使你遭受到懊悔的折磨。客厅、谗言、舞会、虚荣、微不足道的事情,这就是我无法走出的魔力圈。现在我要去参战,参加一次前所未有的至为伟大的战争,可我一无所知,一点也不中用。Jesu Bistresamiab le et trèscaus ti que①.”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大伙儿都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听我说话。他们是一群愚蠢的人,如若没有他们,我的妻子就不能生活下去,还有这些女人……但愿你能知道,tou tes les fem mesdistingu é es②和一般的女人都是一些什么人啊!我父亲说得很对。当女人露出她们的真面目的时候,自私自利、虚荣、愚笨、微不足道——这就是女人的普遍特征。你看看上流社会的女人,他们似乎有点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对,我的心肝,甭结婚吧,甭结婚吧。”安德烈爵说完了话。 -------- ①法语:我是个快嘴快舌的人。 ②法语:这些像样的女人。 “我觉得非常可笑,”皮埃尔说道,“您认为自己无才干,认为自己的生活腐化堕落。其实您前途无量,而且您……” 他没有说出“您怎么样”,可是他的语调表明,他很器重自己的朋友,对他的前途抱有厚望。 “这种话他怎么能开口说出来呢?”皮埃尔想道。皮埃尔认为安德烈公爵是所有人的楷模,纯粹是因为安德烈公爵高度地凝聚着皮埃尔所缺乏的品德,这种品德可以用“意志力”这个概念至为切贴地表示出来。安德烈公爵善于沉着地应酬各种人,富有非凡的记忆力,博学多识(他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洞悉一切),尤其是善于工作、善于学习,皮埃尔向来就对安德烈公爵的各种才能感到惊讶。如果说安德烈缺乏富于幻想的推理能力(皮埃尔特别倾向于这个领域),那么,他却不认为这是缺点,而是力量的源泉。 在最良好、友善和朴实的人际关系中,阿谀或赞扬都不可缺少,有如马车行驶,车轮需要抹油一样。 “Jesuisunhommefini,”①安德烈公爵说道,“关于我的情况有什么话可说的呢?让我们谈谈你的情况吧,”他说道,沉默片刻后,对他那令人快慰的想法微微一笑。 这一笑同时也在皮埃尔脸上反映出来了。 “可是,关于我的情形有什么话可说的呢?”皮埃尔说道,他嘴边浮现出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微笑,“我是个什么人呢?Jesuisunbatard!”②他忽然涨红了脸。显然,他竭尽全力才把这句话说了出来,“sansnom,sansfortune……③也好,说实话……”但是他没把“说实话”这个词儿说出来,“我暂且自由自在,我心里感到舒畅。不过,我怎么也不知道我应当先做什么事。我想认真地和您商量商量。” -------- ①法语: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②法语:一个私生子。 ③法语:既无名,亦无财富。 安德烈公爵用慈善的目光望着他。可是在他那友爱而温柔的目光中依旧显露出他的优越感。 “在我心目中,你之所以可贵,特别是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们整个上流社会中的一个活跃分子。你觉得舒适。你选择你所愿意做的事吧,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你以后到处都行得通,不过有一点要记住:你不要再去库拉金家中了,不要再过这种生活。狂饮、骠骑兵派头,这一切……对你都不适合了。” “Quevoulez-vous,moncher,”皮埃尔耸耸肩,说道,“Lesfem mes,mon cher,les femmes!”① “我不明白,”安德烈答道:“Lesfem mescom meil faut B,”②这是另一码事;不过库拉金家的Les fem mes,lesfem me set levin③,我不明白啊!” -------- ①法语:我的朋友啊,毫无办法,那些女人,那些女人啊! ②法语:像样的女人。 ③法语:女人,女人和酒。 皮埃尔在瓦西里·库拉金公爵家中居住,他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利一同享受纵酒作乐的生活,大家拿定了主意,要阿纳托利娶安德烈的妹妹为妻,促使他痛改前非。 “您可要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皮埃尔说道,他脑海中仿佛突然出现一个极妙的想法,“真的,我老早就有这个念头。过着这种生活,对什么事我都拿不定主意,什么事我都无法缜密考虑。真头痛,钱也没有了。今天他又邀请我,我去不成了。” “你向我保证,你不走,行吗?” “我保证!” 当皮埃尔离开他的朋友走出大门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钟。是夜适逢是彼得堡六月的白夜。皮埃尔坐上一辆马车,打算回家去。但是他越走近家门,他就越发感觉到在这个夜晚不能入睡,这时候与其说是深夜,莫如说它更像黄昏或早晨。空荡无人的街上可以望见很远的地方。皮埃尔在途中回忆起来,今日晚上必定有一伙赌博的常客要在阿纳托利·库拉金家里聚会。豪赌之后照例是纵酒作乐,收场的节目又是皮埃尔喜爱的一种娱乐。 “如果到库拉金家去走一趟该多好啊。”他心中想道。但是立刻又想到他曾向安德烈公爵许下不去库拉金家串门的诺言。 但是,正如所谓优柔寡断者的遭遇那样,嗣后不久他又极欲再一次体验他所熟悉的腐化堕落的生活,他于是拿定主意,要到那里去了。他蓦地想到,许下的诺言毫无意义,因为在他向安德烈公爵许下诺言之前,他曾向阿纳托利公爵许下到他家去串门的诺言。他终于想到,所有这些诺言都是空洞的假设,并无明确的涵义,特别是当他想到,他明天有可能死掉,也有可能发生特殊事故,因此,承诺与不承诺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皮埃尔的脑海中常常出现这一类的论断,它消除了他的各种决定和意向。他还是乘车到库拉金家中去了。 他乘马车到达了阿纳托利所住的近卫骑兵队营房旁一栋大楼房的门廊前面,他登上了灯火通明的台阶,上了楼梯,向那敞开的门户走进去。接待室内荡然无人,乱七八糟地放着空瓶子、斗篷、套鞋,发散着一股酒味,远处的语声和喊声隐约可闻。 赌博和晚膳已经完毕了,但是客人们还没有各自回家。皮埃尔脱下斗篷,步入第一个房间,那里只有残酒与剩饭,还有一名仆役;他内心以为没有被人发现,悄悄地喝完了几杯残酒。第三个房间传出的喧器、哈哈大笑、熟悉的叫喊和狗熊的怒吼,清晰可闻。大约有八个年轻人在那敞开的窗口挤来挤去。有三个人正在玩耍一只小熊,一个人在地上拖着锁上铁链的小熊,用它来恐吓旁人。 “我押史蒂文斯一百卢布赌注!”有个人喊道。 “当心,不要搀扶!”另一人喊道。 “我押在多洛霍夫上啊!”第三个人喊道,“库拉金,把手掰开来。” “喂,把小熊‘朱沙’扔开吧,这里在打赌啊!” “要一干而尽,不然,就输了。”第四个人喊道。 “雅科夫,拿瓶酒来,雅科夫!”主人喊道,他是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穿着一件袒露胸口的薄衬衣站在人群中间,“先生们,等一会。瞧,他就是彼得鲁沙,亲爱的朋友。”他把脸转向皮埃尔说道。 另一个身材不高、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人从窗口喊叫:“请上这里来,给我们把手掰开,打赌啊!”这嗓音在所有这些醉汉的嗓音中听来令人觉得最为清醒,分外震惊。他是和阿纳托利住在一起的多洛霍夫,谢苗诺夫兵团的军官,大名鼎鼎的赌棍和决斗能手。皮埃尔面露微笑,快活地向四周张望。 “我什么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等一会,他还没有喝醉。给我一瓶酒。”阿纳托利说道,从桌上拿起一只玻璃杯,向皮埃尔跟前走去。 “你首先喝酒。” 皮埃尔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起酒来,而那些蹙起额头瞧瞧又在窗口挤来挤去的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倾听着他们交谈。阿纳托利给他斟酒,对他讲,多洛霍夫和到过此地的海员,叫做史蒂文斯的英国人打赌,这样议定:他多洛霍夫把脚吊在窗外坐在三楼窗台上一口气喝干一瓶烈性甜酒。 “喂,要喝干啊!”阿纳托利把最后一杯酒递给皮埃尔,说道,“不然,我不放过你!” “不,我不想喝。”皮埃尔用手推开阿纳托利,说道;向窗前走去。 多洛霍夫握着英国人的手,明确地说出打赌的条件,但主要是和阿纳托利、皮埃尔打交道。 多洛霍夫这人中等身材,长着一头鬈发,有两只明亮的蓝眼睛。他约莫二十五岁。像所有的陆军军官那样,不蓄胡子,因而他的一张嘴全露出来,这正是他那令人惊叹的脸部线条。这张嘴十分清秀,弯成了曲线。上嘴唇中间似呈尖楔形,有力地搭在厚实的下嘴唇上,嘴角边经常现出两个微笑的酒窝。所有这一切,特别是在他那聪明、坚定而放肆的目光配合下,造成了一种不能不惹人注意这副脸型的印象。多洛霍夫是个不富裕的人,没有什么人情关系。尽管阿纳托利花费几万卢布现金,多洛霍夫和他住在一起,竟能为自己博得好评,他们的熟人把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利比较,更为尊重多洛霍夫,阿纳托利也尊重他。多洛霍夫无博不赌,几乎总是赢钱。无论他喝多少酒,他从来不会丧失清醒的头脑。当时在彼得堡的浪子和酒徒的领域中,多洛霍夫和库拉全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一瓶烈性甜酒拿来了。窗框使人们无法在那窗户外面的侧壁上坐下,于是有两个仆役把窗框拆下来,他们周围的老爷们指手划脚,不断地吆喝,把他们搞得慌里慌张,显得很羞怯。 阿纳托利现出洋洋得意的神气,向窗前走去。他禁不住要毁坏什么东西。他把仆人们推开,拖了拖窗框,可是拖不动它。他于是砸烂了玻璃。 “喂,你这个大力士。”他把脸转向皮埃尔说道。 皮埃尔抓住横木,拖了拖,像木制的窗框喀嚓喀嚓地响,有的地方被他弄断了,有的地方被扭脱了。 “把整个框子拆掉,要不然,大家还以为我要扶手哩。”多洛霍夫说道。 “那个英国人在吹牛嘛……可不是?……好不好呢? ……”阿纳托利说道。 “好吧。”皮埃尔望着多洛霍夫说道,多洛霍夫拿了一瓶烈性甜酒,正向窗前走去,从窗子望得见天空的亮光,曙光和夕晖在天上连成一片了。 多洛霍夫手中拿着一瓶烈性甜酒,霍地跳上了窗台。 “听我说吧!“他面向房间,站在窗台上喊道。大家都沉默不言。 “我打赌(他操着法语,让那个英国人听懂他的意思,但是他说得不太好),我赌五十金卢布,您想赌一百?”他把脸转向英国人,补充了一句。 “不,就赌五十吧。”英国人说道。 “好吧,赌五十金卢布,”二人议定,“我要一口气喝干一整瓶烈性糖酒,两手不扶着什么东西,坐在窗台外边,就坐在这个地方把它喝干(他弯下腰来,用手指指窗户外边那倾斜的墙壁上的突出部分)……就这样,好吗?……” “很好。”英国人说道。 阿纳托利向英国人转过身去,一手揪住他的燕尾服上的钮扣,居高临下地望着他(那个英国人身材矮小),开始用法语向他重说了打赌的条件。 “等一下!”多洛霍夫为了要大家注意他,便用酒瓶敲打着窗户,大声喊道,“库拉金,等一会,听我说吧。如果有谁如法炮制,我就支付一百金卢布。明白么?” 英国人点点头,怎么也不肯让人明白,他有意还是无意接受打赌的新条件。阿纳托利不愿放开英国人,虽然那个英国人点头示意,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阿纳托利用英语把多洛霍夫的话向他翻译出来。一个年轻的、瘦骨嶙峋的男孩——近卫骠骑兵,这天夜里输了钱,他于是爬上窗台上,探出头来向下面望望。 “吓!……吓!……吓!……”他瞧着窗外人行道上的石板说道。 “安静!”多洛霍夫高声喊道,把那个军官从窗台上拉了下来,被马刺绊住腿的军官很不自在地跳到房间里。 多洛霍夫把酒瓶搁在窗台上,这样拿起来方便,他谨小慎微地、悄悄地爬上窗户。他垂下两腿,双手支撑着窗沿,打量了一番,把身子坐稳,然后放开双手,向左向右移动,拿到了一只酒瓶。阿纳托利拿来了两根蜡烛,搁在窗台,虽然这时候天大亮了,两根蜡烛从两旁把多洛霍夫穿着一件白衬衣的脊背和他长满鬈发的头照得通亮了。大家都在窗口挤来挤去。那个英国人站在大家前面。皮埃尔微微发笑,不说一句话。一个在场的年纪最大的人露出气忿的、惊惶失惜的神色,忽然窜到前面去,想一把揪住多洛霍夫的衬衣。 “先生们,这是蠢事,他会跌死的。”这个较为明智的人说道。 阿纳托利制止他。 “不要触动他,你会吓倒他,他会跌死的。怎样?……那为什么呢?……哎呀……” 多洛霍夫扭过头来,坐得平稳点了,又用双手支撑着窗户的边沿。 “如果有谁再挤到我身边来,”他透过紧团的薄嘴唇断断续续地说,“我就要把他从这里扔下去。也罢!……” 他说了一声“也罢”,又转过身去,伸开双手,拿着一只酒瓶搁到嘴边,头向后仰,抬起一只空着的手,这样,好把身子弄平稳。有一个仆人在动手捡起玻璃,他弯曲着身子站着不动弹,目不转睛地望着窗户和多洛霍夫的脊背。阿纳托利瞪大眼睛,笔直地站着。那个英国人噘起嘴唇,从一旁观看。那个想阻拦他的人跑到屋角里去,面朝墙壁地躺在沙发上。皮埃尔用手捂住脸,此时他脸上虽然现出恐怖的神色,但却迷迷糊糊地保持着微笑的表情。大家都沉默不言。皮埃尔把蒙住眼睛的手拿开。多洛霍夫保持同样的姿态坐着,不过他的头颅向后扭转过来了,后脑勺上的卷发就碰在衬衫的领子上,提着酒瓶的手越举越高,不住地颤抖,用力地挣扎着。这酒瓶显然快要喝空了,而且举起来了,头也给扭弯了。“怎么搞了这样久呢?”皮埃尔想了想。他仿佛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多洛霍夫把脊背向后转过去,一只手神经质地颤栗起来,这一颤栗足以推动坐在倾斜的侧壁上的整个身躯。他全身都挪动起来了,他的手和头越抖越厉害,费劲地挣扎。一只手抬了起来抓住那窗台,但又滑落下去了。皮埃尔又用手捂住眼睛,对自己说:永远也没法把它睁开来。他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微微地摆动起来了。他看了一眼:多洛霍夫正站在窗台上,他的脸色苍白,但却露出了愉快的神态。 “酒瓶子空了。” 他把这酒瓶扔给英国人,英国人灵活地接住。多洛霍夫从窗上跳下来。他身上发散着浓重的甜酒气味。 “棒极了!好样的!这才是打赌啊!您真了不起啊!”大家从四面叫喊起来了。 那个英国人拿出钱包来数钱。多洛霍夫愁苦着脸,沉默不语。皮埃尔一跃跳上了窗台。 “先生们!谁愿意同我打赌呢?我同样做它一遍,”他忽然高声喊道,“不需要打赌,听我说,我也这么干。请吩咐给我拿瓶酒来。我一定做到……请吩咐给我拿瓶酒来。” “让他干吧,让他干吧!”多洛霍夫面带微笑,说道。 “你干嘛,发疯了么?谁会让你干呢?你就站在梯子上也会感到头晕啊。”大家从四面开腔说话。 “我准能喝干,给我一瓶烈性甜酒吧!”皮埃尔嚷道,做出坚定的醉汉的手势,捶打着椅子,随即爬上了窗户。 有人抓住他的手,可是他很有力气,把靠近他的人推到很远去了。 “不,你这样丝毫也说服不了他,”阿纳托利说道,“等一等,我来哄骗他。你听我说,跟你打个赌吧,但约在明天,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到×××家中去了。” “我们乘车子去吧,”皮埃尔喊道,“我们乘车子去吧!…… 把小熊‘米沙’也带去。” 他于是急忙抓住这头熊,抱着它让它站起来,和它一同在房里跳起舞来,双腿旋转着。 ------------------ 7 瓦西里公爵履行了他在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上答应名叫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替她的独子鲍里斯求情的诺言。有关鲍里斯的情形已禀告国王,他被破例调至谢苗诺夫兵团的近卫队中担任准尉。安娜·帕夫洛夫娜虽已四出奔走斡旋,施展各种手段,但是,鲍里斯还是未被委派为副官,亦未被安插在库图佐夫手下供职。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晚会后不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就回到莫斯科,径直地到她的富有的亲戚罗斯托夫家中去了,她一直住在莫斯科的这个亲戚家中,她的被溺爱的鲍里斯从小就在这个亲戚家中抚养长大,在这里住了许多年,他刚被提升为陆军准尉,旋即被调任近卫军准尉。八月十日近卫军已自彼得堡开走,她那留在莫斯科置备军装的儿子要在前往拉兹维洛夫的途中赶上近卫军的队伍。 罗斯托夫家中有两个叫做娜塔莉娅的女人——母亲和小女儿——过命名日。从清早起,波瓦尔大街上一栋莫斯科全市闻名的叫做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的大楼前面,装载着贺客的车辆就来回奔走,川流不息。伯爵夫人和漂亮的大女儿坐在客厅里接待来宾,送走了一批宾客,又迎来了另一批宾客,不停地应接。 这位伯爵夫人长着一副东方型的瘦削的脸盘,四十五岁上下,她为儿女所劳累(有十二个儿女),身体显得虚弱。由于体弱,她的动作和言谈都很迟缓,这却赋予她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的风貌。叫做安娜·米哈伊洛莫娜·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就像他们家里人一样,也坐在那儿,帮助和应酬宾客。年轻人认为不必参与接待事宜,都呆在后面的几个房间里。伯爵迎送着宾客,邀请全部宾客出席午宴。 “十分、十分感激您machère或moncher①,(他对待一切人,无论地位高于他,抑或低于他,都毫无例外地、毫无细微差别地称machère或moncher),我个人代替两个过命名日的亲人感激您。请费神,来用午膳。您不要让我生气,moncher。我代表全家人诚挚地邀请您,machère。”他毫无例外地,一字不变地对一切人都说这番话,他那肥胖的、愉快的、常常刮得很光的脸上现出同样的神态,他同样地紧握来宾的手,频频地鞠躬致意。送走一位宾客后,伯爵回到那些尚在客厅未退席的男女宾客面前,他把安乐椅移到近旁,显露出热爱生活、善于生活的人所固有的样子,豪放地摊开两腿,两手搁在膝盖上,意味深长地摇摇摆摆,他预测天气,请教保健的秘诀,有时讲俄国话,有时讲很差劲的、但自以为道地的法国话,后来又现出极度困倦、但却竭尽义务的人所独具的样子去送宾客,一面弄平秃头上稀疏的斑发,又请宾客来用午膳。有时候,他从接待室回来,顺路穿过花斋和堂馆休息室走进大理石大厅,大厅里已经摆好备有八十份餐具的筵席,他望着堂倌拿来银器和瓷器,摆筵席、铺上织花桌布,并把出身于贵族的管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喊到身边来,说道: “喂,喂,米佳,你要注意,把一切布置停妥。好,好,” -------- ①法语:亲爱的女客,亲爱的男客。 他说道,十分满意地望着摆开的大号餐桌,“餐桌的布置是头件大事。就是这样……”他洋洋自得地松了口气,又走回客厅去了。 “玛丽亚·利洛夫娜·卡拉金娜和她的女儿到了!”伯爵夫人的身材魁梧的随从的仆人走进客厅门,用那低沉的嗓音禀告。伯爵夫人思忖了一会,闻了闻镶有丈夫肖像的金质鼻烟壶。 “这些接客的事情把我折磨得难受,”她说道,“哦,我来接待她这最后一个女客。她真拘礼,请吧,”她用忧悒的嗓音对仆人说,内心好像是这样说:“哎呀!让你们这些人置我于死命吧!” 一个身段高大、肥胖、样子骄傲的太太和她的圆脸蛋的、微露笑容的女儿,衣裙沙沙作响,走进客厅来。 “Chèrecomtesse,ilyasilongtemps… elleaéléa litéela pauv re en fant… au bal des Razoumow sky… etlacom tesse Apraksine… j’aié tési heureu se……①,听见妇女们互相打断话头、闹哄哄的谈话声,谈话声和连衣裙的沙沙声、移动椅子的响声连成一片了。这场谈话开始了,谈话在头次停顿的时候正好有人站起来,把那连衣裙弄得沙沙作响,有人说:“Jeaui sbien charm é e,la sant é dlema man… etlacomtes se Aprak sine.”②连衣裙又给弄得沙沙作响,有人朝接待室走去,穿上皮袄或披起斗篷,就离开了。谈话中提到当时市内的首要新闻——遐尔闻名的富豪和叶卡捷琳娜女皇当政时的美男子老别祖霍夫伯爵的病情和他的私生子皮埃尔,此人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举办的晚会上行为不轨,有失体统。 -------- ①法语:伯爵夫人……已经这样久了……可怜的女孩,她害病了……在拉祖莫夫斯基家的舞会上……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我简直高兴极了…… ①法语:我非常、非常高兴……妈妈很健康……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 “我非常惋惜可怜的伯爵,”一个女客人说道,“他的健康情况原已十分恶劣,现今又为儿女痛心,这真会断送他的命啊!” “是怎么回事?”伯爵夫人问道,好像她不知道那女客在说什么事,不过她已有十五次左右听过关于别祖霍夫伯爵感到伤心的原因。 “这就是现在的教育啊!”一位女客说,“现在国外时,这个年轻人就听天由命,放任自流,而今他在彼得堡,据说,他干了不少令人胆寒的事,已经通过警察局把他从这里驱逐出去了。” “您看,真有其事!”伯爵夫人说道。 “他很愚蠢地择交,”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插嘴了,“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他的那个多洛霍夫,据说,天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勾当。二人都受罪了。多洛霍夫被贬为士兵,别祖霍夫的儿子被赶到莫斯科去了。阿纳托利·库拉金呢,他父亲不知怎的把他制服了,但也被驱逐出彼得堡。” “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伯爵夫人问道。 “他们真是些十足的土匪,尤其是多洛霍夫,”女客人说道,“他是那个备受尊重的太太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多洛霍娃的儿子,后来怎么样呢?你们都可以设想一下,他们三个人在某个地方弄到了一头狗熊,装进了马车,开始把它运送到女伶人那里去了。警察跑来制止他们。他们抓住了警察分局局长,把他和狗熊背靠背地绑在一起,丢进莫伊卡河里。狗熊在泅水,警察分局局长仰卧在狗熊背上。” “machère,警察分局局长的外貌好看吗?”伯爵笑得要命,高声喊道。 “啊,多么骇人呀!伯爵,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可是太太们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真费劲才把这个倒霉鬼救了出来,”女客人继续说下去,“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的儿子心眼真多,逗弄人啊!”她补充一句话,“听人家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脑子也挺灵活。你看,外国的教育结果把他弄到这个地步。虽然他有钱,我还是希望这里没有谁会接待他。有人想介绍他跟我认识一下,我断然拒绝了:我有几个女儿嘛。” “您干嘛说这个年轻人很有钱呢?”伯爵夫人避开少女们弯下腰来问道,少女们马上装作不听她说话的样子,“要知道,他只有几个私生子女。看来……皮埃尔也是个私生子。” 女客人挥动一手下臂。 “我想,他有二十个私生子女。” 公爵夫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插话了,她显然是想显示她的社交关系,表示她熟悉交际界的全部情况。 “就是这么一回事,”她低声地、意味深长地说道,“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颇有名声,尽人皆知……他的儿女多得不可胜数,而这个皮埃尔就是他的宠儿。” “旧年这个老头儿还挺漂亮哩!”伯爵夫人说道,“我还未曾见过比他更漂亮的男人。” “现在他变得很厉害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我想这样说,”她继续说下去,“根据妻子方面的关系,瓦西里公爵是他的全部财产的直接继承人,但是他父亲喜爱皮埃尔,让他受教育,还禀告国王……如果他一旦辞世,他的病情加重,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断气,罗兰也从彼得堡来了,谁将会得到这一大笔财产,是皮埃尔呢,或者是瓦西里公爵。四万农奴和数百万财产。这一点我了若指掌,瓦西里公爵亲口对我说过这番话。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正是我的表舅哩。而且他给鲍里斯施行洗礼,是他的教父。”她补充一句,好像一点不重视这等事情似的。 “瓦西里公爵于昨日抵达莫斯科。有人对我说,他来的用意是实地视察。”女客人说。 “是的,但是,entrenous,”①公爵夫人说道,“这是一种藉口,说实话,他是来看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的,他听到伯爵的病情加重了。” -------- ①法语: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不可与外人道也。 “但是,machère,这是个招儿,”伯爵说道,他发现那个年长的女客不听他说话,就向小姐们转过脸去说,“我心里想象,那个警察分局局长的外貌是十分漂亮的。” 他于是想到那个警察分局局长挥动手臂的模样,又哈哈大笑起来,那响亮的嗓子低沉的笑声撼动着他整个肥胖的身躯,他发出这种笑声,就像平素吃得好,特别是喝得好的人所发出的笑声一样。“好吧,请您到我们那里来用午饭。”他说道。 ------------------ 8 大家都默不作声。伯爵夫人望着女客人,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但她并不掩饰那种心情:如果那个女客人站立起来,退席离开,她丝毫也不会感到怏怏不乐。女客的女儿正在弄平连衣裙,用疑问的眼神望着母亲,就在这时分,忽然听见隔壁房里传来一群男人和女人向门口迅跑的步履声、绊倒椅子的响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跑进房里来,用那短短的纱裙盖住一件什么东西,她在房间当中停步了。很明显,她在跑步时失脚,出乎意料地蹦得这么远。就在这同一瞬间,一个露出深红色衣领的大学生、一个近卫军军官、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和一个身穿儿童短上衣的面颊粉红的胖乎乎的男孩在那门口露面了。 伯爵猛然跳起来,摇摇摆摆地走着,把两臂伸开,抱住跑进来的小女孩。 “啊,她毕竟来了!”他含笑地喊道,“过命名日的人!machère过命名日的人!” “machère,ilyauntempspour,tout,”①伯爵夫人假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她说,“你总是溺爱她,埃利。”她对丈夫补充地说。 “Bonjour,machère,jevousfélicite,”女客人说道,“Quel lede li cieu se en fant!②”她把脸转向母亲,补充地说。 -------- ①法语:一切事情都得有个时间,亲爱的。 ②法语:我亲爱的,您好,向您表示祝贺。多么可爱的小孩子! 小姑娘长着一双黑眼睛,一张大嘴巴,相貌不漂亮,但挺活泼。她跑得太快,背带滑脱了,袒露出孩子的小肩膀,黑黝黝的打绺的鬈发披在后面,光着的手臂十分纤细,身穿一条钩花裤子,一双小脚穿着没有鞋带的矮靿皮靴。说她是孩子已经不是孩子,说她是女郎还不是女郎,她正值这个美妙的年华。她从父亲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走到了母亲近旁,母亲的严厉呵斥她不在乎,倒把脸儿藏在母亲的花边斗篷里,不知她为什么而笑,一面若断若续地说到她从衣裙下面掏出来的洋娃娃。 “你们看见吗?……一个洋娃娃……咪咪……你们都看见。” 娜塔莎不能说下去了(她以为一切都很可笑),她倒在母亲身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非常响亮,以致所有的人,连那个过分拘礼的女客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你得啦,走吧,带上你这个丑东西走吧!”母亲说道,假装发脾气,把女儿推到一边去。“这是我的小女儿。”她把脸转向女客说道。 娜塔莎有一阵子把脸从母亲的花边三角头巾下抬起来,透过笑出的眼泪,从底下朝她望了一眼,又把脸蛋藏了起来。 女客人被迫欣赏家庭中的这个场面,认为有参与一下的必要了。 “我亲爱的,请您告诉我,”她把脸转向娜塔莎,说道,“这个咪咪究竟是您的什么人?大概是女儿吧?” 娜塔莎不喜欢对待儿童的宽容的口气,女客人却用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她一言不答,严肃地瞟了女客人一眼。 与此同时,这一辈年轻人:军官鲍里斯——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的儿子、大学生尼古拉——伯爵的长男、索尼娅——伯爵的一个现年十五岁的外甥女以及小彼得鲁沙——伯爵的幼子,都在客厅里入席就座了。显然,他们竭尽全力把还流露在每个人脸上的兴奋和悦意保持在合乎礼仪的范围以内。显而易见,他们在迅速奔跑出来的后面的几个房间里,闲谈比起在这里议论城里的谗言、天气和comtesseApraksine①的问题,听来令人更开心。他们有时候互相凝视,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 ①法语: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 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军官,从童年时代起就是朋友,两个人年龄相同,而且长得漂亮,但其面目并不相像。鲍里斯是个身材魁梧、头发浅黄的青年,他那宁静而俊美的面孔上,五官生得端正,眉清目秀。尼古拉是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一头鬈发,面部表情坦率。他的上嘴唇边逐渐长出黑色的短髭,他的灵敏和激情在整个面部流露出来。尼古拉一走进客厅,两颊就涨红了。显然,他想开口说话,但却找不到话题;鲍里斯正好相反,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应付的办法,沉着而戏谑地讲起洋娃娃咪咪的事,说他认识它的时候,它还是个小姑娘,当时它的鼻孔还没有碰坏,他记得在这五年内它变老了,头顶也现出裂纹了。他说了这句话,便朝娜塔莎望了一眼。娜塔莎转过脸去不理睬他,看了看眯缝起眼睛、不出一声笑得浑身发抖的小弟弟,她再也按捺不住了,一跃而起,迈开敏捷的小腿,从客厅里飞奔出来。鲍里斯没有发笑。 “妈妈,看来您也要走了吧?要马车吗?”他面露微笑地对母亲说。 “好,走吧,走吧,吩咐他们把马车准备好。”她含笑说道。 鲍里斯悄悄地走出来,跟在娜塔莎后面,那个胖乎乎的男孩生气地跟在他们后面跑,好像他的事情遭受挫折而懊悔似的。 ------------------ 9 年轻人当中,除开伯爵夫人的长女(她比她妹妹年长四岁,举止已经跟大人一样了)和作客的小姐而外,客厅里剩下尼古拉和外甥女索尼娅二人了。索尼娅是个身段苗条、小巧玲珑的黑发女郎,在那长长的睫毛遮掩下闪现出温柔的眼神,一条乌黑而浓密的发辫在头上盘了两盘,脸上的皮肤,特别是裸露而消瘦、肌肉发达而漂亮的手臂和颈项的皮肤,都略带黄色。她那动作的平稳,小小肢体的柔软和灵活,有点调皮而自持的风度,便像一只尚未发育成熟的美丽可爱的猫崽,它必将成为一只颇具魅力的母猫。显然她认为面露微笑去谛听众人谈话是一种礼貌的态度,但是,她那对洋溢着少女热情崇拜的眼睛,从那长长的浓密的睫毛下面,情不自禁地望着行将入伍的consin①,她那笑意一点也不能欺骗任何人,显而易见,这只小猫蹲下来,只是想要更有力地跳起来,如同鲍里斯和娜塔莎一样从客厅里窜出去,和她的表兄一块儿嬉戏。 -------- ①法语:表兄。 “machère,是的,”老伯爵把脸转向女客,一面指着他的尼古拉,说道,“machère,看,他的朋友鲍里斯擢升为军官了,为友谊起见,他不想落在鲍里斯后面,抛弃了大学和我这个老头,也服兵役去了。有人在档案馆给他弄到一个差事,本来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这不就是看情面嘛?”伯爵用疑问的口气说道。 “是呀,有人说已经宣战了。”女客人说。 “早就有人在说啊,”伯爵说道,“说了一阵子,又说一阵子,就不再说了。machère,这不就是看情面嘛!”他把自己说过的话重说一遍,“尼古拉去当骠骑兵了。” 女客摇摇头,不知道要说什么话。 “根本不是为友情,”尼古拉答道,涨红了脸,好像他受到一种使他羞愧的诋毁似的,他于是要为自己辩护,“根本不是为友情,而只是觉得我有服兵役的天职。” 他回头望望表妹,又望望做客的小姐,她们二人都面露称赞的微笑望着他。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上校舒伯特今天在我们这儿吃午饭,他在这儿度假,要把尼古拉带走。这有什么法子呢?”伯爵说道,耸耸肩,诙谐地提起这件显然使他深感痛楚的事情。 “爸爸,我已经跟您说过,”儿子说道,“如果您不愿意放我走,那么我就留下来。但是我知道,除开服兵役而外,我毫无用场;我不是外交家,不是官员,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他说道,露出风华正茂之时的轻薄的样子,不时地端详索尼娅和做客的小姐。 小猫用眼睛紧紧地盯住他,随时都准备嬉戏一通,表露一下它那猫的本性。 “嗯,嗯,好极了!”老伯爵说道,“向来就急躁……波拿巴还在冲昏大家的头脑,大家都想到他由中尉摇身一变当上皇帝了。也罢,愿上帝保佑。”他补充一句,并不注意女客嘲讽的微笑。 成年人开始谈论波拿巴的事情。卡拉金娜的女儿朱莉把脸转向小罗斯托夫,说道: “很遗憾,星期四那天您没有到阿尔哈罗夫家里去。您不在场,我觉得寂寞无聊。”她说道,向他露出温和的微笑。 年轻人因受奉承而深感荣幸,脸上呈露出风华正茂之时的轻浮的微笑,他坐得离她更近了,他和那笑容可掬的朱莉单独地闲聊起来,根本没发觉他这情不自禁的微笑竟像一柄醋意的尖刀戳进那面红耳赤、佯装微笑的索尼娅的心窝。闲谈的中间,他回过头来瞥了她一眼,索尼娅愤恨地望望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流出眼泪,没有露出假装的微笑,她站起来,从房里走出去。尼古拉的兴奋情绪已经消逝了。他窥伺谈话一中断,就露出扫兴的神态,从房里出来,寻找索尼娅去了。 “所有这些年轻人的秘密事情真藏不住,会露出马脚啊!”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指着正走出门去的尼古拉说道。“Cousi Bnage- danger eux voi sinage,”①她补充一句。 “是的,”伯爵夫人说道,随同这一代年轻人进入客厅带来的一线阳光消失后,她仿佛在回答未曾有人向她提出、但却经常使她全神贯注的问题似的,“她经受了多少苦难、多少烦扰,现在才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欢乐啊!可是现在,说实话,恐惧的比重却大于欢乐。你总是怕这怕那,总是怕这怕那啊!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正值这个年龄,就会遇到许多危险的事情。” “一切以教育为转移。”女客人说道。 “是的,您说的是真话,”伯爵夫人继续说道,“谢天谢地,直至现在,我还是我的子女的朋友,我博得他们充分的信赖。”伯爵夫人说,许多父母出过差错,我重蹈覆辙,他们都以为,子女并没有隐瞒他们的秘密,“我知道,我永远是我的几个女儿的第一个confidente②,尼古拉性情急躁,要是他淘气(男孩子哪能不淘气),也不会像彼得堡这些绅士派头的人那样。” -------- ①法语:表兄弟、表姐妹这种亲戚真糟糕透了啊。 ②法语:出主意的人。 “是啊,都是些很好的、很好的孩子,”伯爵说道,认为这种看法很对头。他往往在解决他认为很复杂的问题时,便用“很好的”这个词来应付,“得了吧!他也想去当个骠骑兵啊!无论您怎样要求,也无济于事,machère!” “你的小女儿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儿!”女客人说道,“火性子人!” “是的,火性子人,”伯爵说道,“她就像我啊!她有一副悦耳的嗓子:虽然她是我的儿女,但我也要如实说来。她将来是个歌唱家,又是一个萨洛莫妮。我们延请了一位意大利人教她唱歌。” “不是太早了吗?据说,她这个时候学唱对嗓子不利。” “哦,不,哪里太早啊!”伯爵说道,“我们母亲辈十二三岁不就出嫁了吗?” “她现在就已爱上鲍里斯了!她怎么样?”伯爵夫人说道,两眼望着鲍里斯的母亲,悄悄地露出微笑,虽然在回答经常使她心神贯注的问题,她继续说下去,“哦,您知道,如果我对她严加管教,如果我禁止她……天知道,他们偷偷地会做出什么事(伯爵夫人心中暗指,他们会接吻),可是现在,她说的每句话我都知道。她晚上自己跑回家来,把一切情形讲给我听。我也许正在惯养她,不过,说实话,这样做似乎更妙。我对大女儿管教得很严。” “是的,教育我的方式完全不一样。”长女——漂亮的名叫薇拉的伯爵小姐面带微笑地说道。 但是微笑并没有使薇拉的面部变得更加漂亮,这是一件常见的事,恰好适得其反,她的脸色变得不太自然,从而令人生厌。长女薇拉长得俊俏,并不笨拙,学习成绩优良,受到很好的教育,她的嗓子悠扬悦耳,她说的话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但是,说来令人诧异,女客也好,伯爵夫人也好,大家都竟然回过头来望她一眼,仿佛十分惊讶似的,为什么她要说这番话,大家都觉得尴尬。 “大家总对年龄较大的儿童自作主张,总想做出什么不平凡的事业。”女客人说道。 “machère,不用隐瞒,承认好了!伯爵夫人对薇拉的事自作主张,”伯爵说道。“这又有什么关系啊!她毕竟变成一个很好的姑娘。”他补充说道,向薇拉递个眼色,表示赞成的意思。 女客们站了起来,答应来吃午饭,便乘马车走了。 “是什么派头!他们都坐着,坐着不走!”伯爵夫人送走客人后说道。 ------------------ 10 娜塔莎步出客厅,奔驰而去,只奔至花房。她在这个房间里停下来了,等候鲍里斯走出门来。她已经不耐烦了。他没有马上走来,她顿了一下脚,快要放声大哭,这时听到了年轻人的不疾速亦不迟缓的文质彬彬的步履声。娜塔莎飞快地窜到花桶中间,躲匿起来了。 鲍里斯在房间中央停步了,环顾了一遭,掸掉制服袖子上的尘屑,走到镜台前,仔细瞧瞧他那俊美的面孔。娜塔莎没有出声,从她躲匿的地方向外观望,等待着,看他怎样办。他在镜台前伫立了片刻,微微一笑,就向大门口走去。娜塔莎想喊他一声,随即改变了念头。 “让他去找吧,”她对自己说道。鲍里斯刚刚走出来,索尼娅涨红了脸,透过泪水愤恨地低声细语,从另一道门走了出来。娜塔莎忍住了,没有起步向她身边跑去,还留在躲匿的地方,宛如戴上一顶隐身帽,不时地窥视人世间的动静。她正在享受一种特别新鲜的乐趣。索尼娅用耳语说着什么话,又回头望望客厅门。尼古拉从门口走出来了。 “索尼娅,你怎么啦?哪能这样呢?”尼古拉说道,向她身边跑来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丢下我别管吧!”索尼娅嚎啕大哭起来。 “不,我知道干嘛。” “哦,您知道,好得很,您上她那儿去吧。” “索——尼娅!有句话要跟你说!哪能凭瞎想这样折磨我,这样折磨你自己!”尼古拉说道,一把抓住她的手。 索尼娅不去挣脱自己的手,停止哭泣了。 娜塔莎屏住气息,一动不动地从她躲匿的地方用那闪闪发亮的眼睛向外张望。“此刻会出什么事呢?”她思忖道。 “索尼娅!我所需要的不是整个世界!在我心目中唯有你才是一切,”尼古拉说道,“我向你证明我说的话。” “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 “哦,我再也不说了,嗯,索尼娅,宽恕我吧!”他把她拖到自己身边,吻了吻她。 “嗬,多么好啊!”娜塔莎心里想道,索尼娅和尼古拉从房里走出以后,她跟随着他们,把鲍里斯喊到自己身边来。 “鲍里斯,您到这里来,”她现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狡黠的神态说道,“我有一件事要说给您听。到这里来吧,到这里来吧。”她说道,把他领到花房里她躲匿过的花桶之间。鲍里斯微露笑容,跟在她后面走去。 “这究竟是件什么事呢?”他发问。 她困窘不安,向四下打量一番,看见她那被扔在花桶上的洋娃娃,把它拿起来。 “吻吻这个洋娃娃吧。”她说道。 鲍里斯用关切而温和的目光望着她那兴奋的脸盘,一声也不回答。 “您不愿意吗?喂,就到这儿来吧,”她说道,并向花丛纵深走去,扔掉了那个洋娃娃,“靠近点,靠近点吧!”她轻言细语地说道。她双手抓住军官的袖口,在她那涨红了的脸上可以望见激动和恐惧的神色。 “您愿意吻吻我吗?”她低声细语,几乎听不清楚,皱着眉头向他瞧着,脸上露出微笑,激动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鲍里斯面红耳赤。 “您多么可笑!”他说道,向她弯下腰来,面红得更加厉害,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等待好机会。 她突然跳到花桶上,身段就显得比他高了,她用自己的双手把他抱住了,于是她那纤细的裸露的手臂在他的颈项上方弯成弧形了,她仰起头来,把头发甩在后面,正好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 她经过花钵中间窜到花丛的另一边,低垂着头,停步不前了。 “娜塔莎,”他说道,“您知道我是爱您的,可是……” “您爱上我了吗?”娜塔莎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我爱上您了,但是您瞧,真是的,我们以后不要像刚才那样冒冒失失……还有四个年头……那时候我会向您求婚。” 娜塔莎思忖了一下。 “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她说道,弯屈着她那纤细的指头算算,“很好!那么成了定局罗?” 欣喜和安定的微笑使她兴奋的面部神采奕奕。 “成定局了!”鲍里斯说道。 “永远吗?”小女孩说道,“一直到寿终正寝?” 她于是挽着他的手臂,露出幸运的神色,静悄悄地和他并排走到摆满沙发的休息室里去。 ------------------ 11 会客的事情使伯爵夫人疲惫不堪,她吩咐不再招待任何人,又指示门房,只邀请一些务须登门饮宴的贺客。伯爵夫人想和自己童年时代的女友——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单独晤谈,自从她自彼得堡归来,伯爵夫人还没有好好地探查她啦。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露出一幅泪痕斑斑但却令人心欢的面孔,把身子移向伯爵夫人的安乐椅近旁。 “我对你直言不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我们这些老朋友剩存的已经很少了!因此,我十分珍惜你的友情。”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望了望薇拉,便停住了。伯爵夫人握了握朋友的手。 “薇拉,”伯爵夫人把脸转向显然不受宠爱的长女,说道,“您怎么一点不明事理啊?难道你不觉得,你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吗?到几个妹妹那里去吧,或者……” 貌美的薇拉鄙夷地微露笑容,显然她一点也不感到屈辱。 “妈妈,假如您老早对我说了这番话,我老早就会离开您了。”她说了这句话,便向自己房里去了。 但是,当她路过摆满沙发的休息室时,她发觉休息室里有两对情人在两扇窗户近侧对称地坐着。她停步了,鄙视地微微一笑。索尼娅坐在尼古拉近侧,他把他头次创作的诗句誊写给她看。鲍里斯和娜塔莎坐在另一扇窗户旁边,当薇拉走进来时,他们都默不作声了。索尼娅和娜塔莎带着愧悔、但却幸福的神态,瞥了薇拉一眼。 看见这些热恋的小姑娘,真令人高兴和感动。但是她们的样子在薇拉身上显然没有引起愉快的感觉。 “我请求你们多少次了,”她说道,“不要拿走我的东西,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房间。”她拿起尼古拉身边的墨水瓶。 “我马上给你,马上给你。”他说道,把笔尖蘸上墨水了。 “你们向来不善于适合时宜地做事情,”薇拉说道,“方才你们跑到客厅里来,真教大家替你们害臊。” 虽然她说的话完全合情合理,莫非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回答,这四个人只是互使眼色而已。她手里拿着墨水瓶迟迟未起步,在房里滞留。 “你们这样的年纪,会有什么秘密,娜塔莎和鲍里斯之间,你们二人之间会有什么秘密,会是一些愚蠢事。” “嘿,薇拉,这与你何干。”娜塔莎用低沉的嗓音作辩护。 这天她对大家显然比平常更慈善,更温和。 “很愚蠢,”薇拉说道,“我替你们害臊,这是什么秘密呢?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不招惹你和贝格就是了。” 娜塔莎急躁地说…… “我认为,你们不会触犯人,”薇拉说道,“因为我从来没有什么不轨的行为。看吧,你怎样对待鲍里斯,我准会告诉妈妈。” “娜塔莉娅·伊利尼什娜待我非常好,”鲍里斯说道,“我不会诉怨的。”他说道。 “鲍里斯,请您不要管,您是这么一个外交家(外交家这个词在儿童中间广为流传,他们使这个词具有一种特殊意义),真够乏味,”娜塔莎用委屈的颤栗的嗓音说道,“她干嘛跟着我,纠缠得没完没了?这一点你永远也不会明白,”她把脸转向薇拉说道,“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你简直没有心肠,你只是个ma-damedeGenlis①(尼古拉给薇拉起的侮辱人的绰号),你主要的乐趣就是给他人制造不愉快的事情。你去向贝格献媚吧,你想怎样献媚就怎样献媚。”她急匆匆地说道。 -------- ①法语:让莉夫人。 “是的,我也许不会在客人们面前去追逐一个年轻人……” “得啦,你达到目的了,”尼古拉插话了,“在大家面前说了许多讨厌的话,真使大家扫兴了。我们到儿童室去吧。” 这四个人有如一群惊弓之鸟都站立起来,从房里走出去了。 “人家对我说了许多讨厌的话,可我没有对谁说什么。”薇拉说道。 “madamedeGenlis!madamedeGenlis!”有人从门后传出一阵笑语。 貌美的薇拉给了大家一种令人激动的不愉快的印象,但她却微微一笑;大家说的话显然对她不发生作用,她向镜台前走去。把围巾和头发弄平,一面注视着她那美丽的面孔,她显然变得更冷漠,更安详了。 客厅中的谈话持续下去了。 “啊!亲爱的,”伯爵夫人说道,“在我的生活上toutn’estpasrose,我难道看不见吗,dutrain,quenousallons①,我们的财富不能长久地维系下去!这个俱乐部和他的慈善,全都碍了事。我们住在乡下,我们难道会静心养性吗?戏院呀,狩猎呀,天知道还有什么花样。至于我的情形,又有什么可谈的呢?哦,这一切一切你究竟是怎样安排的啊?安内特,我对你的境况常常感到惊讶,你这个年纪,怎么一个人乘坐马车,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到各位部长那里去,到各个贵族那里去,你善于应酬各种人,真令我感到惊奇!嗬,这方面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妥善安排的啊?这方面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内行。” -------- ①法语:依照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并非幸福盈门,尽如人意。 “啊,我的心肝!”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答道,“但愿你不要知道,当一个寡妇,无依无靠,还有一个你所溺爱的儿子,生活多么艰苦,什么事都得学会,”她带着有点傲气的神态继续说道,“这场诉讼让我学了乖。如果我要会见某位显要达官,我就写一封便函:‘Prin ces seunetel le①欲晋谒某人,’我于是外出走一趟。我坐上马车亲自造访,哪怕走两趟也好,走三趟、四趟也好,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无论别人对我持有什么看法,对我来说,横直一样。” “喂,你怎样替鲍里斯求情的呢?”伯爵夫人问道,“要知道,你的儿子已经是近卫军军官了,而尼古拉才当上士官生。 没有人为他斡旋哩。你向谁求过情呢?” “我向瓦西里公爵求过情。他真是殷勤待人。现在他什么都答应了,并且禀告了国王。”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异常高兴地说道,完全忘记了她为达到目的而遭受的凌辱。 “瓦西里公爵怎么样?变老了吧?”伯爵夫人问道,“自从我们在鲁缅采夫家演了那幕闹剧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我想,他已经忘记我了。Ilmefaisaitlacour,”②伯爵夫人面露微笑地想起这件事。 “他还是那个样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答道,“他很殷勤地待人,满口说的是奉承讨好的话。Les grand eursneluiont pastourné lat ê tedu tout③。‘亲爱的公爵夫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能替您做的事太少了,’他对我说道,‘如有事就请吩咐吧。’不过,他是个享有荣誉的人,是个挺好的亲戚,娜塔莎,可你总知道,我疼爱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为了他的幸福我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啊。我的境况糟糕透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降低嗓门心情忧悒地继续说下去,“我的情况糟糕透了,使我现在处于最难堪的地位。我那倒霉的讼案把我拥有的一切吞噬掉了,而且毫无进展。你可以想象我没有金钱,àlalettre④竟然没有十戈比的小银币,我不知道要用什么给鲍里斯置备军装,”她掏出一条手绢,哭起来了,“我现在需要五百卢布,而我身边只有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纸币。我处于这种境地……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身上。如果他不愿意支援他的教子——要知道他曾给鲍里斯施洗礼——,不愿意发给他一笔薪金,那么,我的奔走斡旋势必付诸东流;我将用什么给他置备军装啊。” -------- ①法语:某公爵夫人。 ②法语:他轻浮地追求过我。 ③法语:荣耀的地位没有使他变样子。 ④法语:有时候。 伯爵夫人两眼噙着泪水,沉默地想着什么事。 “我常常想到,这也许就是罪孽,”那公爵夫人说道,“我常常想到,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孤单地生活……他有这么多产业……他的生活目的何在?对他来说,生命是沉重的负担,可是鲍里斯才刚刚开始生活。” “他想必会给鲍里斯留下什么财产。”伯爵夫人说道。 “chèreamie①,天晓得!这些富翁和显贵都是利己主义者。但是我还是即刻偕同鲍里斯到他那里去,坦率地对他说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家对我抱有什么看法,请听便吧,说实话,只要儿子的命运有赖于此事,我一切都不在乎,”公爵夫人站立起来,“现在是两点钟,四点钟你们吃午餐。我出去走走还来得及哩。” -------- ①法语:亲爱的朋友。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具有精明能干、善于利用时间的彼得堡贵族夫人的作风,她派人去把儿子喊来,和他一同到接待室去。 “我的心肝,再会吧,”她对送她到门口的伯爵夫人说道,“请你祝我成功吧。”她背着儿子轻言细语地补充说一句。 “machère,您到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那里去吗?”伯爵从餐厅出来,也到接待室去时,说道,“如果皮埃尔身体好一些,请他上我家里来吃午饭。要知道,他时常到我这里来,和孩子们一块跳舞。machère,务必要请他。哦,让我们看看,塔拉斯今天怎样大显神通啊。他说,奥尔洛夫伯爵家里未曾举办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午宴哩。” ------------------ 12 “MoncherBoris,”①当他们搭乘名叫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的四轮轿式马车经过铺有麦秆的街道,驶入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家的大庭院时,名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对儿子说道,“moncherBoris,”母亲从旧式女外套下面伸出手来,胆怯地、温存地把手搁在儿子手上说道,“待人要殷勤、体贴。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毕竟是你的教父,你未来的命运以他为转移。moncher,你要记住,要和蔼可爱,你会这样做……” -------- ①法语:我亲爱的鲍里斯。 “如果我知道,除开屈辱而外,这能得到什么结果……,”儿子冷漠地答道,“但是我向您许了愿,我要为您而效劳。” 虽然有一辆什么人的四轮轿式马车停在台阶前面,但是门房还是把偕同儿子的母亲仔细观察一番(他们并没有通报姓氏,径直地走进两排壁龛雕像之间的玻璃穿堂里),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她那身旧式的女外衣,问他们访问何人,是访问公爵小姐,还是访问伯爵,得知访问伯爵之后,便说大人今天病情更严重,不接见任何人。 “我们可以走啦。”儿子说了一句法国话。 “monami!”①母亲用央求的嗓音说道,又用手碰碰儿子的手臂,仿佛这一触动就可以使他平静,或者使他兴奋似的。 鲍里斯默不作声,没有脱下军大衣,他用疑问的目光望着母亲。 -------- ①法语:我的朋友。 “老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把脸转向门房,用温柔的嗓音说道,“我知道,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的病情严重,……因此我才来探视……我是他的亲戚……老兄,我不会惊动他……不过,我必须见见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他不是呆在这里么。请通报一声。” 门房忧郁地拉了一下通到楼上的门铃的引线,就扭过脸去。 “名叫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求见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他向那走下楼来、从楼梯凸缘下面向外张望的穿着长袜、矮靿皮靴和燕尾服的堂倌喊道。 母亲把那染过的丝绸连衣裙的裙褶弄匀整,照了照嵌在墙上的纯正的威尼斯穿衣镜。她脚上穿着一双矮靿破皮靴,沿着楼梯地毯,走上楼去了。 “moncher,vousm’avezpromis,”①她又向儿子转过脸去说道,她用手碰碰儿子,要他振作起来。 儿子低垂着眼睛,不慌不忙地跟在她后面。 他们走进了大厅,厅里有扇门通往瓦西里公爵的内室。 当母亲随带儿子走到屋子中间,正想向那个看见他们走进来便飞快起身的老堂倌问路的时候,一扇门的青铜拉手转动了,瓦西里公爵走出门来,他按照家常的穿戴方式,披上一件天鹅绒面的皮袄,只佩戴一枚金星勋章,正在送走一个头发黝黑的美男子。这个美男子是大名鼎鼎的彼得堡的罗兰大夫。 “C’estdoncpositif?”②公爵说道。 “Monprince,‘Errarehummanumest’,mais…③大夫答道,弹动小舌发喉音,用法国口音说出几个拉丁词。 “C’estbien,c’estbien…”④ -------- ①法语:我的朋友,你向我许愿了。 ②法语:这是确实的吗? ③法语;我的公爵,“人本来就难免犯错误,”可是…… ④法语:好啦,好啦…… 瓦西里公爵看见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她带在身边的儿子,便鞠了一躬把那个大夫打发走了,他沉默地、但现出发问的样子向他们面前走去。她儿子发现母亲的眼中忽然流露出极度的忧伤,便微微一笑了之。 “是呀,公爵,我们是在多么忧愁的情况下会面啊!……哦,我们亲爱的病人现在怎样了?”她说道,仿佛没有注意到向她凝视的非常冷漠的、令人屈辱的目光。 瓦西里公爵现出疑虑的惶惑不安的神态看看她,而后又看看鲍里斯。鲍里斯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瓦西里公爵没有躬身答礼,却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转过脸来,摇摇头,努努嘴,以示回答她的问话,公爵的动作意味着病人没有多大希望了。 “莫不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惊叫道,“啊!这多么可怕!想起来真是骇人哩……这是我的儿子。”她用手指着鲍里斯补充了一句,“他想亲自向您表示感激。” 鲍里斯又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公爵,请您相信我吧,母亲心眼里永远也不会忘记您为我们做的善事。” “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我能做一点使你们愉快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高兴。”瓦西里公爵说道,又把胸口的皱褶花边弄平。在这儿,在莫斯科,在受庇护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面前,和在彼得堡安内特·舍列尔举办的晚会上相比较,他的姿态和声调都表明他高傲得多了。 “你好好供职,尽力而为,做个当之无愧的臣民,”他很严肃地对着鲍里斯补充说,“我感到非常高兴……您在这里休假么?”他用冷漠的语调说,迫使他照办。 “大人,我听候命令,接到新的任命就动身。”鲍里斯答道,他不因公爵的生硬语调而恼怒,也不表示他有交谈的心意,但他心地平静,态度十分恭敬,公爵禁不住用那凝集的目光朝他瞥了一眼。 “您和您母亲住在一起吗?” “我住在那个叫做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那里,”鲍里斯说道,又补充一句话:“大人。” “这就是那个娶了娜塔莉娅·申申娜的伊利亚·罗斯托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瓦西里公爵用单调的嗓音说道,“Jen’ai jamais pucon ce vo ir,comment Nathalies’estdéci dee à é pouser cetou rsmal— leche!Unper son nagecom plét em ents tupi de etri di cule.Et joueur à cequ’ondit。”①。 “maistresbravehomme,monprince,”②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脸上流露出令人感动的微笑,仿佛她也知道,罗斯托夫伯爵值得这样评价似的,可是她请求人家怜悯一下这个可怜的老头。 “大夫们说了什么呢?”公爵夫人沉默片刻后发问,她那泪痕斑斑的脸上又流露出极度的哀愁。 “希望不大了。”公爵说道。 “不过我很想再一次地感谢叔叔对我和鲍里斯的恩赐。C’estson fil leul。”③她补充一句,那语调听来仿佛这个消息必然会使瓦西里公爵分外高兴似的。 -------- ①法语:我从来都不明白,娜塔莎竟然拿定主意嫁给这头邋遢的狗熊。十分愚蠢而荒唐。据说,还是个赌棍哩。 ②公爵,但他为人厚道。 ③法语:这是他的教子。 瓦西里公爵陷入了沉思,蹙起了额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心中明白,根据别祖霍夫的遗嘱来看,他怕她成为争夺财产的敌手,她赶快让他安心下来。 “如果不是我有真挚的爱心,对叔叔一片忠诚,”她说道,露出特别自信和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出“叔叔”这个词:“我熟悉他的性格,高尚而坦率,可是要知道,他身边尽是一些公爵小姐……她们都很年轻……”她低下头来,轻言细语地补充说道:“公爵,他是否履行了最后的义务,送了他的终?这最后的时刻多么宝贵啊!要知道,比这临终更糟的事是不会有的了,既然他的病情如此沉重,就必须给他准备后事。公爵,我们妇女辈,”她很温和地微微一笑,“一向就知道这些话应该怎样说哩。我务必要去见他一面。无论这件事使我怎样难受,可我养成了忍受痛苦的习惯。” 公爵显然已经明了,甚至在安内特·舍列尔举办的晚会上就已明了,很难摆脱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位夫人。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这次见面不会使他难受吧,”他说道,“我们就等到晚上好了。大夫们预告了危象。” “公爵,可是在这种时刻,不能等待啊。Pensez,ily va dusa lut de so name… Ah!c’est terrible,les devoirsd’unchr é tien…”① -------- ①法语:我想想看,这事情涉及他的灵魂的拯救……啊!这多么可怕,一个基督徒的义务…… 内室里的一扇门开了,一位公爵小姐——伯爵的侄女走出来了,显露出忧郁的冷淡的脸色,她腰身太长,和两腿很不相称。 瓦西里公爵向她转过脸来。 “哦,他怎么样了?” “还是那个样子。不管您认为怎样,这一阵喧嚣……”公爵小姐说道,回头望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便像望着一个陌生人拟的。 “Ah,chère,jenevousreconnaissaispas,”①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含着幸福的微笑,说道,她迈着轻盈而迅速的脚步向伯爵的侄女面前走去,“Jeviens dam ivenet jes ni sanaus poun vousai denasoi gnenmon oncle J’imagine,comlien vous aneg soug gent.”②她同情地翻着白眼,补充说道。 公爵小姐一言未答,甚至没有微微一笑,就立刻走出去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脱下了手套,摆出洋洋自得的姿态,在安乐椅里坐下来了,并请瓦西里公爵坐在她近旁。 “鲍里斯!”她微微一笑,对儿子说道,“我上伯爵叔叔那里去,我的朋友,你先到皮埃尔那里去,别忘记转告他,罗斯托夫家邀请他。他们请他用午饭。我想他去不成,是吗?” 她把脸转向公爵说道。 “正好相反,”公爵说道,看来他的心绪欠佳,“Jes erais tres content sivousme de bar ras sezdece jeune hom me……③他就在这里,伯爵一次也没有询问他的情况。” 他耸耸肩。堂倌领着这个年轻人下楼,从另一座楼梯上楼,到彼得·基里洛维奇那里去了。 -------- ①法语:啊,亲爱的,我没有认出您了。 ②法语:我来帮助您照料叔叔。我想象得到,你够辛苦的了。 ③法语:如果您能够使我摆脱这个年轻人,那我就会感到非常高兴…… ------------------ 13 皮埃尔在彼得堡始终没有给自己选择一门职业,他确因滋意闹事被驱逐到莫斯科去。有人在罗斯托夫家叙述的那则故事合乎事实。皮埃尔参与了一起捆绑警察分局局长和狗熊的案件。他在几天前才回来,像平日一样,呆在父亲住宅里。虽然他推想,他的这段历史,莫斯科已经家喻户晓。他父亲周围的那些太太一向对他不怀好意,她们要借此机会使他父亲忿怒。但是在他抵达的那天,他还是到他父亲的寓所去了。他走进公爵小姐平时驻足的客厅,向用绷子绣花和读书(她们之中有一人正在朗读一本书)的几个小姐打招呼。她们共有三个人。年长的小姐素性好洁,腰身太长,面部表情过分严肃,她就是到过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家里串门的姑娘,她在朗读一本书;两个年幼的小姐脸颊粉红,十分秀丽,她们之间的差异只是其中一位唇上长着一点使她显得更为美丽的胎痣,她们二人都用绷子绣花哩。她们会见皮埃尔,把他看作死人或鼠疫病人。年长的公爵小姐中断了朗读,默不做声地用恐惧的眼睛朝他瞟了一眼;那位年幼的公爵小姐,脸上没有胎痣,却流露出同样的表情;最年幼的小姐,脸上长着一点胎痣,天性活泼,滑稽可笑,她朝绷子弯下腰去,藏起了笑意,大概她已预见到即将演出一幕闹剧,这使她觉得可笑。她把绒线向下扯,弯下腰来,好像在识别图案似的,好不容易她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Bomjour,macousine,”皮埃尔说道,“Vousnemere Bcon nais sezpas?”① “我还记得很清楚,很清楚。” “伯爵的健康情况怎样?我能会见他吗?”皮埃尔像平日那样不好意思地问道,但并没有困窘不安。 “伯爵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遭受痛苦,似乎您试图使他在精神上遭受更大的痛苦。” “我能会见伯爵吗?”皮埃尔重复自己说过的话。 “嗯!……假如您想杀死他,杀掉他,那么您就能见他一面。奥莉加,走去看看,表叔喝的汤炖好了吗,时候快到了。”她补充说道,向皮埃尔表示,她们都很忙,正忙着安慰他父亲,显然他只是忙着让他父亲心痛。 奥莉加走出去了。皮埃尔站了片刻,望望那两个表妹,鞠了一躬,说道: “那我就到自己房里去好了。在能会面的时候,就请你们告诉我吧。” 他走出去了,身后传来那个长有胎痣的表妹的洪亮悦耳、但却低沉的笑声。 翌日,瓦西里公爵来了,他在伯爵家里落歇。他把皮埃尔喊到身边,对他说道: “Moncher,sivousvousconduisezici,commeà Péters beurg,vous fi ni rez très mal;c’est tout ceque jevous dis,②伯爵的病情很严重,很严重;你根本用不着和他见面。” -------- ①法语:表妹,您好,您不认识我了? ②法语:我亲爱的,假如您在这里也像在彼得堡那样行为不正当,结果会弄得很糟,这是真话。 从那时起,大家不再打扰皮埃尔了,他孑然一人整天价呆在楼上自己房里。 当鲍里斯向皮埃尔房里走进来时,他正在房里来回踱方步,有时候在屋角里停步不前,对着墙壁做出威胁的手势,仿佛用长剑刺杀那看不见的敌人似的,他板起脸孔从眼镜上方向外张望,然后又开始踱来踱去,有时候口里喃喃地说着不清晰的话语,他耸耸肩,摊开两手。 “L’Angleterreavécu,”①他皱起眉头,用手指指着某人说道,“M.Pit tcom met rai tre à lana tionetau droit des gensest con dam né à…”②这时分他把自己想象为拿破仑本人,并随同英雄经历危险越过加来海峡,侵占了伦敦,但他尚未说完处死皮特这句话时,忽然看见一个身材匀称、面目俊秀、向他走来的青年军官。他停步了。皮埃尔离开鲍里斯时,他才是个十四岁的男孩,皮埃尔简直记不得他了,尽管如此,皮埃尔还是现出他所特有的敏捷而热情的样子,一把握住鲍里斯的手,脸上含着友善的微笑。 -------- ①法语:英国完蛋了。 ②法语:皮特是个背叛民族、出卖民权的败类,要判处…… “您记得我吗?”鲍里斯面露愉快的微笑,心平气和地说道,“我和我母亲来找伯爵,可是他好像身体欠佳。” “是啊,他好像身体欠佳。人家老是打扰他。”皮埃尔答道,竭力地追忆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何人。 鲍里斯觉得,皮埃尔不认识他了,但他认为用不着说出自己的姓名,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丝毫不觉得困惑不安。 “罗斯托夫伯爵请您今天到他家去用午饭。”他在相当长久的使皮埃尔觉得很不自在的沉默后说道。 “啊!罗斯托夫伯爵!”皮埃尔高兴地说道,“伊利亚,那末,您就是他的儿子罗?您可以想想,我头一眼没有把您认出来呢。您还记得我们和m-meJacquot①乘车上麻雀山吗?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啊。” -------- ①法语:雅科太太。 “您搞错了,”鲍里斯露出不同凡俗的略带讥讽的微笑,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是鲍里斯,是叫做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的儿子,罗斯托夫的父亲叫做伊利亚,他儿子叫做尼古拉。我可不认识什么雅科太太。” 皮埃尔挥了挥手,晃了晃脑袋,好像有蚊蚋或蜜蜂向他袭来似的。 “哎,是怎么回事啊!我把什么都搞混了。有这么许多莫斯科的亲戚!是的,您是鲍里斯……嗯,我们说得有个头绪了。喂,您对布伦远征有什么看法呢?只要拿破仑渡过海峡,英国人就要遭殃了,是吗?我想,远征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愿维尔纳夫不要出漏子!” 布伦远征的事,鲍里斯一无所知,他不看报,还是头一次听到维尔纳夫这个人物。 “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莫斯科,对午宴和谗言比对政治更为关心,”他用那平静的讥讽的语调说道,“这事情,我一无所知,心里也不去想它。莫斯科最关心的是谗言,”他继续说道,“眼下大家都在谈论您,谈论伯爵哩。” 皮埃尔露出善意的微笑,好像他惧怕对方会说出什么使他本人懊悔的话。但是鲍里斯一直盯着皮埃尔的眼睛,他说话时,听来令人信服,但却索然乏味。 “莫斯科除开散布流言飞语而外,再也没有事情可干了,”他继续说道,“大家都在关心,伯爵会把财产留给什么人,不过他可能比我们大家活得更长,这就是我的衷心的祝愿……” “说得对,这真够呛,”皮埃尔随着说起来,“真是够呛。”皮埃尔老是害怕这个军官会出乎意外地热衷于一场使他本人感到尴尬的谈话。 “您必定以为。”鲍里斯有点涨红了脸,说道,但没有改变嗓音和姿态,“您必定以为,大家关心的只是从富翁那里得到什么东西。” “真是这样。”皮埃尔思忖了一会。 “为了要避免误解,我正想把话对您说,假如您把我和我母亲都算在这类人之列,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虽然很贫穷,但我至少要替自己说话;正是因为您父亲很富有,我才不把自己看成是他的亲戚,无论是我,还是我母亲,我们永远也不会乞讨他的任何东西,也不会接受他的任何东西。” 皮埃尔久久地不能明白,但是当他明白了,他就从沙发上飞快跳起来,以他那固有的敏捷而笨拙的动作一把托住了鲍里斯的手臂;这时分他比鲍里斯的脸红得厉害多了,满怀着又羞愧又懊悔的感情说起话来: “这多么古怪!我难道……可谁又会去想呢?……我十分清楚……” 可是鲍里斯又把他的话打断了: “我把话全部说出来了,我觉得非常高兴。您也许会不乐意,就请您原谅我吧。”他说道,不仅不让皮埃尔安慰他,他反而安慰皮埃尔,“但是我希望,我不会使您受到屈辱。我的规矩是坦率地把话说干净……我应该怎样转达呢?您去罗斯托夫家吃午饭吗?” 鲍里斯显然推卸了沉重的责任,自己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却又使别人处于那种境地,于是他又变得非常愉快了。 “不,请您听我说吧,”皮埃尔心平气和地说道,“您是个不平凡的人。您方才说的话很不错,很不错。不消说,您不认识我了。我们许久不见面了……那时候还是儿童呢……您可以把我推测一番……我心里明白,十分明白。如果我缺乏勇气,这件事我就办不成啊,可是这棒极了。我和您认识了,我觉得非常高兴。说来真奇怪,”他沉默片刻,面露微笑地补充了一句,“您把我推测成什么样子!”他笑了起来。“也罢,这没有什么,那怎样呢?我们以后会认识得更加透彻的。就这样吧。”他握握鲍里斯的手。“您是否知道,伯爵那儿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哩。他没邀请我……我怜悯他这个人……可是有什么法子呢?” “您以为拿破仑会派军队越过海峡吗?”鲍里斯面露微笑地问道。 皮埃尔心里明白,鲍里斯想要改变话题,于是答应他了,开始诉说布伦远征之事的利与弊。 仆役走来呼唤鲍里斯去见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快要走了。皮埃尔答应来用午饭,为了要和鲍里斯亲近起来,他紧紧地握着鲍里斯的手,透过眼镜温和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离开以后,皮埃尔又在房间里久久地踱着方步,他再也不用长剑去刺杀那个望不见的敌人了;当他回想起这个聪明可爱、性格坚强的年轻人时,脸上微露笑容。 正像青春时期的人,尤其是像独居之时的人那样,他对这个年轻人抱着一种无缘无故的温情,他起誓了,一定要和他做个朋友。 瓦西里公爵送走公爵夫人。公爵夫人用手巾捂着眼角,她泪流满面。 “这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她说道,“无论我花费多大的代价,我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我准来过夜。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不管。每瞬间都很宝贵啊。我真不明白,公爵小姐们干嘛要磨磨蹭蹭。也许上帝会帮助我想出办法来给他准备后事……Adieu,mon prince,que leb on Di eu vous soutien ne……”① “Adieu,mabonne,”②瓦西里公爵答道,一面转过脸去避开她。 -------- ①法语:公爵,再见吧,但愿上帝保佑您…… ②法语:我亲爱的,再见吧。 “唉,他的病势很严重,糟糕透了,”当母亲和儿子又坐上四轮轿式马车时,母亲对儿子说道,“他几乎什么人也认不得了。” “妈妈,我不明白,他对皮埃尔的态度怎样?”儿子问道。 “遗嘱将说明一切,我的亲人,我们的命运以它为转移……” “可是您为什么认为,他会把点什么东西留给我们呢?” “唉,我的朋友!他那么富有,可我们却这么穷!” “嘿,妈妈,这还不是充分的理由啊。” “哎呀,我的天!我的天!他病得多么厉害啊!”母亲悲叹地说道。 ------------------ 14 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偕同儿子乘车去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家时,叫做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用手巾捂着自己的眼睛,她独自端坐良久,而后按了一下铃。 “亲爱的,您怎么啦,”伯爵夫人对强迫自己等候片刻的婢女气忿地说道,“您不愿意服务,是不是?那我就替您另找活儿做。” 伯爵夫人的女友极为痛苦,一贫如洗,忍屈受辱,伯爵夫人感到伤心,因此情绪不佳,每逢这种情形,她总是借用“亲爱的”和“您”称呼婢女,以示心境。 “我有过错,夫人。”婢女说道。 “请伯爵到我这里来。” 伯爵踉踉跄跄地向妻子跟前走来,像平时一样,脸上露出一点愧悔的样子。 “啊,伯爵夫人!sautéaumadère①炒花尾榛鸡,非常可口,machene!我尝了一下。买塔拉斯卡没有白花一千卢布,值得!” -------- ①法语:调味汁加马德拉葡萄酒。 他坐在妻子身旁,豪放地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斑白的头发给弄得蓬乱。 “我的伯爵夫人,有什么吩咐?” “我的亲人,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里怎么弄脏了?”她用手指着他的西装背心说道,“这是调味汁,说真的,”她面露微笑,补充了一句,“听我说,伯爵,我要钱用。” 她的脸上露出愁容。 “啊,我的伯爵夫人!……”伯爵忙乱起来了,取出钱夹子。 “伯爵,我要很多钱,我需要五百卢布。”她掏出细亚麻手绢,揩丈夫的西装背心。 “马上,马上。喂,谁在那里呀?”他吼道,只有在他深信被呼唤的人会迅速应声而来的情况下,才用这样的嗓门呼喊,“喊米坚卡到我这儿来!” 米坚卡是在伯爵家受过教育的贵族的儿子,现在主管伯爵家里的事务,这时他脚步轻盈地走进房里来。 “亲爱的,听着,”伯爵对那走进来的恭恭敬敬的年轻人说道,“你把……给我拿来,”他沉思起来,“对,七百卢布,对。你要小心,像上次那样破破烂烂的肮肮脏脏的不要拿来,给伯爵夫人拿些好的纸币来。” “米坚卡,对,请你拿干净的纸币,”伯爵夫人忧郁地呼气,说道。 “大人,您吩咐什么时候拿来?”米坚卡说道,“您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请您放心,”他发现伯爵开始急促地、困难地呼吸,向来这是他开始发怒的征候,于是补充了一句,“我几乎置之脑后了……您吩咐我马上送来吗?” “对,对,就是这样,送来吧。要交给伯爵夫人。” “这个米坚卡是我的金不换,”当年轻人走出门去,伯爵微笑着,补充一句话,“没有什么‘行不通’的事。‘行不通’这样的说法我可忍受不了啊。什么事都行得通。” “唉,伯爵,重钱,贪钱。金钱引起了人世间的多少悲伤!” 伯爵夫人说道,“我可很需要这笔钱。” “我的伯爵夫人,您是个出了名的爱挥霍的女人。”伯爵说道,吻吻妻子的手,又走回书斋去了。 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离开别祖霍夫又回到家里时,那笔钱用手绢盖着,搁在伯爵夫人身边的茶几上,全是崭新的钞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发现,伯爵夫人不知为何事扫兴起来。 “喂,我的朋友,怎么样了?”伯爵夫人问道。 “唉,他的病势十分恶劣!真没法认出他是谁了,他的病情太严重,太严重。我呆了一下子,竟没有说出两句话……” “安内特,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拒绝我吧,”伯爵夫人忽然说,面红耳赤,这在她那瘦削、庄重、中年人的面孔上显得十分古怪。这时候,她从手帕下面掏出钱来。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霎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弯下腰去,好在适当的瞬间巧妙地拥抱伯爵夫人。 “这是我给鲍里斯缝制军装的钱……”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面拥抱她,一面哭泣起来。伯爵夫人也哭起来了。她们之所以哭泣,是因为她们和睦相处,她们待人都很仁慈,她们是青春时代的朋友,她们现在关心的竟是卑鄙的东西——金钱;她们之所以哭泣,还因为她们的青春已经逝去了……可是从这两人的眼里流下的倒是愉快的眼泪…… ------------------ 15 叫做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随同几个女儿陪伴着许多客人坐在客厅里。伯爵把几位男客带进书斋去,让他们玩赏他所搜集的土耳其烟斗。他有时候走出来,问问大家:“她来了没有?”大伙儿正在等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上流社会中绰号叫做leterribledragon①的夫人,她之所以大名鼎鼎,并不是由于财富或荣耀地位,而是由于心地正直,待人朴实的缘故。皇室知道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整个莫斯科和整个彼得堡都知道她。她使这两个城市的人感到惊奇,他们悄悄地讥笑她的粗暴,谈论她的趣闻。但是人人都一无例外地尊敬她,而且畏惧她。 -------- ①法语:恐龙。 书斋里烟雾弥漫,大家正在谈论文告中业已宣布的战争和征兵事宜。谁也还没有读到上谕,但是人人都知道业已颁布了。那伯爵坐在一面抽烟,一面交谈的两位邻近的客人之间的土耳其式沙发上。伯爵自己不抽烟,也不开口说话,可是他时而把头侧向这边,时而侧向那边,显然他在留意地观看这两位抽烟的客人,静听被他惹起的两位邻座的讧争。 交谈者之中一人是文官,那布满皱纹、瘦削的面部刮得很光,带着易动肝火的神态,他已经趋近老年,但穿着像个挺时髦的年轻人。他盘着两腿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那模样跟户主家里人不相上下,他的嘴角上深深地叼着一根琥珀烟嘴子,一面眯缝起眼睛,若断若续地抽烟。这位客人是老光棍,伯爵夫人的堂兄,莫斯科的沙龙中常常议论他,都说他是个造谣中伤的人。他对交谈者,似乎会装作屈尊俯就的样子。另一位客人长着一张白里透红的面孔,精神焕发,是个近卫军军官,他梳洗得整齐清洁,扣上了衣扣,嘴中叼着一根琥珀烟嘴子,用那粉红的嘴唇轻轻地吸烟,从美丽的嘴中吐出一个个烟圈来。他就是谢苗诺夫兵团的军官贝格中尉,鲍里斯和他一起在这个兵团入伍。娜塔莎逗弄过薇拉——伯爵夫人的长女,将贝格称为她的未婚夫。伯爵坐在他们之间,全神贯注地听着。除开他所酷爱的波士顿牌戏之外,倾听大家争论,是一件使他至为愉快的事,尤其是当他在两个喜爱聊天的人中间引起争论的时候,他就觉得更加高兴了。 “老兄,怎么啦,montrèshonoraole①阿尔万斯·卡尔雷奇,”申申说道,微微一笑,他把民间最通俗的俄文语句和优雅的法文句子混杂在一起,这也就是他说话的特点,“Vous com pte zvous faire desrentes surl’etat②,您想获得连队的一笔收入吗?” -------- ①法语:可尊敬的。 ②法语:您想获得政府的一笔收入。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表白一下,骑兵服役的收益比步兵服役要少得多,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请您设想一下我现在的处境吧。” 贝格说起话来总是十分准确、心平气和,态度很谦恭,他的谈话向来只是关系到他个人的私事,每当他人谈论的事情和他没有直接关系时,他便沉默不言。他能这样接连几个小时默不作声,一点也不觉得忸怩不安,而且不让他人产生这种感觉。可是交谈一提到他本人,他就长篇大论地说起来,明显地露出喜悦的神色。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如果我在骑兵部队服役,那怕是挂中尉军衔,在四个月之内我所挣的钱也不会超过两百卢布,现在我已挣到两百三十卢布。”他说道,脸上露出洋洋得意的令人喜悦的微笑,一面回头看看申申和伯爵,仿佛他的成就永远是其他一切人共同期望的主要目标,他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除此之外,我调到近卫军以后,现在就崭露头角了,”贝格继续说道,“近卫军的步兵里常有空缺。请您设想一下,靠这两百三十卢布,我怎么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呢。我要储存一些钱,还得寄一些给父亲。”他继续说道,一面吐出一个烟圈。 “Labalanceyest……①commeditleproverbe,②德国人用斧头背都能打出谷来。”申申说道,另一边嘴角上叼着一根烟嘴子,并且向伯爵丢了个眼色。 -------- ①法语:是真的…… ②法语:照谚语说。 伯爵哈哈大笑起来。其余的客人看见申申在谈话,都走到面前来听听。贝格对嘲笑和冷漠的态度都不注意,继续述说他调到近卫军后,军衔就高于中等军事学校的同学了,他讲在战时连长可能就义,而他在连队职位较高,能够轻而易举地当上连长,他又讲他在兵团里人人热爱他,他父亲对他非常满意。贝格谈论这一切,看来洋洋自得,似乎没有意料到,人家也会有自己的志趣。可是他讲得娓娓动听,不卑不亢,那种年轻人所固有的幼稚的自私心理暴露无遗,终于使听众无力反驳了。 “老兄,您不论在步兵服役,还是在骑兵服役,到处都有办法,这就是我对您的预言。”申申说道,拍拍他的肩膀,把脚从土耳其式沙发上放下来。 贝格喜悦地微微一笑。伯爵和跟随在他身后的客人,都向客厅走去。 午宴前还有一小段时间,前来聚会的客人都已就坐,等候吃小菜,他们还没有开始长谈,但是同时却又认为必须活动一下,而且用不着默不作声,以此表示他们根本不急于就坐。主人们隔一会儿望一下门口,有时候彼此看一眼。客人们就凭这种眼神来竭力猜度,主人们还在等候谁,或者等候什么,是等候迟迟未到的高贵亲戚呢,还是等候尚未煮熟的肴馔。 皮埃尔在临近午宴时来到了,他在客厅当中随便碰到的一把安乐椅上不好意思地坐着,拦住大家的络。伯爵夫人想要他说话,但是他戴着眼镜稚气地向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某人似的,他简短地回答伯爵夫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的样子羞羞涩涩,只有他一人觉察不出来。大部分客人都晓得他耍狗熊闹出的丑闻,因此都出于好奇心看看这个长得高大的胖乎乎的忠厚人,心里都疑惑这个谦虚的笨伯怎么会戏弄警察分局局长呢。 “您是不久以前回国的吗?”伯爵夫人问他。 “Oui,madame.”①他向四面打量,答道。 “您没有看见我丈夫吗?” “Non,madame.”②他不适时地微微一笑。 “您不久以前好像到过巴黎?我想这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伯爵夫人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互使眼色。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心中明白,这是人家要她来接待这个年轻人,她于是就坐在他的近旁,开始提到他的父亲的事;他如同回答伯爵夫人一样,只用三言两语来回答她的话。客人们彼此正忙于应酬。 “LesRazoumovsky… caaétécharmant… Vousêtesbien bon ne… La com tes se Aprak sine… ”③四面传来了话语声。伯爵夫人站起身来,向大厅走去了。 -------- ①法语:夫人,是,是,是。 ②法语:夫人,还没有,没有。 ③法语:拉祖莫夫斯基家里的人……太好了……这太好了……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 “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吗?”大厅里传来了她的声音。 “正是她。”听见有一个女人嗓音刺耳地回答。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应声随即走进房里来。 小姐们、甚至夫人们,年迈的女人除外,都站立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门口停步了,她身材十分肥胖,高大,这个五十岁的太太高高地抬起长满一绺绺斑白鬈发的头,环顾了一下客人,不慌不忙地弄平连衣裙的宽大的袖子,好像要卷起自己的袖子似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向来都说俄国话。 “祝贺过命名日的亲爱的夫人和儿童们,”她说道,声音洪亮而圆浑,盖过了其他声音,“你这个老色鬼,怎么样了,“她把脸转向正在吻着她的手的伯爵说道,“你在莫斯科大概觉得无聊吧?没有地方可以追逐猎犬了吧?但是毫无办法啊,老爷,你瞧瞧这些小鸟儿都要长大了……”她用手指着几个姑娘说道,“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应该给她们找个未婚夫。” “我的哥萨克,怎么样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娜塔莎叫做哥萨克。)她说道,用手抚摩着毫无惧色、欢欢喜喜走来吻她的手的娜塔莎,“我知道这个姑娘是个狐狸精,可是我还喜爱她。” 她从女式大手提包里取出一双梨形蓝宝石耳环,送给两颊粉红、喜气洋洋的过命名日的娜塔莎,之后立即转过脸去避开她,对皮埃尔说话。 “嗨,嗨,亲爱的!到这里来,”她用假装的尖声细语说道,“亲爱的,来吧……” 她现出威吓的样子把衣袖卷得更高了。 皮埃尔走到面前来了,他透过眼镜稚气地望着她。 “亲爱的,到我跟前来,到我跟前来!当你父亲有权有势的时候,只有我这个人才对他说真心话,对于你呢,我听凭上帝的吩咐,也这样做就是。” 她沉默一会儿,大家都不开腔,等待着就要发生什么事,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场白而已。 “这孩子好嘛,没有什么话可说!这孩子好嘛!……他父亲躺在病榻上,他却寻欢作乐,竟然把警察分局局长捆在狗熊背上。我的天,真不要脸,真不要脸!去打仗好了。” 她把脸转了过去,向伯爵伸出一只手来,伯爵险些儿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好吧,我看差不多要就座了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启程前行,骠骑兵上校领着伯爵夫人尾随其后,上校是个合乎时代需要的能人,他要和尼古拉一道去追赶已经开拔的团队。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申申搓成一对了。贝格向薇拉伸出手来,做出亲热的姿态。笑容可掬的朱莉·卡拉金娜和尼古拉一同走向餐桌,准备入座。其他一些成对的男女跟随在他们后面。沿着大厅鱼贯而行。儿童和男女家庭教师不结成一对,作为殿后。堂倌都忙碌起来,椅子碰撞得轧轧作响,乐队奏起合唱曲,客人入席就座了。刀叉的铿锵声、客人的说话声、堂倌轻盈的步履声替代了伯爵家庭乐队的奏鸣声。伯爵夫人坐在餐桌一端的首席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坐在右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其他女客坐在左边。伯爵坐在餐桌的另一端,骠骑兵上校坐在左边,申申和其他男客坐在右边。年纪较大的年轻人坐在长餐桌的一旁;薇拉和贝格并排而坐,皮埃尔和鲍里斯并排而坐;儿童和男女家庭教师坐在另一旁。伯爵从水晶玻璃器皿、酒瓶和水果盘后不时地望望妻子和她那系着蓝色绸带的高高翘起的寝帽,亲热地给邻座斟酒,但也没有把自己忘记。伯爵夫人并没有忘记她这个主妇应尽的责任,也向她丈夫投以意味深长的目光,她似乎觉得丈夫的秃头和面庞在苍苍白发的强烈对照下,显得红透了。在妇女就座的餐桌一端,传来均匀的嘟哝声,在男人就坐的另一端,说话声越来越响亮,尤其是那个骠骑兵上校的嗓音如雷贯耳,他吃得多,喝得多,脸红得越来越厉害,伯爵把他看作客人的模范。贝格面露温和的微笑,正和薇拉谈到,爱情并非是世俗的感情,而是纯洁的感情。鲍里斯向他自己的新相识说出餐桌上客人的姓名,并和坐在对面的娜塔莎互使眼色。皮埃尔寡于言谈,不时地瞧瞧陌生的面孔,他吃得太多了。从那两道汤中他所挑选的alatortue①和大馅饼,直到花尾榛鸡,他何尝放过一道菜。当那管家从邻座肩后悄悄地端出一只裹着餐巾的酒瓶,一边说:“纯马德拉葡萄酒”,“匈牙利葡萄酒”,或“莱茵葡萄酒”时,他何尝放过一种葡萄酒。每份餐具前面放着四只刻有伯爵姓名花字的酒樽,皮埃尔随便拿起一只酒樽,高高兴兴地喝酒,一面露出愈益快活的神态打量着客人。娜塔莎坐在对面,她正盯着鲍里斯,就像十三岁的姑娘两眼盯着头次接了吻的她所热恋的男孩那样。有时候她把同样的目光投在皮埃尔身上,但不知为什么,他在这个可笑的活泼的姑娘的目光逼视下真想笑出声来。 -------- ①法语:甲鱼汤。 尼古拉在朱莉·卡拉金娜身旁坐着,离索尼娅很远。他又面露情不自禁的微笑和她说些什么话。索尼娅含着微笑,摆出很大的架子,但显而易见,她深受醋意的折磨,脸上时而发白,时而发红,聚精会神地谛听尼古拉和朱莉之间的谈话。一位家庭女教师心神不安地环顾四周,仿佛倘若有人想要凌辱儿童,她就要给予反击似的。一名德国男家庭教师极力记住种种肴馔,甜点心以及葡萄酒,以便在寄往德国的家信中把这全部情形详尽地描述一下。当那管家拿着裹有餐巾的酒瓶给大家斟酒时,竟把他漏掉了,他简直气忿极了。他愁眉苦脸,力图表示他不想饮这种葡萄酒。他所以恼火,是因为谁也不了解,他喝酒不是解渴,也不是贪婪,而是由于一种真诚的求知欲所致。 ------------------ 16 在男客就座的餐桌的一端,谈话变得越来越热烈了。上校已经讲到,彼得堡颁布了宣战文告,他亲眼看见的一份文告已由信使递交总司令了。 “真见鬼,我们干嘛要和波拿巴作战?”申申说道,“Iladé jàra bat tule ca quet à l’au triche, Jecrains quecet te foisce ne soitno tre towr。”① -------- ①法语:他已经打掉了奥地利的威风,我怕现在要轮到我们了。 上校个子高大,长得很结实,是个活泼好动的德国人,老军人和爱国者。申申的话使他生气了。 “为什么,阁下,”他说道,把母音“唉”发成“爱”,把软音发成硬音,“皇帝知道这件事。他在文告中说道,不能对俄国遭受威胁而熟视无睹,不能对帝国的安全、它的尊严和盟国的神圣权利遭受威胁而熟视无睹,”他说道,不知怎的特别强调“盟国的”这个词,好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他凭藉他那正确无讹的记忆公文的天赋,把文告中的引言重说了一遍:“……国王的意愿,他唯一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乃是: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奠定欧洲的和平,现已拟定调遣部分军队出国,再度竭尽全部力量以企臻达此一目标。” “阁下,这就是为了什么。”他说了一句收尾的话,露出教训人的神态,一面喝完那杯葡萄酒,看看伯爵的脸色,想获得赞扬。 “Connaissezvousleproverbe,①‘叶廖马,叶廖马,你不如坐在家中,把你的纺锤磨平。”“申申蹙起眉头,微露笑容,说道,“Celanous convientàmer veil le,②苏沃洛夫顶什么用,他也被打得àplatecouture③,目前我们苏沃洛夫式的人物在哪里呢?Je vous deman deun peu.”④他说道,不断地从俄国话跳到法国语。 -------- ①法语:您知道这句谚语。 ②法语:这对于我们非常适宜。 ③法语:落花流水。 ④法语:我要问您。 “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上校用手捶桌子,说道,“为皇帝献身,一切才会亨通。尽可能少地(在“可能”这个词上他把嗓音拖得特别长),尽可能少地议长论短,”他把话说完了,又朝伯爵转过脸来,“这就是我们老骠骑兵的论点,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年轻人和年轻的骠骑兵,您怎样评论呢?”他把脸转向尼古拉,补充一句话。尼古拉听到话题涉及战争后,便丢开对方不管,睁大两眼,全神贯注地谛听上校说话。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尼古拉答道,他面红耳赤,一面转动着盘子,挪动着几只酒杯,脸上露出坚决的无所顾忌的神情,好像他眼前遭受到严重的危险似的,“我深信,俄国人都要为国捐躯,或者会赢得胜利。”他说道。正如其他人在这种时分说出过分激动的不是恰如其分的话那样,他也有同样的感受。 “C’estbienbeaucequevousvenezdedire.”①朱莉坐在他身旁叹息道。当尼古拉说话时,索尼娅全身颤抖起来,脸红到耳根,从耳根红到脖子,从脖子红到肩膀。皮埃尔谛听上校说话,点点头,表示赞同。 -------- ①法语:很好!您说得很好。 “这么说真好。”他说道。 “地道的骠骑兵,年轻人。”上校又捶了一下桌子,嚷道。 “你们在那里吵什么?”忽然从餐桌那边传来玛丽亚·德米特罗耶夫娜低沉的语声。“你为什么要捶桌子呢,”她把脸转向骠骑兵说道,“你对什么人动肝火?你真的以为现在你面前就有一群法国人!” “我说的是真话。”骠骑兵面露微笑说道。 “老是说战争,”伯爵从餐桌那边嚷道,“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要知道,我的儿子要去作战了,儿子要去作战了。” “我有四个儿子,都在军队里服役,我并不忧虑。一切都由上帝支配:你是躺在灶台上死去;还是在战斗中得到上帝的保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从餐桌的那端用浑厚的嗓音毫不费劲地说道。 “真是这样。” 谈话又集中火力了——女士在餐桌的一端,男子汉在餐桌的另一端。 “你问不到什么,”小弟弟对娜塔莎说道,“你问不到什么!” “我一定要问。”娜塔莎答道。 她的脸红起来了,表现出无所顾忌的欢快的果断。她欠身起来一下,向坐在对面的皮埃尔投以目光,请他仔细听着,又向母亲转过脸去说话。 “妈妈!”整个餐桌都听见她的低沉洪亮的童音。 “你干嘛?”伯爵夫人惊恐地问道,但她凭女儿的脸色看出她在胡闹,就向她严肃地挥挥手,摇摇头,装作威吓和遏制的样子。 谈话暂时停止了。 “妈妈!有什么蛋糕?”娜塔莎脱口说出这句话,她的嗓音听来更坚定。 伯爵夫人想蹙起眉头,可是她没法蹙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伸出她那肥胖的指头,威吓她。 “哥萨克!”她用威吓的口气说。 大多数客人都望着长辈,不知道应当怎样应付这场恶作剧。 “瞧我收拾你!”伯爵夫人说。 “妈妈!有蛋糕吃吗?”娜塔莎已经大胆任性、欢快地嚷起来,她事先确信,她的恶作剧会大受欢迎。 索尼娅和胖乎乎的彼佳笑得躲藏起来,不敢抬头。 “你瞧,我不是问了。”娜塔莎对小弟弟和皮埃尔轻言细语地说,她又向皮埃尔瞥了一眼。 “冰激凌,只是人家不给你。”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娜塔莎明白,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此她也不害怕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什么样的冰激凌?我不爱吃奶油冰激凌。” “胡萝卜冰激凌。” “不是的,什么样的冰激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什么样的冰激凌?”她几乎叫喊起来。“我想知道啊!”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伯爵夫人都笑了起来,客人们也都跟着笑起来。大家不是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回答觉得好笑,而是对这个女孩百思不解的大胆和机智觉得好笑,她居然有本事、有胆量这样对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当人家告诉娜塔莎,快要摆上菠萝冰激凌时,她才不再纠缠了。端出冰激凌之前,先端出香槟酒。乐队又开始奏乐,伯爵吻了一下伯爵夫人,客人都站立起来,向伯爵夫人道贺,隔着桌子跟伯爵碰杯,跟孩子们碰杯,并互相碰杯。堂倌忙碌起来了,又跑来跑去,可以听见椅子碰撞的响声,客人们的两颊显得更红了,又依照原先的顺序走回客厅,走回伯爵的书斋。 ------------------ 17 玩波士顿纸牌的大牌桌摆开了,牌局也都凑成了,伯爵的客人们在两个厅里就座,一间是摆有沙发的休息室,一间是图书室。 伯爵把纸牌铺成扇面形,好不容易才改变午睡的习惯,他对着大家露出一张笑脸。伯爵夫人诱使年轻人聚集在击弦古铜琴和竖琴的近旁。朱莉在大家的请求下头一个用竖琴弹奏了一首变奏短曲,她和其余的女孩一块邀请素以音乐天赋出名的娜塔莎和尼古拉唱一首什么歌。大家像对待大人那样对待娜塔莎,她因此显得十分高傲,但同时有几分胆怯。 “我们唱什么?”她问道。 “《泉水》。”尼古拉答道。 “喂,快点。鲍里斯,到这里来吧,”娜塔莎说道,“索尼娅究竟到哪里去了?” 她向四周环顾,看见她的朋友不在房里,便跑去寻找她了。 娜塔莎跑进索尼娅房里,找不到她的女友,便跑到儿童室去了,那里也没有索尼娅的人影。娜塔莎明白,索尼娅呆在走廊里的箱笼上。走廊里的箱笼是罗斯托夫家年轻妇女们倾吐哀愁的地方。诚然,索尼娅呆在箱笼上,俯卧在保姆那张邋遢的条纹绒毛褥子上,她身上穿的粉红色的薄纱连衣裙都给揉皱了。她用手蒙着脸,哽噎得大声痛哭,赤裸裸的肩膀不住地颤抖。娜塔莎整天价因为过命名日而喜形于色,这时分脸色突然变了,她的视线呆滞不动了,之后她的宽大的脖子颤抖了一下,嘴角松垂下来了。 “索尼娅,你怎么样?……您是怎么回事?呜——鸣—— 呜!……” 娜塔莎咧开大嘴哭起来了,样子变得十分难看,她像儿童似地嚎啕大哭,不知为什么,只是因为索尼娅哭泣的缘故。索尼娅想要抬起头来,想回答她的话,可是没法这样办,她把头藏得更深了。娜塔莎哭着,在蓝色的绒毛褥子上坐下,一面拥抱着女友。索尼娅鼓足一股劲,欠起身子,揩掉眼泪,开始述说起来。 “过一个礼拜尼古连卡要去打仗了,他的……公文……下达了……他亲自对我说了……我并不想哭哩……”她让娜塔莎看看她拿在手里的一张纸条,那是尼古拉写的诗句,“我并不想哭哩,可是你没法了解……谁也没法了解……他的心肠多么好啊。” 她于是又哭起来,哭他的心肠太好。 “你觉得挺好……我不妒嫉……我爱你,也爱鲍里斯,”她聚精会神地说道,“他是个可爱的人……对你们毫无妨碍。可是尼古拉是我的表兄……有必要……总主教本人允准……即使那样也不行。而且,若是妈妈(索尼娅认为伯爵夫人是母亲,把她称呼为母亲)……她说我断送尼古拉的锦绣前程,我没有好心眼我忘恩负义,说实话……真的……”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我这样爱她,也爱你们大家,唯独薇拉……为什么?我有什么对她过不去呢?我十分感谢你们,我乐于为你们牺牲一切,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 索尼娅不能再往下说了,又托着头,埋进绒毛褥子里。娜塔莎安静下来了,但是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她心里明白她朋友的苦衷是何等沉重。 “索尼娅,”她忽然说道,仿佛猜中了表姐伤心的真实原因,“薇拉在午饭后大概对你说过什么话?是吗?” “是的,尼古拉本人写了这些诗,我还抄了一些别的诗;她在我桌上发现了,还说要把它拿给妈妈看,说我忘恩负义,说妈妈决不会容许他娶我为妻,他要娶朱莉为妻。你看见,他整天价同她在一块吗?……娜塔莎!这是为什么?……” 她又哭了起来,显得比原先更悲伤了。娜搭莎帮助她欠起身来,拥抱她,透过眼泪微露笑容,开始安慰她。 “索尼娅,我亲爱的,不要相信她,不要相信啊。你总还记得我们和尼古拉三人在摆满沙发的休息室里说的话吧,是在晚饭后,你还记得吧?我们不是拿定了主意,把日后的事情划算好了吗?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是你总还记得事事都美满,事事都亨通。你看申申叔叔的兄弟娶他的表妹为妻,而我们不就是堂表子妹嘛,鲍里斯也说过完全可以这样做嘛。你知道,什么事我都对他说了。他既聪明,而又善良,”娜塔莎说道……“索尼娅,我亲爱的,你不要哭,索尼娅,我的心肝。”她一面吻她,一面发笑。“薇拉真凶恶,去她的吧!事事都会好起来,她也决不会告诉***妈的。尼古拉倒会亲口把话说出来,至于朱莉嘛,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她。” 她于是吻她的头。索尼娅稍微抬起身子来,那只小猫也活跃起来了,一双小眼睛闪闪发光,它好像就要摇摇尾巴,伸出四双柔软的脚爪霍地跳起来,又要去玩耍线团,好像它适宜于这种游戏似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说的是实在的话?真的?”她说道,一面飞快地弄平连衣裙和头发。 “说实话吗?真的吗?”娜塔莎答道,一面给她的朋友弄平辫子下面露出来的一绺粗硬的头发。 她们二人都笑了起来。 “喂,我们去唱《泉水》这首歌吧。” “我们去吧。” “你可知道,坐在我对面的这个胖乎乎的皮埃尔多么滑稽可笑!”娜塔莎停步时忽然说道,“我觉得非常快活!” 娜塔莎于是在走廊里跑起来了。 索尼娅拍掉身上的绒毛,把诗藏在怀里靠近突出的胸骨的脖子旁边,她两颊通红,迈着轻盈而快活的步子,跟在娜塔莎身后沿着走廊向摆满沙发的休息室跑去。年轻人应客人之请唱了一首人人喜欢的四人合唱曲《泉水》之后尼古拉还唱了一首已经背熟的歌曲: 在令人欣悦的晚上, 在皎洁月色映照下, 你想象这该是多么幸福: 有个什么人在这尘世上, 她心中暗自把你思念! 她那秀丽的巧手 拨弄着金色的竖琴, 竖琴激越的和音 把你召唤 召唤到身边! 还有一两天, 幸福的生活就要来临…… 唉,你的朋友 活不到那么一天! 他还没有唱完最后一句歌词,青年人就在大厅里准备跳舞,乐师们按照霍拉舞曲的节奏,把脚儿跺得咚咚响,这时传来他们的咳嗽声。 皮埃尔坐在客厅里,申申和这个从外国归来的皮埃尔谈论起使他觉得索然无味的政治范畴的事情,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和他们攀谈起来,当乐队开始奏乐时,娜塔莎步入客厅,她向皮埃尔身边径直地走去,两脸通红,含笑地说道:“妈妈吩咐我请您去跳舞。” “我怕会搞乱了舞步,”皮埃尔说道,“不过,假如您愿意当我的老师……” 于是他低低地垂下他那只肥胖的手,递给苗条的少女。 当一对对男女拉开距离站着、乐师正在调音律时,皮埃尔和他的小舞伴一同坐下来。娜塔莎觉得非常幸福:她和国外回来的大人跳过舞了。她在大家眼前坐着,像大人那样和他交谈。她手里拿着一把折扇,一位小姐让她拿去扇扇的。她装出一副地道的交际花的姿态(天知道她是何时何地学到的本领),她扇扇子,隔着折扇露出微笑,和她的舞伴交谈。 “她是啥模样?她是啥模样?你们看吧,你们看吧。”老伯爵夫人走过大厅,用手指着娜塔莎,说道。 娜塔莎两颊通红,笑了起来。 “妈妈,怎么啦?您何苦呢?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第三节苏格兰民间舞曲奏到半中间时,客厅里的坐椅被移动了,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大部分贵宾和老年人都在这里打纸牌,他们久坐之后伸伸懒腰,把皮夹和钱包放进衣袋里,一个个向大厅走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随同伯爵走在最前面,二人都现出喜悦的神色。伯爵诙谐地装出拘礼的样子,有点像跳芭蕾舞似的,把他那圆圆的手臂伸给玛丽亚·德米特罗耶夫娜。他挺直身子,神采奕奕,流露出特别洒脱的机智的微笑。一跳完苏格兰民间舞,他就向乐师击掌,面对第一提琴手,向那合唱队吼叫: “谢苗!你熟悉《丹尼拉·库波尔》么?” 这是伯爵青年时代喜欢跳的一种舞蹈。(《丹尼拉·库波尔》其实是英吉利兹舞的一节。) “瞧我爸爸吧。”娜塔莎朝着整个大厅嚷道(根本忘记了她在和大人一同跳舞),她把长有鬈发的头向膝盖微微垂下,非常洪亮的笑声响彻了厅堂。 诚然,大厅里的人都含着欢快的微笑打量那个愉快的老人,一个比他高大的显赫的女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站在他身旁,他那手臂蜷曲成圆形,合着拍子摇晃着,舒展开双肩,两脚向外撇开,轻盈地踏着拍子,他圆滚滚的脸上越来越眉开眼笑,让观众准备欣赏将要出现的场景。一当听见欢快的、引人入胜的、与快乐的《特烈帕克》舞曲相似的《丹尼拉·库波尔》舞曲,大厅的几个门口蓦然堆满了家仆的笑脸,一旁是男仆,一旁是女仆,他们都出来观看尽情作乐的老爷。 “我们的老爷!真是苍鹰啊!”保姆从一道门口高声地说道。 伯爵跳得很棒,而且心中有数,不过他的女舞伴根本不擅长跳舞,她也不想把舞跳好。她那硕大的身段笔直地站着,把两只强而有力的手臂低垂下去(她把女式手提包转交给伯爵夫人),只有她那副严肃、但却俊美的面孔在跳舞。伯爵的整个浑圆的身体是他外表上的特点,而越来越显得愉快的眉开眼笑的脸庞和向上翘起的鼻孔却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外貌特征。如果认为,伯爵跳得越来越痛快,他那出乎意料的灵活转动和脚步从容的轻盈跳跃会使观众心神向往,那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转身或踏拍子时,肩膀一动或者手臂一卷曲,就可轻而易举地产生同样良好的印象;虽然她的身躯过分地肥胖,态度素来严厉,每个观众仍然赞赏不已。舞跳得愈益热闹了。他们对面的别的舞伴一刻也没有引起观众的注意,而且也不介意这件事。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吸引着全体的注意力。在场的人们本来就目不转睛地望着跳舞的伴侣,可是娜塔莎却拉拉这个人袖子,扯扯那个人的连衣裙,要大家都来看看她爸爸。跳舞暂停时,伯爵吃力地喘气,向乐师们挥手喊叫,要他们快点奏乐。伯爵围绕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疾速地旋转,时而把脚尖踮起,时而把脚跟跺地,越来越矫捷,越来越勇猛,终于把舞伴领到她的坐位上,他把一只脚向后磴起来,低垂淌着热汗的头,这样才跳完了最后一个舞步,在洪亮的掌声和笑声中,尤其是在娜塔莎的哈哈大笑声中,他用右手挥动一下,腾空画了一个圆圈。两个跳舞的人停步了,吃力地喘气,用麻纱手巾揩汗。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跳舞啊,machère,”①伯爵说道。 “《丹尼拉·库波尔》真不错!”玛丽亚·德米特罗耶夫娜卷起袖子,久久地、吃力地喘气,说道。 -------- ①法语:老大娘。 ------------------ 18 当人们在乐师因困倦而弹奏走调的音乐伴奏下正跳第六节英吉利兹舞、疲乏的堂倌和伙夫正准备晚膳的时候,别祖霍夫伯爵第六次罹患中风病。大夫们宣布,他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了,有人给病人做了忏悔仪式和圣餐仪式,并且还做了涂圣油仪式的准备。平素在这种时刻,这所住宅里的人总是乱哄哄的,惶恐不安地期待。卖棺材的人都聚集在住宅大门外,遇有马车驶近,便躲到一边去,他们等着承做安葬伯爵的棺材,赚一笔大钱。莫斯科军区总司令不断派遣副官来打听伯爵的病情,这天晚上他亲自乘车前来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大官别祖霍夫伯爵作临终告别。 华美的接待室挤满了人。当军区总司令独自和病人一起呆了半小时左右,走出门来的时候,大家都肃然起敬地站立起来,他微微鞠躬答礼,想尽快地从凝视他的大夫、神职人员和亲戚身边走过去。这些日子里,瓦西里公爵显得消瘦,脸色苍白,他伴送着军区总司令,轻声向他反复地说着什么话。 瓦西里公爵送走军区总司令后,独自一人在大厅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把一条腿高高地架在另一条腿上,用臂肘撑着膝头,用手捂住眼睛。他这样坐了片刻,便站立起来,用惊恐的目光向四下环顾一番,不像惯常那样,他迈着急急匆匆的脚步,经过走廊,到住宅后院去找公爵的大小姐了。 在灯光暗淡的房间里,人们彼此窃窃私语,声音若断若续,每当有人从通往行将就木者的寝室门口进出,房门发出微弱响声时,人们就寂然无声,用那洋溢着疑问和期待的目光,望望那扇房门。 “人的命运,”一个年老的神职人员对坐在他近旁、稚气地听他说话的女士说道,“命是注定的,不可逾越的。” “我想,举行涂圣油仪式为时不晚吧?”这位女士补充说出神职人员的头衔,问道,仿佛她在这一点上毫无意见似的。 “大娘,这种圣礼仪式是很隆重的。”神职人员答道,一面用手摸摸那盖有几绺往后梳的斑白头发的秃顶。 “他究竟是谁?是军区总司令本人?”有人在房间的另一端问道,“他显得多么年轻啊!……” “六十多岁了!据说,伯爵已经认不得他了,是吗?大家想举行涂圣油仪式吗?” “有个人我可知道哩,他受过七次涂圣油礼了。” 公爵的二小姐从病人寝室里走出来,两眼泪痕斑斑,她在罗兰大夫身旁坐下,这位大夫用臂肘撑在桌子上,姿势优美地坐在叶卡捷琳娜画像下面。 “Tr’èsbeau,”大夫在回答有关天气问题时,说道,“trèsbeau, prin ces se,et puis, à Mos cou on se croi tà la com Bpagne.”① “N’est—ce—pas?”②公爵小姐叹息道,“可以让他喝水吗?” 罗兰沉思起来。 “他服了药吗?” “服过了。” 大夫看了看卜列格怀表。 “请您拿一杯开水,放进unepincée(他用那纤细的指头表示unepincée是什么涵义)de crem or tar tari……”③ -------- ①法语:很好——公爵小姐,天气很好,而且,莫斯科和乡下很相像。 ②法语:是真的? ③法语:一小撮酒石。 “没有患了三次中风还能幸存的事,”德国大夫对副官说道。 “他从前是个精力多么充沛的男人啊!”副官说道。“这份财产以后归什么人?”他轻言细语地补充一句。 “自愿当继承人的准会有的。”德国人面露微笑,答道。 大家又向门口望了一眼,门吱呀一声响了,公爵的二小姐依照罗兰的指点做好了饮料,送到病人那里。德国大夫向罗兰面前走去。 “大概他还能拖到明天早上吧?”德国人说着一口蹩脚的法国话问道。 罗兰撇一撇嘴唇,在鼻子前严肃地挥动指头,表示不赞同。 “今天夜晚,不会更晚。”他轻声说道,他因为能够明确地了解并说明病人的病情而洋洋自得,他脸上露出文质彬彬的笑意,走开了。 与此同时,瓦西里公爵打开了公爵小姐的房门。 房间里半明半暗。神像前面只点着两盏长明灯。神香和花朵散发着沁人的幽香。这个房间摆满了小柜子、小橱子、茶几之类的小家具。围屏后面看得见垫上绒毛褥子的高卧榻上铺着雪白的罩单。 “哦,是您呀,我的表兄吗?” 她站起身来,把头发弄平,她的头发向来是,甚至目前也是又平又光的,宛如头发和脑袋是用同一块原料造成的,头发又上了一层油漆。 “怎么,出了什么事吗?”她问道,“我真害怕得不得了。” “没有什么,还是那个样子,卡季什,我只是来和你谈一件事情,”公爵说道,困倦地坐在她刚刚坐过的安乐椅上,“可是,你把这张椅子坐热了,”他说道,“到这里来坐吧,cau B sons。” ① -------- ①法语:我们谈谈。 “我原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公爵小姐说,带着总是那样严肃而呆板的面部表情在公爵对面坐下,准备听他说话。 “我的表兄,我想熟睡一会儿,就是没法睡着。” “我亲爱的,怎么样?”瓦西里公爵说道,他一把握住公爵小姐的手,习惯地轻轻一按。 可以看出,“怎么样”这几个字是有关他们两人不开口也能相互了解的许多事情。 公爵小姐的腰身干瘦而僵直,和腿比起来显得太长了,一对灰眼睛突出来,直楞楞地、冷冰冰地端详着公爵。她摇摇头,叹口气,望了望神像。她的姿态可以说明她无限忠诚,但内心忧愁,也可以说明她非常劳累,希望快点得到休息,瓦西里公爵把她的姿态说成是困倦的表示。 “而我觉得,”他说道,“你以为我觉得更轻快吗?Jesuisèreintè,com meun che val depos te,①卡季什,可是我还要和你谈谈,很认真地谈谈。” -------- ①法语:我疲乏透了,像一匹驿马。 瓦西里公爵沉默不言,他的两颊时而这边时而那边神经过敏地抽搐起来,使得他的脸庞带有他在客厅里驻足时从未有过的令人不悦的表情。他的眼神也一反常态,时而放肆无礼地、滑稽可笑地望人,时而惊惶失措地环顾四周。 公爵小姐用一双干瘦的手把那只小狗抱在膝头上,聚精会神地望着瓦西里公爵的眼睛。可是,看起来,她即令沉默不言呆到早晨,也没法提出问题来打破这种静默。 “我亲爱的公爵小姐,表妹,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你是不是知道,”瓦西里公爵说道,看起来,要继续把话说下去,内心斗争不是没有的,“像现在这种时刻,什么都应当考虑考虑,应当考虑到将来,考虑到你们……我爱你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公爵小姐还是那样目光暗淡、滞然不动地望着他。 “最后,还应当考虑考虑我的家庭,”瓦西里公爵恼怒地推开自己身边的茶几,两眼没有望着她,继续说下去,“卡季什,你知道,你们马蒙托夫家的三个姐妹,可还有我的妻子,唯独我们才是伯爵的直系继承人。我晓得,我晓得,说这些事情,想这些事情,你觉得非常难受。我也不觉得轻松;可是,我的朋友,我有五十多岁了,一切事都要有所准备。我派了人去接皮埃尔,伯爵用手笔直地指着他的肖像,要他到他那里来,你知不知道?” 瓦西里公爵以疑问的眼神望望公爵小姐,但他没法弄明白,她是否在想他对她说的话,还是随便地望着他……“我为一桩事一直都在祷告上帝,moncousin,”她答道,“祈祷上帝宽恕他,让他高尚的灵魂平安地离开这个……” “对,是这样的,”瓦西里公爵心情急躁地继续说下去,一面用手搓着秃头,愤愤地把推开的茶几移到身边来,“可是,到头来,到头来,问题就在于,你自己知道,去冬伯爵写了遗嘱,把他的全部产业留给皮埃尔,我们这些直系继承人都没有份了。” “遗嘱随他去写吧,没有关系,”公爵小姐心平气和地说道,“但是他不能把遗产交给皮埃尔。皮埃尔是个私生子。” “machère,”瓦西里公爵忽然说道,他紧紧贴着茶几,露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说话的速度更快了,“假如伯爵禀告国王,请求立皮埃尔为子,那可怎么是好?你明白,就凭伯爵的功勋,他的请求是会受到尊重的……” 一些人以为他们自己比谈话对方知道的情形更多,他们就会面露微笑的,公爵小姐也同样地微微一笑。 “我还有更多的话要对你说,”瓦西里公爵一把抓着她的手,继续说下去,“信是写好了,尽管还没有寄上,国王也知道底细,只不过问题在于,这封信是否烧毁。若是没有焚毁,不久的将来一切都会完蛋的。”瓦西里公爵叹口气,用以使人家明白,“一切都会完蛋”的是有什么含义,“伯爵的文件一被拆开,遗嘱及信函就要呈交国王,他的请求大概会得到尊重的。皮埃尔作为合法的儿子就能获得一切产业。” “而我们的那一份遗产呢?”公爵小姐问道,讥讽地微笑,好像一切都会发生,只有这桩事不会发生似的。 “Mais,mapauvreCatiche,c’estclair,commele jour,①那时候,只有他一人才是全部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你们一定得不到自己的这一份。我亲爱的,你必须知道,遗嘱和奏疏是否已经写好了,或者已经烧毁了。假如这两样被人置之脑后,那你就应当知道这些东西搁在哪里,并且一一找到,因为……” “竟有如此愚蠢之事!”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露出恶意的微笑,也没有改变眼睛的表情,“我是个女人,依您看,我们都是些蠢货。可是,据我所知,私生子不能继承遗产…… un bat ard,”②她补充一句,以为通过翻译,可以使公爵彻底明了他缺乏继承的充分理由。 -------- ①法语:可是,卡季什,这是一清二楚的事啊。 ②法语:私生子。 “卡季什,你怎么总不明白!你这样聪明,怎么不明白;倘使伯爵给国王写了奏疏,请求国王承认他的儿子是合法的。这么说,皮埃尔已经不是皮埃尔,而是别祖霍夫伯爵了,到那时他可凭遗嘱获得全部遗产吗?倘使遗嘱和奏疏未被烧毁,那末,你除了具有高尚品德,聊以自慰而外,什么也捞不到。 这是千真万确的话。” “我知道,遗嘱已经写好了,但是我也知道,遗嘱不生效,您似乎认为我是个十足的蠢货,mon cousin,”公爵小姐说道,她那神态,俨如那些认为自己说了侮辱性的俏皮话的女人的神态一样。 “你是我的亲爱的公爵小姐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瓦西里公爵急躁地说道,“我到你这里来不是要和你争吵,而是要和一个亲人、一个善良、诚挚的亲人谈谈你的切身利益问题。我第十次告诉你,倘使伯爵的文件中附有呈送国王的奏疏和对皮埃尔有利的遗嘱,那末,我亲爱的,你和你的几个妹妹都不是遗产继承人了。假若你不相信我,你就相信知情人吧:我方才跟德米特里·奥努夫里伊奇(他是个家庭律师)谈过话,他也是这样说的。” 显然,公爵小姐的思想上忽然起了什么变化,她那薄薄的嘴唇变得苍白了(眼睛还是那个样子),当她开口说话时,嗓音时断时续,显然这并非她自己意料的事。 “这样挺好啊,”她说道,“我从前不想要什么,现在也不想要什么。” 她把那小狗从膝盖上扔下去,弄平连衣裙的皱褶。 “这就是谢忱,这就是对为他牺牲一切的人们的感激之情,”她说道,“好极了!很好!公爵,我什么都不要了。” “是的,可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几个妹妹。”瓦西里公爵答道。 但是公爵小姐不听他说话。 “是的,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可是我已经置之脑后了。除了卑鄙、骗局、嫉妒、阴谋诡计,除了忘恩负义,黑心眼的忘恩负义,我在这栋住宅里什么也不能期待……”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份遗嘱搁在什么地方?”瓦西里公爵问道,他的两颊痉挛得比先前更加厉害了。 “是的,我十分愚蠢,还轻信人们,喜爱他们,并且牺牲我自己。可是只有那班卑鄙恶劣的坏人才会得心应手。我晓得这是谁搞的阴谋诡计。” 公爵小姐想站立起来,可是公爵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不让她走。公爵小姐露出那副样子,就像一个人突然对全人类感到悲观失望似的;她愤恨地望着交谈的对方。 “我的朋友,时间还是有的。卡季什,你要记住,这种种事情都是无意中发生的,是在气忿和罹病之际发生的,之后就遗忘了。我亲爱的,我们的义务就是要纠正他的错误,不让他做出这等不公允的事,减轻他临终之时的疾苦,不让他在心里想到使那些人不幸时死去……” “那些为他而牺牲一切的人,”公爵小姐应声说道,又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公爵不放她走,“他从来不会器重他们。不,moncousin,”她叹息地补充说,“我要铭记,在这尘世上不能期待奖励,在这尘世上既无荣誉,亦无公理。在这尘世上就要狡猾,凶恶。” “行了,voyons,①安静下来吧,你的好心肠我是知道的。” -------- ①法语:行了。 “不,我的心肠恶毒。” “你的心我是知道的,”公爵重复地说道,“我珍惜你的友谊,希望你对我抱有同样的观点。安静下来吧,par lon srai Bson①,时间还是有的,也许会有一昼夜,也许只有一个钟头,你把你所知道的有关遗嘱的情况全部说给我听吧,主要的是,遗嘱搁在哪儿,你应当知道。我们立刻把它拿给伯爵过目,他大概把它遗忘了,他想把它毁掉。你心里明白,我唯一的心愿就是神圣地履行他的意愿,正是为了这一层,我才走到这里来。我呆在这儿只是为着帮助他,也帮助你们。” “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我晓得这是谁搞的阴谋诡计。我晓得。”公爵小姐说道。 “我的心肝,不是那么回事。” “她就是您的被保护人,您的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个卑劣、可恶的女人,给我做婢女我都不愿意接受。” “Neperdons point de temps.”② “唉,您甭说了吧!她去冬悄悄窜到这里来,向伯爵说了许多骂我们大家,特别是骂索菲的卑鄙龌龊的话,真叫我没法再说一遍,伯爵给弄得害病了,一连两个礼拜不愿意和我们见面。我知道就在这时候他写了这份令人厌恶的文件,不过我以为这份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Nousyvoila③,你干嘛不早点说给我听呢?” -------- ①法语:我们正经地谈谈吧。 ②法语:我们甭浪费时间吧。 ③法语:问题也就在这里。 “在他枕头底下的嵌花皮包里。我现在知道了,”公爵小姐不回答他的话,说道,“是的,设若我有罪孽,弥天的罪孽,这就是我痛恨这个可恶的女人,”公爵小姐几乎要叫喊起来,脸色全变了,“她干嘛悄悄窜到这里来?我把要说的话向她一股脑儿说出来,到时候一股脑儿说出来!” ------------------ 19 当客厅中和公爵小姐寝室中交谈正酣的时候,皮埃尔(已着人接他回家)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她认为应当伴他同行)乘坐的四轮轿式马车开进了别祖霍夫伯爵的庭院。当马车车轮软绵绵地经过铺在窗下的麦秆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把脸转向皮埃尔,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当她弄清了,皮埃尔正在车厢的一角睡熟了,她便把他喊醒。皮埃尔睡醒了,跟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身后从车厢里走出来,这时分他才想了想他要和行将就木的父亲见面的事情。他发现他们没有朝前门门口走去,而是朝后门门口走去。他从马车踏板走下来时,有两个穿着市侩服装的人急匆匆地从后门门口跑到墙边的暗影里。皮埃尔停了一会儿,发现住房两边的暗影里还有几个类似模样的人。然而,无论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无论是仆役,还是马车夫,都不会望不见这几个人,但却不去理睬他们。由此看来,非这样不可,皮埃尔拿定了主意,便跟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后面走去。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迈着急促的脚步沿着灯光暗淡的狭窄的石梯上楼,一面招呼落在她身后的皮埃尔跟上来。虽说皮埃尔心里不明白,他为什么真的要见伯爵,他更不明白,他为什么必须沿着后门的石梯上楼,但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坚定和仓忙的样子来推敲,他暗自断定,非这样不行,别无他途。在石梯半中间,有几个拿着水桶的人,穿着皮靴,踏得咯咯作响,朝着他们迎面跑下楼来,险些儿把他们撞倒。这几个人挨在墙上,让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过去,当他们看见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时,丝毫没有现出诧异的样子。 “这里可通往公爵小姐的住房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他们之中的某人问道。 “在这里。”有个仆役大胆地、嗓音洪亮地答道。仿佛现在什么事都是可行的,“大娘,门在左边。” “伯爵也许没有喊我,”皮埃尔走到楼梯的平台时,说道,“我回到自己的住房去好了。”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停步了,想和皮埃尔一同并肩走。 “Ah,monami”她说道,那姿态就像早晨和儿子在一起时碰碰他的手那样,“croyez,que je sof fre,autant quevous,mais soye zhom me。”① “说实话,我去好吗?”皮埃尔问道,透过眼镜温和地望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Ah,monami,oubliezlestortsqu’onapuavoi renvers vous,pen sez quec’e stvo trepère…… peut-êtreàl’ago nie她叹了口气,“Je vousai tout de suite aime com memon fils,fiez vou sà moi,Pierre,Jen’oub lie rai pas vo sin té rêts.”② -------- ①法语:啊,我的朋友,请您相信,我比您更加难受,但是,您要做个男子汉。 ②法语:啊,我的朋友,请您忘记人家对您不公道的态度吧。请您想想,他是您父亲……也许他死在旦夕。就像爱儿子那样,我一下子爱上您了。皮埃尔,信赖我吧,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切身利益。 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仿佛愈益感觉得到,一切都非如此不可,他于是温顺地跟随在那个打开房门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身后。 这道门朝向后门的外间。公爵小姐们的一个年老的仆役坐在屋角里织长统袜子。皮埃尔从来没有到过这半边住宅,连想也没有想过这种内室的生活。一个婢女手捧托盘,托着一只长颈水瓶,从后头赶上他们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称呼她小妹子、亲爱的,向她探问公爵小姐们的健康状况。她带领皮埃尔沿着砖石结构的走廊向前走去。走廊左边的第一扇门通向公爵小姐们的住房。手捧长颈水瓶的婢女在仓促中没有关上房门(这时分整座住宅显得手忙脚乱),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从旁边走过时,情不自禁地朝房里瞥了一眼,瓦西里公爵和公爵的大小姐正坐在这间屋里,彼此隔得很近,正在谈话。瓦西里公爵看见有人从旁边过去,做了个烦躁的动作,身子向后仰,靠在椅背上;公爵的大小姐霍地跳起来,无所顾忌地、鼓足气力地砰的一声关上门了。 这个动作和公爵的大小姐平素的宁静截然不同,瓦西里公爵脸上露出的恐怖和他固有的傲气也不相称,因此皮埃尔止了步,他以疑问的目光透过眼镜望了望他的带路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没有显示出诧异的样子,只是微微一笑,喘了喘气,好像在表示,这一切没有出乎她所意料。 “Soyezhomme,monami,c’estmoi quiveil lerai à vo sin té rêts。”①她在应对他的眼神时说道,而且行速更快地沿着走廊走去了。 -------- ①法语:我的朋友,要做个大丈夫,我准维护您的利益。 皮埃尔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更不明白veilleràvo sin te cits①有何涵义,但他心里明白,这一切理当如此。他们经过走廊走到和伯爵的接待室毗邻的半明半暗的大厅。这是皮埃尔从正门的台阶一看就知晓的冰凉的豪华卧室之一。但是,就在这卧室的中央,摆着一只空浴盆,地毯上洒满了水。一名仆役和一名手捧香炉的教堂下级职员踮着脚尖向他们迎面走来,并没有注意他们。他们走进了皮埃尔熟悉的接待室,室内安装有两扇朝着冬季花园的意大利式窗户,陈列着一座叶卡捷琳娜的半身大雕像和一幅她的全身画像。接待室里还是原来那些人,差不多还是坐在原来那些位子上窃窃私语。大家都静默起来了,回头望望走进门来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她泪痕斑斑,脸色苍白;也回头望望个子高大、长得肥胖的皮埃尔,他低垂着头,顺从地跟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后面。 -------- ①法语:维护他的利益。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神色表明了,她已经意识到紧要关头来到了。她不让皮埃尔离开她身边,显露出彼得堡女士那种务实的风度,步入房间,那样子比早上显得更大胆了。她觉得,她领着一个死在旦夕的伯爵想要见面的人,所以,她被接见一事是有保证的了。她向房里所有的人匆匆地瞥了一眼,看见了伯爵的那个听取忏悔的神甫,她没有躬起身子,但忽然变得更矮小了。她迈着小步东歪西扭地走到神甫面前,十分恭敬地接受一个又一个神职人员的祝福。 “谢天谢地,总算赶到了,”她对一个神职人员说道,“我们大伙儿,这些亲属多么担心啊。这个年轻人就是伯爵的儿子,”她把嗓门压得更低,补充了一句,“多么可怕的时刻!” 她说完这些话,就向大夫面前走去了。 “Cherdocteur,”她对他说道,“ce jeune hom me estle fils du com te…… ya— t— ildel’espoir?”① 大夫沉默不言,飞快地抬起眼睛,耸起肩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也同样地耸起肩膀,抬起几乎是合上的眼睛,叹了一口气,便离开大夫,向皮埃尔面前走去。她把脸转过来,和皮埃尔交谈,样子显得特别谦恭、温柔而又忧愁。 “Ayezconfianceensamisericorde!”②她对他说道,用手指了指小沙发,让他坐下来等候她,她自己悄悄地向大家盯着的那扇门走去,门的响声几乎听不见,她随即在门后隐藏起来了。 -------- ①法语:亲爱的大夫,这个青年是伯爵的儿子……是不是有希望呢? ②法语:信赖天主发善心吧! 皮埃尔拿定了主意,事事都听从他的带路人,他向她指给他看的小沙发走去。一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躲在门后,他就发现,房间里的众人的目光都过分好奇地、同情地凝聚在他身上。他发现,大家在窃窃私语,用目光向他表示,有如目光中流露出恐惧,甚至是奴颜婢膝的样子。大家都向他表示前所未有的敬意。有个他不认识的女士,原先她和几个神职人员谈话,此刻站起身来,向他让座。副官把他无意中掉在地上的一只手套捡起来交给他。他从大夫们身边经过时,他们都默不做声,躲到一边去,给他让路。皮埃尔本来想坐在别的位子上,以免那个女士受拘束,本来想自己把手套捡起来,从那些根本没有拦路的大夫们身边绕过去,可是他突然感到这样做似乎不恰当,他感到今天晚上他是个务必要举行一次可怖的、人人期待的仪式的人物,因此他必须接受大家为他服务。他默不作声地从副官手里接过那只手套,坐在那个女士的座位上,摆出一副埃及雕像那样天真的姿势,把一双大手搁在摆得平衡的膝头上。他暗自下了决心,认为必须这样行事,为了要今天晚上不张皇失措,不做出傻事,他就不宜依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务必要完全听从指导他的人们的摆布。 还不到两分钟,瓦西里公爵便穿着那件佩戴有三枚星徽的长衣,高高地仰着头,傲慢地走进房里来。从清早起他似乎显得有点消瘦,当他向房里环顾,瞧见皮埃尔时,他的两眼比平常瞪得更大了。他向皮埃尔面前走去,一把握住他的手(过去他从未握过他的手),并且向下曳了曳,好像想测试一下,这只手臂的力气大不大。 “Courage,courage,monamiI la de mand é à vous voir,C’est bien ……”①他于是要走了。 但是皮埃尔认为,问一问是有必要的。 “身体可好么……”他踌躇起来,不知道把行将就木的人称为伯爵是否恰当;他觉得把他称为父亲是很难为情的。 “Ilaeuencoreuncoup,ilyau ne de mi— heure、还发作过一次。Cou rage,mo nami …”② -------- ①法语:我的朋友,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他吩咐人家把您喊来。这很好…… ②法语:半小时前还发作过一次。……我的朋友……不要气馁…… 皮埃尔处于思路不清的状态中,他一听到“中风病发作”,便把这个词想象成受到某件物体的打击。他惶惑不安地望了望瓦西里公爵,之后才想起,有种病叫做中风。瓦西里公爵在走路时对罗兰说了几句话,就踮着脚尖走进门去。他不善于踮着脚尖走路,整个身子呆笨地一耸一耸地翕动。公爵的大小姐跟在他身后,几个神甫和教堂下级职员尾随其后,仆人们也走进门里去。从门后可以听见物体移动的响声,末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跑了出来,她的脸部仍然显得那样苍白,但却流露着坚决履行义务的神色,她碰碰皮埃尔的手臂,说道: “Labontédivineestinépuisable,C’estla cé ré monie del’ex - tre me on cti on quivacom mencer venez.”① -------- ①法语:上帝的慈善是无穷的。马上就要举行涂圣油仪式了。我们走吧。 皮埃尔踩着柔软的地毯走进门来,他发现一名副官、一个不相识的女士,还有仆役中的某人都跟在他身后走进门来,好像此刻无须获得许可就能走进这个房间了。 ------------------ 20 这个大房间皮埃尔了若指掌,几根圆柱和一道拱门把它隔开来了,四面墙上挂满了波斯壁毯。房间里的圆柱后面,一方摆着一张挂有帷幔的高高的红木卧榻,另一方陈设着一个大神龛,像晚祷时的教堂一般,房间的这一部分灯火明亮,红光四射。神龛的灿烂辉煌的金属衣饰底下,放着一张伏尔泰椅,上面摆着几个雪白的、尚未揉皱的、显然是刚刚换上的枕头,皮埃尔所熟悉的他父亲别祖霍夫伯爵的端庄的身躯就躺在这张伏尔泰椅上,一床鲜绿色的被子盖在他腰上,在那宽大的额头上还露出狮子鬃毛般的白发,在那俊美的橙红色的脸上,仍旧刻有高贵者特有的深深的皱纹。他直挺挺地躺在神像下方,两只肥大的手从被底下伸出来,放在它上面。右手手掌向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插着一根蜡烛,一名老仆从伏尔泰椅后面弯下腰去,用手扶着那根蜡烛。几个神职人员高高地站在伏尔泰椅前面,他们身穿闪闪发光的衣裳,衣裳外面露出了长长的头发,他们手里执着点燃的蜡烛,缓慢地、庄严地做着祷告。两个年纪较小的公爵小姐站在神职人员身后不远的地方,用手绢捂着眼角边,公爵的大小姐卡季什站在她们前面,她现出凶恶而坚定的神态。目不转睛地望着神像,好像在对众人说,如果她一环顾,她就没法控制自己。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流露着温顺的忧愁和大度包容的神色,她和一个不认识的女士伫立在门旁。这扇门的另一边,靠近伏尔泰椅的地方,瓦西里公爵站在雕花的天鹅绒面交椅后面,他把椅背向自己身边转过来,左手执着一根蜡烛撑在椅背上,每次当地用手指碰到额角时,他就抬起眼睛,一面用右手画十字。他的脸上呈露着心安理得的虔诚和对上帝意志的无限忠诚。“假若你们不明白这种感情,那末你们就更糟了。”他那神色仿佛说出了这番话。 一名副官、数名大夫和一名男仆站在瓦西里公爵后面,俨如在教堂里那样,男人和女人分立于两旁。大家都沉默不言,用手画着十字,只听见琅琅祈祷声、圆浑而低沉的唱诗声以及静默时移动足步的响声和叹息声。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现出威风凛凛的样子,表示她知道应该怎样行事,她于是穿过房间走到皮埃尔身边,把一支蜡烛递给他。他把蜡烛点燃了,因为他乐于观察周围的人而忘乎所以,竟然用那只拿过蜡烛的手画起十字来。 最年幼的长有一颗胎痣的公爵小姐索菲,两颊粉红,含着笑意,正在打量着皮埃尔。她微微一笑,把脸蛋藏进手绢里,久久地不肯把它露出来。但是她望了望皮埃尔,又笑了起来。显然,她觉得看见他就会发笑,但却忍不住,还是会看他,为避免引诱,她悄悄地窜到圆柱后面去了。在祈祷的半中间,神职人员的声音骤然停止了,但有几个神甫轻声地交谈了三言两语,一名老仆握着伯爵的手,站起身来,向女士们转过脸去。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前走去,在病人前面弯下腰来,从背后用指头把罗兰招呼过来。这个法国大夫没有执着点燃的蜡烛,作出一副外国人的恭敬的样子挨着圆柱站在那里,他那样子表明,尽管信仰不同,但他还是明了正在举行的仪式的全部重要意义,他甚至对这种仪式表示称赞。他迈着壮年人的不声不响的脚步向病人身边走去,用他那雪白而纤细的手指从绿色被子上拿起伯爵那只空手,转过脸去,开始把脉,他沉思起来。有人让病人喝了点什么,在他身旁动弹起来,然后又闪在一边,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暂停之后祈祷又开始了。在暂时休息的时候,皮埃尔看见,瓦西里公爵从椅子背后走出来,那神态表示,他心里知道应该怎样行事,假若别人不了解他,他们的处境就更糟了,他没有走到病人跟前,而是从他身边经过,他去联合公爵的大小姐,和她一起走到寝室深处挂有丝绸帷幔的高高的卧榻那里去了。公爵和公爵的大小姐离开卧榻朝后门方向隐藏起来了,但在祈祷告竣之前,他们二人前后相随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皮埃尔对这种情形,如同对其他各种情形一样,并不太注意,他断然认为,今晚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 唱诗中断了,可以听见一个神职人员恭敬地祝贺病人受圣礼。病人仍旧是死气沉沉地一动不动地躺着。大家在他周围动弹起来了,传来步履声和絮语声,在这些语声之中,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声音听来最刺耳了。 皮埃尔听见她这样说: “一定要将病人移到床上去,在这里是决不行的……” 大夫们、公爵小姐们和仆役们都围在病人身边,以致皮埃尔看不见橙红色的头和狮子鬃毛般的白发,尽管在祈祷时他也看见其他人,但是伯爵的头一刻也没有越出他的视野,从围在伏尔泰椅旁边的人们的小心翼翼的动作来看,皮埃尔已经猜想到,有人在把垂危的人抬起来,把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抓住我的手,那样会摔下去的,”他听见一个仆役的惊恐的低语声,“从下面托住……再来一个人,”几个人都开腔说话,人们喘着粗气的声音和移动脚步的声音显得更加急促了,好像他们扛的重东西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 扛起伯爵的人们,其中包括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内,都赶上年轻的皮埃尔,走到他身边了,从人们的背脊和后脑勺后面,他隐约地看见病人又高又胖的裸露的胸膛,因被人搀起两腋而略微向上翘起的胖乎乎的肩膀和长满卷曲白发的狮子般的头。他的前额和颧骨非常宽阔,嘴长得俊美而富于肉感,目光威严而冷漠。这个头并未因濒临死亡而变得难看,和三个月以前伯爵打发皮埃尔去彼得堡时一模一样。但是,这个头竟因扛起伯爵的人脚步不均匀而显得软弱无力,微微地摇晃,他那冷漠的目光真不知要停留在什么上面。 扛过病人的人们在那高高的卧榻周围忙碌几分钟以后,就各自散开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碰了碰皮埃尔的手,对他说:“venez.”①皮埃尔和她一道走到卧榻前面,病人安放在卧榻之上,那姿态逍遥自在,这显然是和方才施圣礼有关系。他躺着,头部高高地靠在睡枕上,掌心向下,两手平衡地搁在绿色丝绸被子上。当皮埃尔走到近旁,伯爵的目光直直地射在他身上,但是没有人能够了解他那目光表露什么意义,也许它根本没有含义,只是因为他还有一双眼睛,他就要朝个方向随便看看罢了,也许这目光表明了太多的心事。皮埃尔停步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他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他的带路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赶快使个眼色向他示意,同时用手指着病人的手,用嘴唇向它送了个飞吻。皮埃尔极力地把颈子伸长,以免碰到伯爵的丝绸被子,又用嘴唇吻吻他那骨胳大的肥厚的手,履行了她的忠告。无论是伯爵的手,还是他脸上的筋肉都不会颤动了。皮埃尔又疑问地望了望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她发问,他现在该做什么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他使个眼色,心中意指着卧榻旁边的安乐椅。皮埃尔在安乐椅上温顺地坐下来,继续用目光询问,他做得是否恰到好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点点头,表示称赞。皮埃尔又做出一副埃及雕像那种恰如其分的稚气的姿势,显然,他因为自己那粗笨肥大的身体占据太大的空间而倍觉遗憾,才煞费苦心尽量使自己缩得小一点。他两眼望着伯爵。伯爵还在端详着皮埃尔站立时他脸部露出的地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面部表情说明了,她意识到父子最后一次相会的时刻是何等令人感动。这次相会持续了两分钟,皮埃尔心里觉得这两分钟好像一小时似的。伯爵脸上的大块肌肉和皱纹突然间颤抖起来,抖得越来越厉害,他的美丽的嘴扭歪了(这时皮埃尔才明白他父亲濒临死亡了),从那扭歪的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嘶哑的声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极力地看着病人的眼睛,力图猜中他想要什么东西,她时而用手指着皮埃尔,时而指着饮料,时而带着疑问的语调轻声地叫出瓦西里公爵的名字,时而用手指着伯爵的被子。病人的眼睛和脸部流露出已无耐性的样子。他极力凝视一直站在床头的仆人。 -------- ①法语:我们走吧。 “老爷想把身子转向另一侧啦,”仆役轻声地说道,他站了起来,让伯爵把脸部向墙,将那沉重的身躯侧向另一边。 皮埃尔站立起来,帮助这个仆人。 当众人使伯爵翻过身去的时候,他的一只手软弱无力地向后垂下,他用力地想把自己的这只手拿过去,但是无能为力,白费劲。伯爵是否已经发觉,皮埃尔在用那可怖的目光望着这只感觉迟钝的手,也许还有什么别的思绪在这生命垂危的脑海中闪现,但他望了一下自己那只不听使唤的手,望了一下皮埃尔脸上流露的可怖的表情,又望了一下自己的手,那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种和他的仪表不能并容的万分痛苦的微笑,仿佛在讥讽他自己的虚弱无力。皮埃尔望见这种微笑,胸中忽然不寒而栗,鼻子感到刺痛,一汪泪水使他的视线模糊了。病人面向墙壁,被翻过身去。他叹了口气。 “Ilestassoupi.”①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看见走来接班的公爵小姐,说道,“Allons。”② 皮埃尔走出去了。 ------------------ 21 除开瓦西里公爵和公爵的大小姐而外,接待室里没有其他人,他们二人坐在叶卡捷琳娜画像下面,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什么事。他们一望见皮埃尔和他的带路人,就默不作声了。 皮埃尔仿佛看见公爵的大小姐把一样东西藏起来,并且轻言细语地说道: “我不能跟这个女人见面。” “Caticheafaitdonnerduthédanslepetitesalon,”瓦西里公爵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Allez,mapauvre安娜·米哈伊洛夫娜,pren ez que que clhose,autrem en tvous nesuf fire zpas.”③ 他对皮埃尔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亲切地握握他的手。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pet it Aalon④走去。 -------- ①法语:他昏迷不醒了。 ②法语:我们走吧。 ③法语:卡季什已经吩咐人将茶端进小客厅去了。可怜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您最好去提提精神,否则您会没有力气的。 ④法语:小客厅。 “Iln’yarienquirestaure,commeunetassedece tex cel Blent thé rus sea prè su nenuit blan che,”①罗兰在圆形小客厅的桌子前面站着,这张桌上放着茶具和晚餐的冷菜,他端着很精致的不带把的中国茶碗,一口一口地呷着茶,流露着抑制兴奋的神色说道。这天晚上,那些在别祖霍夫伯爵家里的人,为了要提提精神,都聚集在桌子周围。皮埃尔很清楚地记得这间嵌有几面镜子和摆放几张茶几的圆形小客厅。伯爵家里举行舞会时,皮埃尔不会跳舞,只喜欢坐在这间嵌有镜子的小客厅里,从一旁观看那些穿着舞衣、裸露的肩上戴有钻石和珍珠项链的女士们穿过这间客厅时照照镜子的情景,几面闪闪发亮的镜子一连几次反映出她们的身影。现在这个房间只点着两根光线暗淡的蜡烛,在这深夜里,一张小茶几上乱七八糟地放着茶具和盘子,穿着得不太雅致的五颜六色的人们坐在这个房间里窃窃私语,言语行动都表示谁也不会忘记现在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皮埃尔没有去吃东西,尽管他很想吃东西。他带着疑问的目光望望他的带路人,看见她踮起脚尖又走到接待室,瓦西里公爵和公爵的大小姐还呆在那里,没有走出去。皮埃尔认为有必要这样行事,他停了一会,便跟在她后面去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站在公爵的大小姐近旁,二人同时心情激动地轻声说话。 -------- ①法语:在不眠之夜以后,再没有什么比一碗十分可口的俄国茶更能恢复精力的了。 “公爵夫人,请您让我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公爵的大小姐说,她那激动的心情显然跟她砰然一声关上房门时的心情一样。 “可是,亲爱的公爵小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拦住通往寝室的路,不让公爵小姐走过去,她温和而恳切地说,“在可怜的叔叔需要休息的时刻,这样做不会使他太难受么?在他已经有了精神准备的时刻,竟然谈论世俗的事情……” 瓦西里公爵坐在安乐椅上,一条腿高高地架在另一条腿上,现出十分亲热的姿态。他的腮帮子深陷,下部看起来更为肥厚,跳动得很厉害,但是他摆出一副不太关心两个女士谈论的样子。 “Voyons,mabonne,安娜·米哈伊洛夫娜,lais sez faire Ca ti che①,您知道,伯爵多么喜爱她啊。” “这份文件中包含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公爵小姐把脸转向瓦西里公爵,并用手指着她拿在手里的镶花皮包,说道,“我只知道他的真遗嘱搁在旧式写字台里,而这是一份被遗忘的文件……” 她想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身边绕过去,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跳到她跟前,拦住她的去路。 “亲爱的、慈善的公爵小姐,我知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用手抓着皮包,抓得很紧,看起来她不会很快松手的,“亲爱的公爵小姐,我求您,我央求您,怜悯怜悯他。 Jevousenconjure……”② -------- ①法语:不过,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让卡季什去做她知道做的事吧。 ②法语:我央求您。 公爵的大小姐默不作声。只传来用力抢夺皮包的响声。由此可见,如果她开口说话,她也不会说出什么称赞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话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抓得很紧,但是她的声音慢吞吞的,还是保持着谄媚、委婉的意味。 “皮埃尔,我的朋友,到这里来。我想,他在亲属商议事情时不是多馀的。公爵,不是这样吗?” “我的表兄,干嘛不作声?”公爵的大小姐突然叫喊起来,喊声很大,客厅里也能听见,可把大家吓坏了,“天晓得有个什么人胆敢在这里干涉别人的事,在临近死亡的人家里大吵大闹,您干嘛在这个时候一声不吭?一个施耍阴谋诡计的女人!”她凶恶地轻声说道,使尽全身力气去拖皮包,但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前走了几步,不想放开那个皮包,换一只手把它抓住了。 “哎呀!”瓦西里公爵露出责备和惊讶的神态说,他站起身来。“C’estri di cule,vo yons①,放开吧,我说给您听吧。” 公爵的大小姐放开手了。 “您也放开手!”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没有听从他。 “放开,我说给您听吧。我对一切负责。我去问他。我…… 您别这样了。” “Mais,monnpuince,”②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在举行这样盛大的圣礼以后,让他安静片刻吧。皮埃尔,您把您的意见说出来,”她把脸转向年轻人说道;皮埃尔走到他们近侧,诧异地打量着公爵小姐那副凶狠的,丧失体统的面孔和瓦西里公爵的不停地颤动的两颊。 -------- ①法语:这真可笑。得啦吧。 ②法语:但是,我的公爵。 “您要记得,您要对一切后果负责,”瓦西里公爵严肃地说,“您不知道您在搞什么名堂。” “讨厌的女人!”公爵小姐嚷道,忽然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扑了过去,夺取那皮包。 瓦西里公爵低下头来,把两手一摊。 这时分,那扇房门——素来都是轻轻地打开的令人可怖的房门,皮埃尔久久地望着,房门忽然砰地一声被推开了,撞到墙壁上,公爵的二小姐从那里跑出来,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 “你们在做什么事?”她无所顾忌地说道,“Ils’envaet vous melais sez seu le.”① -------- ①法语:他快要死了,可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 公爵的大小姐丢掉了皮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飞快弯下腰去,顺手拾起那件引起争端的东西,就到寝室里去了。公爵的大小姐和瓦西里公爵在清醒以后,也跟在她后面走去。过了几分钟,公爵的大小姐头一个从那里走出来,面色惨白,紧闭着下嘴唇。她看见皮埃尔,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愤恨。 “对了,您现在高兴了,”她说道,“这是您所期待的。” 她于是嚎啕大哭起来,用手绢蒙住脸,从房里跑出去了。 瓦西里公爵跟在公爵的大小姐后面走出去。他步履踉跄地走到皮埃尔坐的长沙发前面,用一只手蒙住眼睛,跌倒在长沙发上。皮埃尔发现他脸色苍白,下颔跳动着,颤栗着,像因冷热病发作而打战似的。 “哎呀,我的朋友!”他一把抓住皮埃尔的胳膊肘,说道,嗓音里带有一种诚实的软弱的意味,这是皮埃尔过去从未发觉到的,“我们造了多少孽,我们欺骗多少人,这一切为了什么?我的朋友,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要知道,我……人一死,什么都完了,都完了。死是非常可怕的。”他大哭起来。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最后一人走出来。她用徐缓的脚步走到皮埃尔面前。 “皮埃尔!……”她说道。 皮埃尔以疑问的目光望着她。她吻吻年轻人的前额,眼泪把它沾湿了。她沉默了片刻。 “Iln’estplus…”① 皮埃尔透过眼镜望着她。 “Allons,jevousreconduiraiTachezdepleurer.Rien ne sou lage,com me les lar mes.”② -------- ①法语:他不在世了。 ②法语:我们走吧,我送您去。想法子哭吧,没有什么比眼泪更能使人减轻痛苦。 她把他带到昏暗的客厅里,皮埃尔心里很高兴的是,那里没有人看见他的面孔。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从他身旁走开了。当她回来时,他把一只手搁在脑底下酣睡了。 翌日清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皮埃尔说: “Oui,moncher,c’estunegrandeper te pour nous tous,Je ne par le pas de vous.Mais dieu vous sou tiend ra,vou sêtes jeune et vous voilàalate ted’ un eim mense for tune,jel’espère,Le tes tanentn’a pas é té encoreou vert,Je vous con naisas sezpour savoirque celanevous tounr ne ra pas lat ê te,mais ce lavousim- pose des devoirs,etil fau têtrehom mê.”① 皮埃尔沉默不言。 “Peut—êtreplustardjevousdirai,moncher,quesi jen’avai spa se te la,Di eu sait cequi serait arrive.Vous savez mononc leavant— hieren corem epromet tait denepasoubli Ber Boris. Maisiln’apas euletemps.J’espère,mon chera mi,quevous rem plirez led é sir devot repère.”② -------- ①法语:对,我的朋友,即使不提及您,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也是极大的损失。但是上帝保佑您,您很年轻,我希望您如今是一大笔财产的拥有者。遗嘱还没有拆开来,对于您的情形我相当熟悉,坚信这不会使您冲昏头脑。但是这要您承担义务,您要做个大丈夫。 ②法语:以后我也许会说给您听的,如果我不在那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您知道,叔父前天答应我不要不顾鲍里斯,但是他来不及了。我的朋友,我希望您能履行父亲的意愿。 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他沉默不言,羞涩地涨红着脸,抬起眼睛望着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皮埃尔谈了几句话,便离开他,前往罗斯托夫家憩宿。翌日清晨醒来,她向罗斯托夫家里人和各个熟人叙述了别祖霍夫伯爵辞世的详细情节。她说,伯爵正如她意料中的情景那样去世了,他的死不仅颇为感人,而且可资垂训。父子最后一次的会面竟如此感人,以致一想起此事她就会痛哭流涕,她不晓得在这令人可怖的时刻,父子二人中谁的行为表现更为出色,是在临终的时候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一一回顾、并对儿子道出感人的话的父亲呢,还是悲恸欲绝、为使死在旦夕的父亲不致于难受而隐藏自己内心的忧愁的、令人目睹而怜惜的皮埃尔。“C’estpenible,maiscelafaitdu bien:caelèvel’amedevoirdeshommes,com melevieux comte et sondi gne fils。”①她说道。她也秘而不宣地、低声地谈到公爵的大小姐和瓦西里公爵的行为,但却不予以赞扬。 -------- ①法语:这是令人难受的,却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当你看见老伯爵和他的当之无愧的儿子时,灵魂就变得高尚了。 ------------------ 22 在童山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的田庄里,大家每天都在等待年轻的安德烈公爵偕同夫人归来,但是期待没有打乱老公爵之家的严谨的生活秩序。在上流社会中浑名叫做leroidePrusse①的大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当保罗皇帝在位时就被流放到农村,他和女儿——叫做玛丽亚的公爵小姐以及她的女伴布里安小姐,在童山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新王朝执政时,虽然他已被允许进入都城,但他继续定居农村,从不外出,他说,如果有谁需要求他,那末他就得从莫斯科走一百五十俄里的路到童山来;而他对任何东西,对任何人都一无所求。他说,只有人才有两大罪恶的根源:无所事事和迷信;只有人才有两大崇高品德:活动和才智。他亲自培养自己的女儿,给她传授代数、几何课程,以便在她身上培养这两大品德;妥善地安排她的生活,要她不断地完成作业。他本人总是很忙,时而写回忆录,时而算高等数学题,时而在车床上车鼻烟壶,时而在花园里劳作和监督他田庄里未曾中断的建筑工程。因为活动的首要条件是秩序,所以在他的生活方式中程序已达到一丝不苟的程度。他依照一成不变的陈规出来用餐,总是在同一时辰,分秒不误。公爵对待周围的人,从他女儿到仆人,态度十分粗鲁,一向要求苛刻,所以,他纵然不算残忍,却常激起连最残忍的人也难以激起的一种对他的敬畏之感。他虽已退休赋闲,在国家事务中不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公爵的田庄所隶属的那个省份的每个上任的省长都认为拜谒他是一种应尽的义务,而且亦如建筑师、园丁或者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在那宽大的堂倌休息间等候公爵于规定时刻出来会客。每当书斋那扇高大的门被推开,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出来会客时,每个在堂倌休息间等候接见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一种尊敬甚至畏惧之感,这个老人头戴扑粉的假发,露出一双肌肉萎缩的小手和两条垂下的灰白的眉毛,有时他皱起眉头,眉毛便挡住那双机灵的、焕发着青春之光的眼睛。 -------- ①法语:普鲁士国王。 年轻夫妇抵达的那天早上,同平素一样,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在规定的时刻走进堂倌休息间叩请早安,她心惊胆战地画着十字,心中念着祷文。她每天走进休息间,每天都祈祷,希望这天的会见能平安无事地结束。 坐在休息间的那个头发上扑了粉的老仆人动作缓慢地站起来,轻言细语地禀告:“请。” 门后可以听见车床均匀地转动的响声。公爵小姐羞羞答答地拉了一下门,门很平稳地、轻易地被拉开了。她在门旁停步了。公爵在车床上干活,掉过头来望了望,又继续干他的活。 大书斋里堆满了各种东西,显然都是一些常用的东西。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着书本和图表,几个高大的玻璃书柜——钥匙插在柜门上,一张专供站着写字用的高台子——台子上摆着一本打开的练习本,一张车床——上面放着几件工具,四周撒满了刨屑,——这一切表明这里在进行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富有成效的活动。从他用以操作的那只穿着绣有银线的鞑靼式的皮靴的不大的脚来看,从青筋赤露、肌肉萎缩的手上磨出的硬皮来看,公爵还具有精神充沛的老人的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极大的耐力。他旋了几圈,便从车床踏板上把脚拿下来,揩干净凿头,把它丢进安在车床上的皮袋里。他向桌前走去,把女儿喊到身边来。他从来没有祝福自己的孩子,只是把他那当天还没有剃过的、胡子拉碴的面颊凑近他女儿,露出严肃的、温和而关怀的样子望望她,说道: “你身体好吗?……喂,坐下来吧!” 他拿起他亲手写的几何学练习本,又用脚把安乐椅推了过来。 “是明天的啊!”他说道,很快找到了那一页,在这段和另一段的两头用硬指甲戳上了记号。 公爵小姐在摆着练习本的桌前弯下腰来。 “等一下,有封你的信。”老人从安在桌上的皮袋中取出女人手笔的信一封,扔在桌上。 公爵小姐看见信,立刻涨红了脸,她赶快拿起信,低垂着头去看。 “爱洛绮丝寄来的吗?”公爵问道,把他那坚固的、略微发黄的牙齿露出来,冷冷一笑。 “是的,是朱莉寄来的。”公爵小姐说道,羞答答地望着,羞答答地微笑。 “还有两封信我不看,而第三封我一定要看,”公爵严肃地说道,“我怕你们在写一大堆废话。第三封我一定要看。” “monpeve①,就连这封信您也看吧。”公爵小姐答道,脸红得更加厉害,一面把信递给他。 -------- ①法语:爸爸。 “我已经说了,第三封,第三封。”公爵把信推开,迅速而果断地喊道。他用胳膊肘撑着桌子,把那绘有几何图形的练习本拖到身边来。 “喂,女士,”老头子开始说话,挨近女儿,朝着练习本弯下腰来,并把一只手搁在公爵小姐坐着的安乐椅的靠背上,公爵小姐觉得自己已被早就熟谙的父亲的烟草气味和老人的呛人的气味笼罩着。“喂,女士,这些三角形都是相似的:你看见,abc角……” 公爵小姐惊惶失措地望着父亲向她逼近的、闪闪发亮的眼睛,脸上泛起了红晕。可见,她什么都不懂得,心里很畏惧,虽然父亲的讲解清清楚楚,但是这种畏惧心毕竟会妨碍她弄懂父亲的进一步的讲解。教师有过错呢,还是女学生有过错呢,但是每天都重现着同样的情况。公爵小姐的眼睛模糊不清了,她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只觉得严厉的父亲那副干瘦的脸孔凑近她身边,她闻到他的气息和气味,只是想到尽快地离开书斋,好在自己房中无拘无束地弄懂习题。老头子发脾气了,轰隆一声把他自己坐的安乐椅从身边移开,又拖过来,他极力控制自己不动肝火,但是,差不多每次都火冒三丈,开口大骂,有时候竟把练习本扔到一边去。公爵小姐答错了。 “嘿,你真是个蠢货!”公爵嚷道,推开那本练习簿,飞快地转过脸去,但立刻站立起来,在房间里走走,用手碰碰公爵小姐的头发,又坐下来。 他将身子移近一点,继续讲解。 “公爵小姐,不行的,不行的,”当公爵小姐拿起继而又合上附有规定的家庭作业的练习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道,“数学是一件首要的大事,我的女士。我不希望你像我们那帮愚昧的小姐。习久相安嘛。”他抚摩一下女儿的面颊,“糊涂思想就会从脑海里跑出去。” 她想走出去,他用手势把她拦住了,从那高高的台子上取下一本尚未裁开的新书。 “还有你的爱洛绮丝给你寄来的一部《奥秘解答》。一本宗教范畴的书。我不过问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我浏览了一下。你拿去吧。得啦,你走吧,你走吧!” 他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等她一出门,他就在她身后亲自把门关上了。 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露出忧悒和惊恐的神色回到她自己的寝室。她常常带有这种神色,使她那副不俊俏的、病态的面孔变得更加难看了。她在写字台旁坐下,台子上放着微型的肖像,堆满了练习本和书本。公爵小姐缺乏条理,她父亲倒有条不紊。她搁下了几何学练习本,急躁地拆开那封信。信是公爵小姐童年时代的密友寄来的,这位密友就是出席过罗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会的朱莉·卡拉金娜。 朱莉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珍贵的朋友,离别是一桩多么可怖、多么令人痛苦的事啊!我多少次反复地对我自己申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幸福的一半寄托在您身上,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是我们的心是用拉不断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心逆着天命,不听从它的摆布,虽然我置身于作乐和消遣的环境中,但是自从我们分离后,我就不能抑制住我心灵深处的隐忧。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旧年夏天那样在您那宽大的书斋里聚首,一同坐在天蓝色的沙发上,“表白爱情”的沙发上呢?我为什么不能像三个月以前那样从您温顺、安详、敏锐的目光中,从我喜爱的目光中,从我给您写信时我依旧在我面前瞥见的目光中汲取新的精神力量呢? 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念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向嵌在右边墙上的穿衣镜照了照,镜子反映出一副不美丽的虚弱的身躯和那消瘦的面孔。一向显得怏怏不乐的眼睛现在特别失望地对着镜子看自己。“她谄媚我哩,”公爵小姐想了想。她把脸转过来继续念信。但是朱莉没有谄媚过朋友;诚然,公爵小姐那双深沉、炯炯发光的大眼睛(有时候仿佛发射出一束束温柔的光芒)十分美丽,尽管整个脸孔不好看,但是这双眼睛却常常变得分外迷人。公爵小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眼睛的美丽动人的表情,即是当她不思忖自己时她的眼睛的表情。如同所有的人,她一照镜子,脸上就流露出生硬的不自然的很不好看的表情。她继续读信: 整个莫斯科只知道谈论战争。我的两个长兄,一个已经在国外,另一个跟随近卫军向边境进发。我们亲爱的皇帝已经放弃彼得堡,有人推测,皇帝意欲亲自督阵,使宝贵生命经受一次战争的风险。愿上帝保佑,万能的上帝大慈大悲,委派一位天使充当我们的君主,但愿他推翻这个煽动欧洲叛乱的科西嘉恶魔。姑且不提我的两个长兄,这次战争竟使我丧失一个最亲密的人。我说的是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他充满热情,不甘于无所作为,离开了大学,投笔从戎。亲爱的玛丽,我向您坦白承认,虽说他十分年轻,但是他这次从军却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旧年夏天我曾经向您谈到这个年轻人,他有这么许多高高的品德和真正的青春活力。当代,在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小老头子中间,这是不常见的啊!尤其是他待人真诚,心地善良。他非常纯洁,充满着理想。我和他的关系虽如昙花一现,但这却是我这个遭受过许多折磨的不幸的心灵尝到的极为甜蜜的欢乐之一。 总有一天我要和您谈谈我们离别的情形、临别时的 赠言。所有这一切未从记忆中磨灭……啊!亲爱的朋友,您十分幸福,您没有尝受过炽热的欢快和难忍的悲痛。您十分幸福,因为悲痛常比欣悦更为强烈。我心中十分明白,尼古拉伯爵太年轻了,诚了作个朋友外,我认为,不可能搭上什么别的关系。但这甜蜜的友情,这多么象有诗意、多么纯洁的关系,是我心灵之所需。这件事别再谈了。 吸引整个莫斯科的注意力的头条新闻,是老别祖霍 夫伯爵的去世和他的遗产问题。您想象一下,三个公爵小姐获得一小部分,瓦西里公爵没有捞到分文,而皮埃尔却是全部遗产的继承人,此外他被公认为法定的儿子,即为别祖霍夫伯爵和俄国最大财富的占有者。据说,在这件事的始末,瓦西里公爵扮演了极其卑鄙的角色,很难为情地往彼得堡去了。我向您承认,我不大懂得遗嘱方面的事情,我只晓得,自从这个人人认识、名叫皮埃尔的年轻人变成别祖霍夫伯爵和俄国最大财富的占有者以后,我觉得可笑的是,我看见那些有及笄女儿的母亲以及小姐本人,都在这位先生面前变了腔调。附带说一句,我总觉得皮埃尔是个十分渺小的人。 因为这两个年头大家都在给我物色未婚夫,认为这 是开心的事儿(对象多半是我不认识的人),所以莫斯科婚姻大事记,要使我成为叫做别祖霍娃的伯爵夫人。可是您明了,这件事完全不合乎我的心愿。不妨顺便提提婚事吧。您是否知道,公认的大娘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不久以前极为秘密地把给您筹办婚事的意图告诉我了。对象正好是瓦西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利,他们正想给他娶一个有钱的、贵族门第的姑娘,您倒被他父母选中了。我不知道您对此事抱有什么看法。但我认为有责任提醒您哩。听说他相貌长得很漂亮,但却是个十足的浪子。关于他的情况,我打听到的只有这些,没有别的了。 够了,不必再扯了。我快写完第二页了,妈妈着人来叫我坐车到阿普拉克辛家去出席午宴。 请您读一读我给您寄上的这本神秘主义的书吧,在我们这儿,这本书大受欢迎。虽然我们普通人的贫乏的智慧很难弄懂这本书中的某些内容,但这却是一本出色的书。读这本书,能使灵魂升华,使灵魂得到安慰。再见吧。向您父亲致以敬意,并向布里安小姐问候。我衷心地拥抱您。 朱莉 再启:请将您长兄和他的可爱的妻子的消息告诉我。 公爵小姐想了想,沉思地微微一笑(与此同时,炯炯的目光照耀着她的脸庞,使它完全变了模样),她突然站立起来,曳着沉重的步子,向桌前走去。她取出一张纸,她的手开始迅速地在纸上移动。她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珍贵的朋友,十三日的来信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充满理想的朱莉,您仍旧爱我。可见您说得那么难堪的离别,在您身上没有产生常见的影响力。您埋怨别离,假如我敢于埋怨,那么我应当说句什么话—— 我丧失了我所珍惜的一切人吗?咳,假若没有宗教的安慰,生活就会极其凄凉。当您谈起您爱慕一个年轻人时,您为什么认为我的目光是严峻的呢?在这方面,我只是严谨地对待自己罢了。我明了别人的这种感情,既然我从未体会这种感情,不能予以赞扬,那我也不加以斥责。 我只是觉得,基督的仁爱,对敌人的爱,较之年轻人的一双美丽的眼睛使您这样一个充满理想的具有爱心的年轻姑娘产生的那种感情更为可敬,更为可贵,更为高尚。 在尚未接到您的来信以前,别祖霍夫伯爵去世的消 息就已经传到我们这里了,我父亲闻讯悲恸万分。他说别祖霍夫伯爵是我们伟大时代剩下的倒数第二个代表人物。现在要轮到他头上了。他将尽力而为,使这一轮尽量晚点到来。愿上帝保佑,使我们免受这种不幸啊! 我是女孩的时候就认识皮埃尔,我不能赞同您对他 的意见。我似乎觉得,他的心肠永远都是善良的。这正是我所珍惜的人应有的品德。至于他所继承的遗产以及瓦西里公爵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这对他们两人都是很不光彩的。啊,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救世的天主说了这么一句话:骆驼穿过针眼比富翁进入天国更容易,这句话很有道理!我怜悯瓦西里公爵,更加怜悯皮埃尔。他这么年少就要肩负一大笔财富的重担,他将要经受多少命运的考验啊!假若有人要问我,这尘世上我最希冀的是什么,我就会说,我希望做个比最贫穷的乞丐更穷的人。亲爱的朋友,我千万次地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给我寄来的一本在你们那里引起纷纷议论的书。其实,您对我说,在这本书的一些可取的内容之间还夹有一些我们普通人的贫乏的智慧不能弄懂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谈奥妙难懂的东西是多余的,不会给人们带来半点裨益。我从来没法领悟某些人的酷嗜,他们酷嗜神秘主义的书籍,思绪给弄得十分紊乱,因为这些书会在他们头脑中引起疑惑,激起他们的臆想,铸成他们那种与基督的纯朴完全对立的夸张的性格。 我们莫如读一读《使徒行传》和《福音书》吧。我 们不要妄图识透书本上包含的神秘的内容,因为趁我们这些不幸的罪人还有肉体的躯壳支撑,它在我们和永恒之间树立着穿不透的隔幕的时候,末日尚未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上天的可怖和神圣的隐秘呢?我们莫如只研究救世的天主遗留给我们作为尘世指南的那些伟大的准则,我们要力求遵守这些准则,并要竭诚地相信,我们越少于纵欲,就越能取悦于上帝。上帝排斥一切不是由他传授的知识,我们越少去研究他不想要我们知道的隐秘,他就会越快地用那神明的智慧为人类拨开茅塞。 我父亲没有对我谈起未婚夫的事,他说的只是,他 收到一封信,正在等待瓦西里公爵的访问。我亲爱的、珍贵的朋友,至于筹划我的婚姻一事,我要说给您听,在我看来,结婚是定当服从的教规。我认为无论这是多么沉重,但若万能的上帝要我担负贤妻良母的天职,我将竭尽全力,忠诚地履行这一天职,而我对上帝赐予我的男人怀有什么感情,我却无心去研究。 我已经收到长兄的一封来信,他向我提到他将和妻子一道来童山。这次欢乐的团聚为时是不长的,因为他快要离开我们去参与战斗,天知道我们如何和何故被卷入这场战争。不光是在你那儿——各种事件和社交的中心,而且在这儿——在田间劳作和市民平常所想象的农村的寂静中,也传来战争的回声,也令人心情沉重。我父亲只知道谈论我丝毫也不明了的南征北战的情形。前天,当我照常在村庄的街道上漫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他们都是我们这里招募入伍的一批新兵……有必要去看看那些上前线的新兵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的情景,听听新兵和家属的啼哭!你想想,人类已经忘记了救世的天主以博爱和宽恕宿怨的教义训导我们,而人类竟把互相谋杀的伎俩看作主要的优点。 亲爱的,慈善的朋友,再见。愿那救世的天主和圣母赐予您神圣而万能的庇护。 玛丽 “Ah,vousexpédiezlecorrier,Princesse,moij’aidej á ex pe di ele mi en.J’a iec ris am apauv remere.”①布里安小姐面露微笑,用她那清脆、悦耳的嗓音说道,她说得很快,“r”音发得不准确。在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的凝神思索、愁闷而阴郁的气氛里,她带进了一种完全异样的轻佻而悦意的洋洋自得的神情。 -------- ①法语:啊,您就要把信寄出去,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信是写给我的可怜的母亲的。 “Princesse,ilfautquejevousprévienne,”她压低嗓门,补充说一句,“Le prin ce ae u uneal tercation,alter cation,”她说道,特别着重用法语腔调发“r”音,并且高兴地听她自己的语声,“unealtercationavecMichel Iva noff.I lest detr è smau vai sehu meur,trèsmorose.Soyez prèvenue,vous sauez.”① “Ah!chèreamie.”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答道,“Jevousaipriedenejamaismeprevenirde l’humeur dans la quel lese trouvem on père.Je ne me peromet spas de le juger,et je nevoud ruis pas que lesau tres lefas sent.”② -------- ①法语:公爵小姐,我得事先告诉您——公爵把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大骂了一顿。他的情绪不好,愁眉苦脸。我事先告诉您,您晓得…… ②法语:啊,我亲爱的朋友,我求您千万不要对我谈论父亲的心境吧。我不容许我自己评说他,我也不希望他人这样做。 公爵小姐看了一下钟,她发觉已经耽误了五分钟弹钢琴的时间,流露出惊惶的神色向休息室走去。按照规定的作息制度,十二点钟至两点钟之间,公爵休息,公爵小姐弹钢琴。 ------------------ 23 白发苍苍的侍仆一面坐在那里打瞌睡,一面静听大书斋里公爵的鼾声。住宅远处的一端,紧闭着的门户后面,可以听见杜塞克奏鸣曲,难奏的乐句都重奏二十次。 这时分,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和一辆轻便马车开到台阶前,安德烈公爵从轿式马车车厢里走出来,搀扶矮小的妻子下车,让她在前面走。白发苍苍的吉洪,头戴假发,从堂倌休息间的门里探出头来,轻言细语地禀告:公爵正在睡觉,随即仓忙地关上了大门。吉洪知道,无论是他儿子归来,还是出现非常事故,都不宜破坏作息制度。安德烈公爵像吉洪一样对这件事了若指掌。他看看表,似乎想证实一下他离开父亲以来父亲的习惯是否发生变化。当他相信父亲的习惯没有改变之后,便转过脸去对妻子说: “过二十分钟他才起床。我们到公爵小姐玛丽亚那里去吧。” 他说道。 在这段时间以来,矮小的公爵夫人可真长胖了,但是当她开腔的时候,那双眼睛抬了起来,长有茸毛的短嘴唇微露笑意,向上翘起来,一望便令人欣快,讨人喜爱。 “maisc’estunpalais.”①她向四周打量一番,对丈夫说道,那神态就像跳舞会的主人被人夸耀似的,“Allons,vite,vite!…”②她一面回顾,一面对吉洪、对丈夫、对伴随她的堂倌微露笑容。 “C’estmariequisexerce?Allonsdoucement,il faut la sur pren dre.”③ -------- ①法语:这真是皇宫啊! ②法语:喂,快点吧,快点吧!…… ③法语:是玛丽亚在练钢琴吗?我们不声不响地走过去,省得她望见我们。 安德烈公爵面露恭敬而忧悒的表情,跟在她后面走去。 “吉洪,你变老了。”他走过去,一面对吻他的手的老头子说道。 在那可以听见击弦古钢琴声的房间前面,一个貌美的长着浅色头发的法国女人从侧门跳出来。布里安小姐欣喜欲狂了。 “Ah!quelbonheurpourlaprincesse,”她说道“Enfin!I lfaut que je la pre vi enne.”① “Non,non,degrace…VousêtesM—lleBourien ne,je vous con nai sd é jà parl’ ami tie quevous portemabl le- soeur.”公爵夫人和她接吻时说道,“El len en ousat tend pas!”② -------- ①法语:公爵小姐该会多么高兴啊!毕竟是来了!应该事先告诉她。 ②法语:不,不,真是的……您可就是布里安小姐,我的儿媳妇是您的好朋友,我已经认识您了。她没料想我们来了。 他们向休息室门前走去,从门里传出反复弹奏的乐句。安德烈公爵停步了,蹙了蹙额头,好像在等待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似的。 公爵夫人走进来,乐句奏到半中间就停止了,可以听见叫喊声,公爵小姐玛丽亚的沉重的步履声和接吻的声音。当安德烈公爵走进来的时候,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拥抱起来了,她们的嘴唇正紧紧贴在乍一见面就亲嘴的地方,她们二人只是在安德烈公爵举行婚礼时短暂地会过一次面。布里安小姐站在她们身边,两手扪住胸口,露出虔诚的微笑,看起来,无论是啼哭还是嘻笑,她都有充分准备。安德烈公爵像音乐爱好者听见一个走调的音那样,耸了一下肩膀,蹙了一下眉头。两个女人把手放开了,然后,仿佛惧怕迟误似的,她们又互相抓住一双手,亲吻起来,放开两只手又互相吻吻脸皮。她们哭起来了,哭着哭着又亲吻起来,安德烈公爵认为这是出人意料的事。布里安小姐同样地哭了。看来安德烈公爵感到尴尬,但是在这两个女人心目中,她们的啼哭是很自然的。显然,她们并不会推测,这次见面会搞出什么别的花样。 “Ah!chère…Ah!marie…”两个女人忽然笑起来,开口说道,“J’airêvé cet ten uit … Vous ne nou sat ten diez don cpas?… Ah!Marie,vousa vez maig ri… E tvou sa vez repris…”① “J’aitoutdesuitereconnumada mel aprin ces se,”②布里安小姐插上一句话。 “Etmoiquinemedoutaispas!…”公爵小姐玛丽亚惊叫道,“Ah!André,je nevous voyais pas.”③ 安德烈公爵和他的妹妹手拉手地互吻了一下,他对她说,她还像过去那样是个pleurnicheuse。④公爵小姐玛丽亚向她的长兄转过脸去,这时她那对美丽迷人的、炯炯发光的大眼睛透过一汪泪水,把那爱抚、柔和、温顺的目光投射到长兄的脸上。 -------- ①法语:啊!亲爱的!……啊!玛丽!……我梦见……——您没料想到我们会来吧?……啊!玛丽,您变得消瘦了,——以前您可真胖啦! ②法语:我立即认出了公爵夫人。 ③法语:我连想也没有想到!……啊!安德烈,我真没看见你哩。 ④法语:好哭的人。 公爵夫人不住地絮叨。她那长着茸毛的短短的上唇时常飞快地下垂,随意地触动一下绯红色的下唇的某一部分,之后她又微微一笑,露出皓白的牙齿和亮晶晶的眼睛。公爵夫人述说他们在救主山经历过一次对她怀孕的身体极为危险的遭遇,随后她立刻谈起她将全部衣服都留在彼得堡了,天晓得她在这里要穿什么衣服,她还谈起安德烈完全变样了,吉蒂·奥登佐娃许配给一个老年人,公爵小姐玛丽亚有个pourtoutdebon①未婚夫,这件事我们以后再叙。公爵小姐玛丽亚还是默不作声地望着长兄,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流露出爱意和哀愁。可见,萦绕她心头的思绪此时不以嫂嫂的言论为转移。嫂嫂谈论彼得堡最近举行的庆祝活动。在谈论的半中间,她向长兄转过脸去。 “安德烈,你坚决要去作战吗?”她叹息道。 丽莎也叹了一口气。 “而且是明天就动身。”长兄答道。 “Ilm’abandonneici,etDieusaitpourquoi,quandilau Brait pua voi rde l’ av an ce ment…”② -------- ①法语:真正的。 ②法语:他把我丢在这里了,天晓得,目的何在,而他是有能力晋升的…… 公爵小姐玛丽亚还在继续思索,没有把话儿听完,便向嫂嫂转过脸来,用那温和的目光望着她的肚子。 “真的怀孕了吗?”她说道。 公爵夫人的脸色变了。她叹了一口气。 “是的,真怀孕了,”她说道,“哎呀!这很可怕……” 丽莎的嘴唇松垂下来。她把脸盘凑近小姑的脸盘,出乎意料地又哭起来了。 “她必需休息休息,”安德烈公爵蹙起额角说,“对不对,丽莎?你把她带到自己房里去吧,我到爸爸那儿去了。他现在怎样?还是老样子吗?” “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个老样子,不晓得你看来他是怎样。”公爵小姐高兴地答道。 “还是在那个时间,照常在林荫道上散步吗?在车床上劳作吗?”安德烈公爵问道,几乎看不出微笑,这就表明,尽管他十分爱护和尊敬父亲,但他也了解父亲的弱点。 “还是在那个时间,在车床上劳作,还有数学,我的几何课。”公爵小姐玛丽亚高兴地答道,好像几何课在她生活上产生了一种极为愉快的印象。 老公爵起床花费二十分钟时间之后,吉洪来喊年轻的公爵到他父亲那里去。老头为欢迎儿子的到来,破除了生活方式上的惯例:他吩咐手下人允许他儿子在午膳前穿衣戴帽时进入他的内室。公爵按旧式穿着:穿长上衣,戴扑粉假发。当安德烈向父亲内室走去时,老头不是带着他在自己客厅里故意装的不满的表情和态度,而是带着他和皮埃尔交谈时那种兴奋的神情,老年人坐在更衣室里一张宽大的山羊皮面安乐椅上,披着一条扑粉用披巾,把头伸到吉洪的手边,让他扑粉。 “啊!兵士!你想要征服波拿巴吗?”老年人说道,因为吉洪手上正在编着发辫,只得在可能范围内晃了晃扑了粉的脑袋,“你好好收拾他才行,否则他很快就会把我们看作他的臣民了。你好哇!”他于是伸出自己的面颊。 老年人在午膳前睡觉以后心境好极了。(他说,午膳后睡眠是银,午膳前睡眠是金。)他从垂下的浓眉下高兴地斜着眼睛看儿子。安德烈公爵向父亲跟前走去,吻了吻父亲指着叫他吻的地方。他不去回答父亲中意的话题——对现时的军人,尤其是对波拿巴稍微取笑一两句。 “爸爸,是我到您跟前来了,还把怀孕的老婆也带来,”安德烈公爵说道,他用兴奋而恭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每根线条流露的表情,“您身体好么?” “孩子,只有傻瓜和色鬼才不健康哩,你是知道我的情况的:从早到晚都忙得很,饮食起居有节制,真是够健康的。” “谢天谢地!”儿子脸上流露出微笑,说道。 “这与上帝无关!欸,你讲讲吧,”他继续说下去,又回到他爱谈的话题上,“德国人怎样教会你们凭藉所谓战略的新科学去同波拿巴战斗。” 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爸爸,让我醒悟过来吧,”他面露微笑,说道,这就表示,父亲的弱点并不妨碍他对父亲敬爱的心情,“我还没有安顿下来呢。” “胡扯,胡扯,”老头子嚷道,晃动着发辫,想试试发辫编得牢固不牢固,一面抓着儿子的手臂,“你老婆的住房准备好了。公爵小姐玛丽亚会领她去看房间,而且她会说得天花乱坠的。这是她们娘儿们的事。我看见她就很高兴啊。你坐下讲讲吧。米切尔森的军队我是了解的,托尔斯泰……也是了解的……同时登陆……南方的军队要干什么呢?普鲁士、中立……这是我所知道的。奥地利的情况怎样?”他从安乐椅旁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方步,吉洪跟着他跑来跑去,把衣服送到他手上,“瑞典的情况怎样?他们要怎样越过美拉尼亚呢?” 安德烈公爵看见他父亲坚决要求,开头不愿意谈,但是后来他越谈越兴奋,由于习惯的关系,谈到半中间,情不自禁地从说俄国话改说法国话了,他开始述说拟议中的战役的军事行动计划。他谈到,九万人的军队定能威胁普鲁士,迫使它放弃中立,投入战争,一部分军队必将在施特拉尔松与瑞典军队合并;二十二万奥国军队和十万俄国军队合并,必将在意大利和莱茵河上采取军事行动,五万俄国军队和五万英国军队必将在那不勒斯登陆;合计五十万军队必将从四面进攻法国军队。儿子述说的时候,老公爵没有表示一点兴趣,好像不听似的,一边走路一边穿衣服,接连有三次出乎意外地打断儿子的话。有一次制止他说话,喊道: “白色的,白色的!” 他的意思是说吉洪没有把他想穿的那件西装背心送到他手上。另一次,他停步了,开口问道: “她快要生小孩吧?”他流露出责备的神态,摇摇头说道,“很不好!继续说下去,继续说下去。” 第三次,在安德烈公爵快要叙述完毕的时候,老年人用那假嗓子开始唱道:“Mal broug,s’en vo— t— en guer re.Dieu sait quand revien dra.”① 儿子只是微微一笑而已。 -------- ①法语:马尔布鲁去远征,天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我不是说,这是我所称赞的计划,”儿子说道,“我只是对您讲讲有这么一个计划。拿破仑拟订了一个更好的计划。” “唉,你没有说出一点新消息,”老年人沉思,像放连珠炮似地喃喃自语:“Dieusaitquandreviendra,”又说:“去餐厅里吧。” ------------------ 24 在那规定的时刻,老公爵扑了香粉,刮了脸,走到餐厅里去,儿媳妇、公爵小姐玛丽亚、布里安小姐和公爵的建筑师都在这里等候他。出于公爵的怪癖,这位建筑师竟被准许入席就座,这个渺小的人物就地位而论,是决不能奢求这种荣幸的。公爵在生活上坚定地遵守等级制度,甚至省府的达官显贵也很少准许入席就座。那个常在角落里用方格手帕擤鼻涕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忽然被准许入席就座了,公爵用他这个惯例来表明,人人一律平等,他不只一次开导女儿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没有一点不如我们的地方。在筵席间,公爵常和寡言鲜语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开心畅谈。 这餐厅又高又大,和住室里所有的房间不相上下,家眷和堂倌在每把椅子背后站着,等候公爵走出门来;管家的手上搭着餐巾,他环视着餐桌的摆设,向仆役使眼色,不时地把激动不安的目光从挂钟移向公爵即将出现的门口。安德烈公爵端详着一副他初次看见的金色大框架,框架里面放着博尔孔斯基公爵家的系谱表,对面悬挂着一样大的框架,里面放着一副做工蹩脚的(显然是家庭画师的手笔)享有世袭统治权的公爵的戴冕画像,他一定是出身于留里克家族,即是博尔孔斯基家的始祖。安德烈公爵看系谱表时摇摇头,不时地暗自微笑,那神态就像他看见一副俨像自己的肖像而觉得可笑似的。 “我在这儿认出是他啊!”他对向他身边走来的公爵小姐玛丽亚说道。 公爵小姐玛丽亚惊奇地望望她的哥哥。她不明白他在暗笑什么。父亲所做的一切在她身上激起一种无法评论的敬意。 “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以他那卓越的的才智,don ners dan sceri dicule!”① -------- ①法语:竟然受制于这等琐事。 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无法理解长兄提出的大胆的见解,她准备向他反驳,书斋里忽然传出人人期待的步履声,公爵像平素一样迈着急速的脚步,高高兴兴地走进门来,仿佛蓄意用那来去匆匆的样子和严格的家庭秩序形成相反的对比。正在这一转瞬之间,大钟敲响了两声,客厅里的另一只钟用那尖细的声音作出了响应。公爵停步了。他那炯炯有神、富于表情而严峻的目光从垂下的浓眉下向大家环顾一番,然后投射在年轻的公爵夫人身上。年轻的公爵夫人这时感觉到一种有如近臣见皇帝出朝时的感情;也就是这位老人使他的心腹产生的一种敬畏之感。他用手摸了摸公爵夫人的头,然后呆笨地拍了一下她的后脑。 “我真高兴,我真高兴,”他说道,又聚精会神地望了一下她的眼睛,就飞快地走开,坐回自己的座位,“请坐,请坐!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坐。” 他向儿媳妇指了指身边的座位。堂倌给她移开椅子。 “嘿嘿!”老年人望着她那浑圆的腰部,说道,“太匆忙了,不好!” 他像平常那样只用嘴巴笑,而不用眼睛笑,他乏味地、冷漠而且不痛快地笑起来。 “你应当走动走动,尽量,尽量多走动。”他说道。 矮小的公爵夫人没有听见或是不想听他说话。她沉默不言,觉得困惑不安。公爵向她问到她的父亲的情况,公爵夫人于是微露笑容,开口说话了。他又向她问到一般的熟人的情况,公爵夫人现出更加兴奋的样子,开始述说起来,她代人向公爵问候,并且转告城里的流言飞语。 “LacomtesseApraksine,lapauvre,aperdusonmari,e tel leap leur è les lar mes de ses yeux,”①她说道,显得更加兴奋起来。 -------- ①法语:可怜的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丧失了丈夫,痛哭了很久,眼睛都哭坏了,可怜的女人。 她越来越显得兴致勃勃,公爵就越来越严肃地注视着她。公爵忽然转过脸去;不再理睬她,好像他已经把她研究得够多的了,对她已有明确的概念,他然后便向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转过脸去。 “喂,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我们的波拿巴要遭殃了。安德烈公爵(他向来都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儿子)告诉我,为了击溃他,聚集了多么雄厚的兵力啊!我们一向认为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谈论过波拿巴的事,可是他心里明白,人家有求于他,目的乃在于打开自己喜欢的话匣子。他诧异地望了望年轻的公爵,自己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产生何种结果。 “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位伟大的战术家!”公爵用手指着建筑师对儿子说。 谈话又涉及战争,涉及波拿巴和现时的将军以及国事活动家。看来,老公爵不仅相信,当前的政要人物全是一些不通晓军事和国务知识初阶的乳臭小子,波拿巴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法国佬,他所以大受欢迎,只是因为没有波将金或者苏沃洛夫式的人物和他对立罢了。他甚至相信,欧洲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障碍,也没有战争,只是一些现时的活动家装作一副办事的模样,演演木偶戏罢了。安德烈公爵愉快地忍受父亲对现代人的嘲笑,明显地露出高兴的神色,喊他父亲谈话,而他自己聆听着。 “过去的一切看来都是好的,”他说道,“那个苏沃洛夫岂不落进了莫罗布下的陷阱,无法自拔了么?” “是谁对你讲的呢?谁讲的呢?”公爵嚷道,“苏沃洛夫吧!”他扔开一只盘子,吉洪赶快将它接住。“苏沃洛夫吧!……安德烈公爵,想想吧。我知道有两个人:一个是腓特烈,一个是苏沃洛夫……莫罗呀!假如苏沃洛夫有权在握,莫罗该当俘虏了,不过他受制于军事参议院。他倒霉透了,鬼都讨厌他。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能尝到腊肠烧酒的滋味啊!苏沃洛夫无法制服他们,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又怎能应付呢?行不通,朋友,”他继续说下去,“你们和我们的将军们制服不了波拿巴,就得雇用一批法国人,让他们认不清自己人,自己人屠杀自己人。德国人帕伦被派往美国纽约去寻找法国人莫罗,”他说道,暗指当年聘请莫罗至俄军任职一事。“真怪!怎么啦,那波将金、苏沃洛夫、奥尔洛夫式的人物难道都是德国人吗?不是的,朋友,或者是你们都发疯了,或都是我已经昏瞆了。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来瞧瞧吧。在他们那儿,波拿巴竟然当上伟大的统帅了!哼!……” “我说的根本不是,他的指示都是可取的,”安德烈公爵说道,“不过,我没法弄明白,您怎能这样评说波拿巴。您想怎样嘲笑,就怎样嘲笑吧,而波拿巴仍然是个伟大的统帅!”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老公爵对那个开始吃烤菜、希望别人把他忘却的建筑师喊道,“我以前对您说过波拿巴是个伟大的战术家,是吗?您看,他也是这样说的。” “可不是,公爵大人。”建筑师答道。 公爵又冷笑起来。 “波拿巴生来有福分。他的士兵很精锐,而且他先向德国人进攻,只有懒人才不打德国人。自从宇宙存在以来,大家都打德国人。他们打不赢任何人。他们只晓得互相杀戮。他就足凭这一手闻名于世的。” 公爵于是就其看法开始分析波拿巴在战争乃至国务上所犯的过失,儿子不表示异议,但是可以看出,无论向他提出任何论据,他都像老公爵那样很难改变自己的看法。安德烈公爵谛听着,克制着不予辩驳,而且情不自禁地感到谅异,这个老年人足不出户在农村独处许多年,对近几年来欧洲的军事政治局势知晓得如此详尽,评述得如此精辟。 “你认为我这个老头儿不了解目前的事态吗?”他说了一句收尾的话。“我念念不忘时事啊!我彻夜目不交睫。嘿,你那个伟大的统帅究竟在哪里大显身手呀?” “这说来话长。”儿子答道。 “你到你自己的波拿巴那里去好了M—lleBourienne,voilàen coreu nad mi ra te ur de uo tregou jatd’em pereur!”①他操着非常漂亮的法国话,喊道: “Voussavez,que jenesuispas bonapar tiste,moprince.”② “OieuSaitquandneviendva…”③公爵不自然地唱道,更加不自然地发笑,从餐桌后面走出来。 在争辩和不争辩的午膳的其余时间里,矮小的公爵夫人默不作声,时而惊惶不安地望望公爵小姐玛丽亚,时而望望老公公,在她从桌子后面走出来时,她一把抓住小姑的手臂,把她喊进另一个房间里。 “Commec’estunhommed’espritvotre,”她说道,“C’estàcausedecelapeut—êtreqúilmefaitpeur.”④“啊,他太慈善了!”公爵小姐玛丽亚说道。 -------- ①法语:布里安小姐,你那个奴才般的皇帝又有一个崇拜者了。 ②法语:公爵,您知道,我不是波拿巴份子啊。 ③法语:天知道什么时候他才回来。 ④法语:您爸爸是个很聪明的人,也许因为这种缘故我才害怕他。 ------------------ 25 第二天黄昏,安德烈公爵要动身了。老公爵遵守生活秩序,午膳后走回自己房里去了。矮小的公爵夫人呆在小姑房里。安德烈公爵穿上旅行常礼服,没有佩戴带穗肩章,在拨给他住的房间里和他的侍仆一同收拾行装。他亲自察看了马车,把手提箱装进车厢,嗣后吩咐套马车。房里只剩下一些安德烈平日随身带着的物品:一只小匣子、一只银质旅行食品箱、两支土耳其手枪和一柄军刀——从奥恰科夫运来的父亲赠送的物品。安德烈公爵的全部旅行用品摆放得齐齐整整,完整无缺,全是崭新的,十分干净的,罩上了呢绒套,并用小带子仔细地捆住。 在即将动身和改变生活规律的时刻,凡善于反思自己行为的人常常会产生一种忧闷的心绪。在这种时刻,他们通常是检查往事,制订长远规划。安德烈公爵脸部流露出沉思和感伤的表情。他把手放在背后。从房间的一角向另一角迈着疾速的脚步,张开眼睛向身前望去,沉思默想地晃着脑袋。他莫非是害怕上战场,抑或是离开妻子而忧心忡忡,——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显然,他只是不想让人家望见他有这种心境;他听见门斗里的步履声,就连忙放开倒背着的手,在桌旁停步了,好像正在捆扎匣子上的布套,脸上带有平常那种宁静和神秘莫测的表情。这时分,可以听见公爵小姐玛丽亚的沉重的步履声。 “有人告诉我,你已经吩咐套马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显然她是跑步来的),“我心里很想和你单独地再谈一会。天知道我们又要别离多久啊。我走来,你不发脾气吧?安德留沙,你变得厉害啊。”她补充一句话,好像要解释这句问话似的。 她喊“安德留沙”这个名字时,脸部微露笑容。看来,她想到这个严肃的俊美的男人,正是那个消瘦的调皮的安德留沙,她幼年时代的朋友,心里觉得十分奇怪。 “丽莎在哪儿?”他问道,只以微微一笑来回答她的问话。 “她觉得非常疲倦,在我房里的长沙发上睡着了。啊,Andrè!Qué ltre son de fem me vou savez,”①她说道,一面在长兄对面的长沙发上坐下。“她完全是个小女孩,一个可爱的愉快的小女孩。我很喜爱她。” 安德烈公爵默不作声,可是公爵小姐发现他脸上流露出嘲讽的鄙夷的表情。 “应当宽宏大量地对待一些小缺点,安德烈,谁会没有缺点啊!你不要忘记,她是在上流社会中教育、长大成人的。而且她目前的境遇并不幸福。应当同情每个人的处境。Tout compren dre,c’est toutpar donner,②你想想,她过惯了这种生活之后,怎么能够和丈夫离别,孤零零地呆在农村,而且怀了孕,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心里有什么感受?这是非常痛苦的。” -------- ①法语:安德烈,你的妻子太可贵了。 ②法语:谁能理解一切,谁就会宽恕一切。 安德烈公爵望着妹妹,脸上露出笑意,就像我们听到我们似乎看透了的那些人说话时面露笑容一样。 “你在农村生活,可是你并不认为这种生活可怕。”他说道。 “我就不一样了。干嘛要谈论我啊!我不企求别的生活,而且不能抱有这种心愿,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安德烈,你要想想,一个年轻轻的上流社会的女人,在大好年华,孑然一人匿身于农村,因为爸爸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我……你是知道我的情况的……对一个习惯于上流社会生活的女人来说,我是多么可怜,多么enresources①,唯独布里安小姐……” “我极不喜欢您那个布里安。”安德烈公爵说道。 “啊,不对,她很可爱,又和善,主要是,她是一个不幸的姑娘。她没有任何亲人。老实说,我不仅不需要她,而且她使我感到不方便。你知道我一向是个野蛮人,现在变本加厉了。我喜欢独处……monpeve②很喜欢她。爸爸亲热而慈善地对待这两个人——她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因为他们二人都获得他的恩泽,斯特恩说,我们与其爱那些向我们布善的人,毋宁爱那些领受我们布善的人。monpeve收留了她这个surlepavé③的孤儿。她十分和善,喜欢她朗读的风度。她每逢夜晚给他朗读。她读得非常动听。” -------- ①法语:不快活。 ②法语:爸爸。 ③法语:被遗弃于街头。 “嘿,玛丽,说真的,我认为父亲的性情有时会使你觉得难受,对不对?”安德烈公爵忽然问道。 公爵小姐玛丽亚先是大为惊讶,然后就害怕他这句问话。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难受?”她说道。 “我认为,他一向都很专横,现在变得难以共处了。”安德烈公爵说道,看来他故意使妹妹难堪,或者想试探一下,才这样轻率地评论父亲的。 “你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安德烈,可是你有点自傲,”公爵小姐说道,她不太注意谈话的进程,过多地注意自己的思路,“这真是一大罪孽。岂可评论父亲?即令是可以,而像monpeve这样的人,只能令人vénération,”①,哪能引起另一种感情?与他相处,我很满意,很幸福!我只希望你们都像我这样幸福。 长兄疑惑地摇摇头。 “安德烈,有一件事使我觉得难受,我如实地告诉你,那就是父亲在宗教方面的观点。我不明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怎能看不清显而易见的事,怎能误入迷途?这就是我的一大不幸。但是我近来看见了他有改善的迹象。近来他的嘲讽不那么恶毒了。有个僧侣来拜门,他接见了僧侣,并且一同谈了很久的话。” “啊,我的亲人,我怕您和僧侣都白费劲。”安德烈公爵嘲讽地,但却亲热地说道。 “Ah!monami,②我只是祷告上帝,希望他能听见我的祷告,安德烈,”沉默片刻之后她羞怯地说道:“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求你。” -------- ①法语:崇拜。 ②法语:啊,我的朋友。 “我的亲人,求我做什么事?” “请你答应我,你不会拒绝我的请求。在你心目中,这件事不用费吹灰之力,也不会使你有损于身分。你只是安慰我而已。安德留沙,请你答应吧,”她说了这句话便把手伸进女式手提包里,拿着一样东西,但是不让别人望见,好像她手上拿的东西正是她所请求的目标,在她的请求尚未获得允诺之前,她是不能从女式手提包里取出这样东西的。 她用央求的目光羞羞答答地望着长兄。 “即使我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安德烈公爵答道,仿佛要猜中是怎么回事。 “你随意想什么都行!我知道你和monpeve都是同样的人。你随意想什么都行,可是你要替我办这件事。请你办妥这件事!我父亲的父亲,即是我们的祖父在南征北战中都随身带着这样东西……”她依旧没有从女式手提包里取出她手里拿着的东西。“你会答应我吗?” “当然,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安德烈,我用神像为你祝福,你要答应我你永远不会把它取下来……答应吗?” “既然它的重量不到两普特,就不会压疼脖子……要让你愉快……”安德烈公爵说道,但是,一当他发现妹妹听了这句戏言,脸上就流露出忧伤的神情,他顿时后悔起来,“我非常高兴,我的确十分高兴,我的亲人。”他补充一句。 “上帝必将依据你的意志拯救你,保佑你,使你倾向他,唯有在他身上才能获得真理和安慰,”她用激动得颤栗的嗓音说道,在长兄面前庄重地捧着一帧救世主像。这帧古式神像呈椭圆形,面色黧黑并饰以银袍,身上系有一条银链。 她在胸前画十字,吻了吻神像,便把它递给安德烈。 “安德烈,请你保存,为我……” 她的一双大眼睛善良而且羞怯地炯炯发光。这双大眼睛照耀着她那瘦削的病态的面孔,使它变得十分美丽了。长兄想要伸手去拿神像,但是她把他拦住了。安德烈心里明白,他便在胸前画了十字,吻了一下神像。同时他脸上带有温和(他深受感动)和嘲笑的表情。 “mercimonami.”① -------- ①法语:我的朋友,我感谢你。 她吻吻他的额头,又在长沙发上坐下来。他们都沉默不言。 “安德烈,我对你说过,你要像平常那样慈善、宽宏大量,不要严厉地责难丽莎,”她开始说道,“她很可爱,很和善,目前她的境况非常困难。” “玛莎,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对你说起我责备妻子或者对她表示不满的话。你干嘛老对我说起这件事呢?” 公爵小姐玛丽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沉默起来了,仿佛觉得自己有过错似的。 “我一点也没有对你说,不过有人对你说了。这真使我伤脑筋。” 公爵小姐玛丽亚的额头、颈项和两颊上的斑斑红晕显得更红了。她心里很想说点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长兄猜中了,午饭后矮小的公爵夫人哭了一顿,说她预感到不幸的分娩,她害怕难产,埋怨自己的命运,埋怨老公公和丈夫。她痛哭一顿以后就睡着了。安德烈公爵怜悯起妹妹来了。 “玛莎,你要知道是这么回事,我没有什么可责备妻子的,以前没有责备,以后也永远不会责备她,在我对她的态度上,我并没有什么可责怪自己的地方。无论我处在何种情况下,我永远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很想知道真相,……你想知道我是否幸福?我并不幸福。她是否幸福?也不幸福。这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 他说话时,站起身来,走到他妹妹面前,弯下腰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他那美丽的眼睛放射出不常见的明智而和善的光芒,但是,他并不望他妹妹,而是逾越她的头部望着黑洞洞的敞开的门户。 “我们到她那里去吧,应当向她告辞了!要不然,你一个人去吧,把她喊醒,我马上就来。彼得鲁什卡!”他向侍仆喊道,“到这里来,收拾东西吧。这件要放在座位里边,这件要放在右边。” 公爵小姐玛丽亚站起身来,向门边走去。这时她停住脚步了。 “André,sivousavezlafoi, vousvousseriezadresséàDieu, pour qu’il vous don ne l’am our quevou sne sen te zpas, etvotre prie reau rai te te exau ce e.”① “是啊,真有这种事吗!”安德烈公爵说道,“玛莎,你去吧,我立刻就来。” 安德烈公爵去妹妹房间的途中,在连结甲乙两幢住宅的走廊里,碰见了笑容可掬的布里安小姐,是日她已经第三次露出天真而喜悦的笑意在冷冷清清的过道上和他邂逅相遇了。 “Ah!jevouscroyaischezvous,”②她说道,不知怎的涨红了脸,低垂着眼睛。 -------- ①法语:安德烈,如果你有一种信仰,你就会祈祷上帝,要他赐予你那种体会不到的爱,要上帝能听到你的祷告。 ②法语:啊,我原来以为您在自己房里哩。 安德烈公爵严肃地瞟了她一眼,脸上顿时流露出狂怒的神色,他什么话也没有对她说,不屑望望她的眼睛,只朝她的额角和头发瞥视一下,眼神是那么鄙夷,以致这个法国女人满面通红,她一言未发便走开了。当他行走到妹妹门口的时候,公爵夫人睡醒了,门户洞开,从里面传来她那愉快的上句紧扣下句的话语声。她说起话来,就像长时间克制之后,现在很想要补偿失去的时光似的。 “Non,maisfigurezvous,lavieillecomtesse Zou bof fa vec de faus ses bou cle set labou chep leine de faus sesdents, commesiel levou lait de fier le san ne es…①玛丽,哈,哈,哈!” 安德烈公爵约莫有五次听见他妻子在旁人面前说伯爵夫人祖博娃的一些同样的闲话,还听见一串串同样的笑声。他悄悄地走进房来。略嫌肥胖、面颊绯红的公爵夫人坐在安乐椅上,手里拿着针线活儿,不住声地说话,一桩桩、一件件回忆彼得堡的往事,甚至回忆一句句的原话。安德烈向她跟前走来,摸摸她的头,问她旅途之余是不是得到休息。她应声回答,又继续说下去了。 -------- ①法语:不,你设想一下,老伯爵夫人祖博娃长着一头假发,一口假牙,好像在嘲笑自己的年纪似的…… 六套马的四轮马车停在台阶前面。外面正是昏暗的秋夜。车夫望不见马车的辕轩。人们都手提灯笼在门廊里忙忙碌碌。一幢雄伟的住宅透过一扇扇高大的窗户反射出耀眼的灯光。仆人们都聚集在接待室里想跟年轻的公爵告别;家属: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里安小姐、公爵小姐玛丽亚和公爵夫人,一个个站在大客厅里。安德烈公爵被人叫到书斋去见父亲,父亲很想单独地跟他告别,他们正在等待着父子走出门来。 安德烈公爵走进书斋时,老公爵戴上老年人用的眼镜,穿着一件洁白的长衫,除开会见儿子之外,他从未穿过这件长衫接见任何人,这时公爵正坐在桌旁写字。他掉过头来望一眼。 “你要走了吗?”他又握着笔管写起字来。 “我来告辞了。” “吻我这里吧,”他指指面颊,“谢谢,谢谢!” “您为什么要谢我?” “因为你没有稽延多日,没有纠缠着女人的衣裙。服兵役第一。谢谢,谢谢!”他继续写字,墨水飞溅,笔尖沙沙地作响。“若是要说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可以同一时间做两件事。” 他补充一句。 “关于我的老婆……我把她留了下来让您老人家操劳,我实在不好意思……” “你瞎说什么?说你该说的话吧。” “我老婆分娩的时候,请您派人去莫斯科请个产科男医生……叫他到这里来。” 老公爵停住了,好像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用严肃的目光凝视他儿子。 “我知道,假如大自然帮不了忙,那就没有谁能帮上忙的,”安德烈公爵说道,看来他感到困惑不安,“我所赞成的是,一百万件事例中通常只有一件是不幸的,但是,这真是她的幻觉,也是我的幻觉。别人对她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她做了恶梦,因此她心里十分畏惧。” “嗯……嗯……”老公爵喃喃地说,一面继续把信写完,“我一定办妥。” 他签了字,忽然很快地把脸转向儿子,哈哈大笑了。 “事情糟糕透了,不是吗?” “爸爸,什么事情糟糕透了?” “你的老婆呀!”老公爵三言两语地、但却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不明了。”安德烈公爵说道。 “亲爱的人,这真是毫无办法的,”公爵说道,“她们都是一路的货色,是离不成婚的。你不要害怕,我决不对人说,可是你自己要知道。” 他用那瘦骨嶙峋的小手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臂,晃了一下,用那仿佛是要把人看透的目光朝着儿子的面孔飞快地扫了一眼,然后又冷冷地笑了。 他儿子叹了一口气,表示他已承认父亲了解他。老年人用那习惯的敏捷的动作继续折叠并封上几封信,他飞快拿起火漆、戳子和信纸,之后又搁下来。 “怎么办。长得俊俏嘛!一切我都办妥,你放心好了。”他在封信时若断若续地说道。 安德烈沉默不言,父亲了解他,这使他觉得愉快,又觉得不愉快。老年人站起身来,把信递给他儿子。 “你听我说,”他说道,“不要替老婆操心,凡是可能办到的事,都一定办到。你听着:把这封信转交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我在信上写了,要他任用你,谋个好差事,不要让你老是当个副官,糟糕透了的职务啊!你告诉他,我还记得他,而且喜爱他。他怎样接待你,以后来信告诉我。假如他待人厚道,就干这个差事吧。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儿子因为不受恩赐,所以不肯在任何人麾下任职。喂,现在到这里来。” 他像放连珠炮似地说话,说不到半句就说完了,可是他儿子已经听惯了,懂得他的意思。他把他儿子领到旧式写字台前面,启开盖子,拉出写字台的抽屉,取出一个笔记本,他把这个笔记本写满了又粗又长又密的小字。 “我想必会死在你前头。你听我说,这里是我的回忆录,在我去世后,把它呈送国王,这里有一张债券和一封信:这里有奖励《苏沃洛夫战史》著述者的一笔奖金。把这些东西寄到科学院去。这里是我的诠注,在我去世后,你自己可以浏阅,从其中获得裨益。” 安德烈没有对父亲说,他想必还能活很久。他心里明白,这种话是用不着说的。 “爸爸,这一切我都能办妥。”他说道。 “好啦,再见吧!”他让他儿子吻吻他的手,然后拥抱自己的儿子。“安德烈公爵,有一点你要牢记在心,如果你被敌人打死,我这个老头子会感到非常悲痛的……”他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突然他用尖锐刺耳的嗓音继续说,“如果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的儿子,我就会……感到汗颜!”他突然用那小尖嗓儿叫了一声。 “爸爸,您可以不对我说这种话。”儿子面带微笑地说道。 老年人默不作声了。 “我还有求于您,”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如果我被敌人打死,如果我将来有个儿子,请让他留在您身边,不要他离开,正如我昨天对您说的那样,让他在您这儿成长……请您照拂一下。” “不把儿子交给老婆吗?”老年人说了这句话,大笑起来。 他们沉默不言,面对面地站着。老年人的敏锐的目光逼视着儿子的眼睛。老公爵的面颊的下部不知怎的颤抖了一下。 “辞别已经完毕了……你走吧!”他忽然说道。“你走吧!” 他把书斋门打开,提高嗓门怒气冲冲地喊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啦?”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望见了安德烈公爵和那身穿白长衫、未戴假发、戴着一副老年人用的眼镜、愤怒地吼叫的老年人匆匆探出来的身子,于是问道。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一声也没有回答。 “好啦,”他向妻子转过脸去说道。“好啦”这个词含有冷嘲热讽的意味,好像他是说:“您现在耍耍您的招儿吧。” “Andredeja?”①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她脸色惨白,恐惧地望着丈夫。 他搂抱她。她尖叫一声,不省人事地倒在他的肩膀上。 他很小心地移开被她枕着的那只肩膀,望了望她的面孔,爱抚地扶她坐在安乐椅上。 “Adieu,marie,”②他轻声地对他妹妹说道,他和她互相吻吻手,从房里飞快走出来。 -------- ①法语:安德烈,怎么,告别完了吗? ②法语:玛丽亚,再见吧。 公爵夫人躺在安乐椅上,布里安小姐给她揉搓太阳穴。公爵小姐玛丽亚搀扶嫂嫂,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泪痕斑斑,还在望着安德烈公爵从那里走过的门口,她画着十字,为公爵祈祷祝福。书斋里多次地传出老头子的怒气冲冲的像射击似的擤鼻涕的声音。安德烈公爵刚刚走出去,书斋门很快就敞开了,从门里露出那个穿白色长衫的老年人的威严的身影。 “他走了吗?那就好了!”他说道,愤怒地望望不省人事的个子矮小的公爵夫人,他露出责备的神态摇摇头,砰的一声关上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