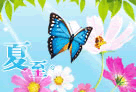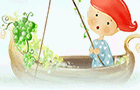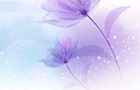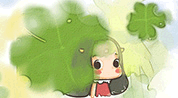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王莫之,一九八二年生于上海。作家,编辑,乐评人。二〇一二年开始发表小说,中短篇作品散见于《收获》《花城》《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出版长篇小说《现代变奏》《安慰喜剧》。
为萨克斯写的蓝色情歌 文/王莫之 Y没念过大学,但我们都认为他是文化人。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写过一百多首流行歌曲,全都录成了唱片(那种七十八转的粗纹黑胶,又重又脆易损坏,单面只有一首歌),演唱者多为旧社会的巨星,如周璇、姚莉、白光等等。 我们平时聚会,很喜欢向Y讨教一些涉及他父亲的老黄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我也不晓得。” 他是真不晓得。他在当父亲之前都不晓得自己的父亲以前是炮制流行歌曲的圣手,不得不说,这与他的年纪有一定的关系。Y是Y父最小的孩子,出生于一九六三年,当时Y父五十四岁,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外公了。那两个小把戏每次来铜仁路看望外公,见到Y还得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小娘舅,见到Y母不叫外婆,而是淡淡地喊一声阿婆,然后像哥哥姐姐那样领着Y到弄堂里玩。出了家门,打弹珠,拍香烟牌,彼此直呼姓名。 小时候的事情Y不愿意多讲,有啥好讲的,讲出来无非是大同小异。他就记得三岁时有一天家里突然闯进来一群陌生人,他被丢在父母睡的那张床上,像个废弃的布娃娃。我们问他当时是何反应,他说:“没啥反应,就是巴瞪巴瞪地看着他们。” 两年后,Y父从静安区军管组收到了一纸判决书。在Y的童年回忆里,父亲经常埋首案头,用笔尖蛮粗的钢笔,蘸蓝墨水,愁眉苦脸地写着汇报材料,一写就是很厚一沓,写完交到居委会。汇报材料好像永远都写不完,就像为弄堂义务打扫卫生每周都要去,Y父对着案头坐久了,有时笔头与思绪打架,他点一支勇士牌的香烟闷几口,对着窗外发呆。有一次,他见Y回来了,把窗户开得更大一些,好让烟气尽快散去。 “爸爸,你又在画图啊?”Y抬头问道。 “乖囡,爸爸帮你画个小白兔好吗?” Y点点头。Y父把他抱到自己的大腿上,握着他的小手,还有一支笔头更粗的美工笔,蘸红墨水,在纸上寥寥几笔,画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多年以后,这只小白兔成了Y父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九年,Y中学毕业,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都进了高中,他没考好,只能去读技校。他为此冲着父亲,发了点小脾气:“你为啥没从小培养我?” “啥?” “你是画家呀,你如果从小就教我画图,我以后也应该是画家。” “画图还要教啊?自己看呀,自己学呀,自己练呀。” Y不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社、杂志社、报社陆续恢复了与Y父的合作,各地的编辑写信或者打电话来约他的插画;好些故友也恢复了走动,重新踏进铜仁路的弄堂,拎着东西,把木头楼梯踩得嘎吱嘎吱响,上二楼,敲Y家的门。这些人,Y基本上毫无印象,反倒是会被他们调侃几句:“你不记得啦,你小的时候,我抱过你的。”然后他就得往自己的嘴唇上抹一层蜜,管那些爷爷辈的叫阿叔、伯伯。这些白发苍苍的长辈以美术界人士为主,也有一些是文学圈的,搞音乐的比较少。讲句心里话,Y还是挺乐意见到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出现总是跟下午茶这件事情前脚碰后脚。有时客人有备而来,有时Y母非常自觉地出门去买;无非是一些海派西点,比如白脱蛋糕、哈斗、牛利等等。Y跟着沾光,从那时起也认同喝咖啡是一种身体需要。Y父喝咖啡很少配西点,顶多吃一个哈斗;比起哈斗,老先生对烟斗更来劲。Y第一次见父亲抽烟斗的时候,还傻兮兮地问呢:“爸,你买了一只烟斗啊?” “没,买了几十年了。” Y父不仅烟瘾大,还喜欢给朋友发香烟。他邀请朋友一道吞云吐雾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呛儿子几句:“拿两块到隔壁去吃,我们要吃香烟了,你跑开点。” Y不响,继续吃点心,喝咖啡,当钉子户。他很愿意钉在客厅的某个角落,默默地听长辈们追忆逝水年华,虽然完全不晓得他们在说些什么,感慨些什么,但是那种偷听的感觉特别美好。他非常清楚,赖在这间屋子里,就能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跟看译制片的感受是相似的,他只当自己是漆黑影院里的一位观众,用沉默的视听去感受父子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交流。大约要到一九八一年,他才忍不住插了一句:“郎静山我晓得的,他是大摄影家。” Y父转头问他:“你晓得郎静山?” “我在杂志上看到的,”Y说,“《摄影世界》《中国摄影》都介绍过他。”Y在八十年代初迷上了摄影,那时候照相机是奢侈品,上海滩能买到的地方极有限,况且,他也买不起,而是问同学借了玩过几次,有一回,还煞有介事地在父亲面前比画起来,说要给老爷子拍人物肖像,被他老子一口骂退。 “小鬼头蛮用功的。”Y父这句话是对着朋友讲的。讲完就把话题切掉了,Y能觉察出来,父亲在刻意回避。 Y当天没再插嘴,而是等客人离开之后,趁着收拾杯子的时候故作镇定地问了一句:“爸,你跟郎静山认识啊?” “谈不上认识。” “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Y父思忖片刻,答道:“郎静山的大女儿叫郎毓英,嫁给了国民党的军官张海容。两夫妻当年在大华饭店办的婚宴,现场还请了鹦鹉乐社去演出。这个鹦鹉乐社相当厉害,是顶顶早的华人爵士乐队,当年在上海滩名气也是蛮响的。” “啥?爵士乐队!” “对啊,爵士乐队。” “这啥时候的事情?” “让我想想看……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九年就有爵士乐队啦?” “鹦鹉乐社是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些外国人办的爵士乐队。跟你讲这些做啥?讲了你也搞不清楚。” “就因为搞不清楚,你要帮我多讲讲呀。” “自己研究。” 一年后,Y的人生迎来了重大转折,对于“自己研究”的父训,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从学校顺利毕业,分配进了某大型国企,搞化工检测,与钢铁中的有害元素打交道;同时期,他开始抽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FUJICA STX-1,五百元,他当时的月工资是三十六块)、属于自己的房间(十平米出头的亭子间)。那间屋子原本住着他的三个姐姐(年纪最小的比他大七岁),随着她们陆续出嫁,房子现在腾空了,他顺理成章地搬了进去。说是搬家,其实就是一条弄堂的距离;说是隔开了一条弄堂,其实仍旧活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这两套房子窗对窗,不拉窗帘的话,Y父朝窗外望去,就能看穿儿子的底细,因为那条弄堂的宽度不超过四米。 有一次,Y晴天白日给窗户挂上一整块的黑布。他在屋内紧张兮兮地忙活着,第一次操作,手有点抖,随后就听到“笃笃笃”的敲击声,“笃笃笃”,又闷又急。别人找他都是敲门、打电话、写信,唯有他老子敲窗,他还不能不放下手头的事情及时回应。他走到窗户口,探出半个脑袋,他父亲此时手握一根三米多长、晾衣服专用的竹竿。 “你在做啥?”那根竹竿问道。 “我在冲照片。” “啥?” “我搭了暗房,在冲照片。” “本事大的嘛,翅膀硬了。” “不是你讲的嘛,自己研究。” 那根竹竿不响,随后叮嘱道:“冲照片的时候香烟别吃,一些药剂当心点,别把房子烧了。” “爸,你开啥玩笑。” 那根竹竿不响,重新停在窗外的晾衣架上。 Y在家里冲洗照片,当时的条件仅限于黑白胶卷。Y是学化工的,配药水他熟门熟路;显影用的托盘,社会上不难买到,价格也便宜;暗房专用的照明灯有点贵,改用普通电灯泡,在灯泡上面涂满红漆;放大机无可替代,暂时买不起,是问朋友借的。 显影,停影,随着一张张黑白照片浮出液面,有那么一组问题也慢慢地呈现在Y的脑海里。有一次,他向父亲展示自己的新作品,随口问道:“爸,我从来就没看到过你年轻时候的照片,那些照片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要藏也不是我藏的,是别人藏的。” “啥?” “你忘记啦,你小的时候。” Y不响,为父亲整理相册,把自己新拍的几张插进去,小心翼翼,像集邮的人在安置新收藏的外国邮票。相册里,主要是Y父七十年代以后拍的黑白照片,彩照极少。有一张彩照,多年以后,Y向我们展示的时候自嘲道:“这是我摄影生涯的开山之作。”严格来说,那是儿子对老子的一次偷拍,Y趁父亲点烟斗的时候,偷偷摁下了快门。冲照片之际,他叫苦连连,知道这一记快门摁下去是什么代价。八十年代初,上海能冲彩色胶卷的地方很少,撇开跨区的路费不谈,冲印一张彩照要八九毛,换言之,哪怕他上班了,一卷彩色胶片冲下去,他整个月的工资就得泡汤。 偏偏Y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大玩家。除了摄影,他同时期对于听音乐这件事情也蛮上心,也是先借后买,入手了一台三洋牌的饭盒录音机,那种小型设备从体格来讲酷似上海人出门带饭用的铝制饭盒。有了“饭盒子”,得配磁带,当年都属于大宗消费,所以他在一九八四年之前,主要是玩黑白摄影。 一九八四年对于Y父来说是值得庆贺的。市文史馆给他发了正式的聘书,聘请他担任馆员;荣誉是巨大的隐形财富,实实在在的好处是,家里每个月多进了一笔收入。那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如果把那个数字换算成一只大闸蟹,那么从今往后的每个月,会有几个蟹脚,甚至加上蟹盖,用于支持Y的摄影爱好。 Y记得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某个周日的上午,吃了早饭,父亲对他说:“下半日你陪我出去一趟,去望一个老朋友。”这事情还挺新鲜的,因为往常Y父是不怎么出门的,朋友交际,通常他是被访的那位。讲起来,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了,出门习惯撑一根手杖——Y父口中的斯蒂克。“这袋东西你来拎。”Y父吩咐儿子。后者接过一个沉甸甸的袋子,里面是瓶装的醉蟹、蟹糊、黄泥螺。 Y父要去拜访的那位旧友家住愚园路常德路口,那一片的弄堂后来全部拆除,现在是晶品购物中心。作为领路人,Y父只带儿子去过一次,后来都是Y自己操作。八十年代的最后五年,Y几乎每个月都会重走这段路,去愚园路找方家伯伯,有时去拿冲好的照片,有时带了要冲的几卷彩色胶卷。那些胶卷最终会装入牛皮信封,用挂号信寄给方家的香港亲戚。用这个办法,平摊各种成本,Y当时冲洗一张彩色照片只要五毛钱。回顾那段时光,Y觉得最大的收获不是省钱,而是与方家伯伯成了忘年交,从他那里听到了别开生面的父亲。 Y第一次去送胶卷的时候,方家伯伯摆摆手说:“不麻烦,不麻烦,你太客气了。”还叫保姆给小伙子倒正广和的橘子水。方家伯伯是孤老,子女都不在内地,退休以前是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跟Y父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 方家伯伯吃口咖啡,说:“上趟你爸来看我,还带了东西,还记得我欢喜吃邵万生的黄泥螺,真正难得。” Y不响。 “你爸对你真好。” “啊?” “他这人,骨头太硬,从来不肯求人。” Y吃橘子水,不响。 “我记得一九三三年天热的时候,玫瑰社解散,团员各奔东西,大家都在托人托关系寻后路,当时我们劝他,快想想办法呀,托托看,他不肯。那么就失业呀。他就靠帮杂志画插图混口饭吃,后来翻《申报》看到有人要去香港办报纸,招美术编辑。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租界,上海人不大情愿去香港,不像后来,后来大家不愿意当汉奸,有蛮多人跑去香港的。你爸去香港属于去得早的。” Y不理解方家伯伯到底在讲什么,尤其是那个玫瑰社。 “玫瑰社是旧上海的歌舞团,你法国的康康舞晓得吗?” “不晓得。” “那么大腿舞呢?就是女的穿了花裙子,一边跳舞一边高抬腿。”Y不响。方家伯伯说:“你爸以前是玫瑰社的乐师,吹萨克斯的。” “啥,他会吹萨克斯?” 方家伯伯不响。 那天,Y回家以后借了抽烟的工夫,向父亲询问萨克斯的事情。Y父吃一口烟斗,冷冷地说:“怎么想起问这个?” “方家伯伯讲你是全中国最早吹萨克斯的人。” “这他是帮我戴高帽子了。他讲我最早,他有啥证据?” Y不响。 “应该这样讲,我呢,吹萨克斯只是吹得比较早,因为我一九二八年跟了歌舞团去南洋演出,路过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你晓得的呀,受美国影响比较大,爵士音乐在当地相当流行,我就对萨克斯蛮感兴趣的,我跟我们团长讲,要么买一把,我来学,他讲好的呀。就这样,我们在南洋演了一年多,等到回上海的时候,我已经改吹萨克斯了。” “没啦?” “没了。” “怎么同样讲这些事情,我听方家伯伯讲,讲得五颜六色的,像在冲彩色照片,怎么被你一讲,就变黑白照片了。” “旧社会呀,旧社会当然都是黑白照片。” Y不响。差不多一个月后,他接到方家伯伯的电话,约了时间过去取照片。这次,他是有备而去,随身带着相机。进了方家,Y主动要求为老先生拍几张照片。方家伯伯哈哈笑道:“好的好的,帮我拍两张。”老先生脸上的笑容一直持续到Y将前情补上。Y明显察觉到,屋内的气氛开始凝结,变得非常严肃。后来方家伯伯对Y说:“你爸既然不肯讲嘛,终归有他的道理,我们应该尊重他,你讲呢?”Y不响。好在老先生的口风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紧。他似乎挺喜欢Y这个小友。Y来拜访,一般选在周日下午,两点钟敲过,那时方家伯伯已经睡过午觉了。他这一来,算是给老先生的下午茶增添了许多欢乐。老先生很愿意跟Y聊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说着说着,他们就在往事的海洋里迷失了,随后,导航的指针便会对准Y父。 有一次,方家伯伯突然问Y,家里谁开火仓。Y说都是母亲在烧。方家伯伯感叹道:“真可惜。你爸烧菜的水平不亚于他吹萨克斯的水平。”Y不响。方家伯伯说:“以前在玫瑰社,社员睏宿舍,吃住在一道,我们经常吃他烧的菜。最欢喜他的焗蛤蜊。怎么烧呢?蛤蜊的肉挖出来,随后跟鱼肉,一般是青鱼,或者胖头鱼,两种肉混在一道,捣捣碎,再摆进蛤蜊壳里,下油锅焗,这味道,赞!” 说来也巧,Y当日回家,进弄堂没多久便闻到一股奇香,也许是黄鱼或者带鱼红烧,也许是煎什么贝壳类的海鲜。他闻香寻味,最后走进了自家的灶间;更诡异的是,竟然是他父亲在掌勺,套着围兜,眉头紧皱,锅子里,油噼里啪啦到处乱溅。 “爸,你在烧啥?” “焗蛤蜊。” “啥?” “快点上去,当心油爆着。” 如此反常的一天,Y父在饭后郑重宣布:“我封笔了。”Y说:“啥?”Y父说:“从今以后,不画了,封笔了。”Y不理解。Y父说:“十几年没画了,笔再拾起来,手都生了,质量明显下降,但是我硬生生在坚持,为啥,还不是为了你。再画下去,就是坏自己的牌子,有啥意思?”Y不响。Y父说:“你现在出道了,当个普通工人蛮好。我们对你没啥要求,你太太平平过日子,我们心满意足。”Y不响。此时Y母接着说道:“黎家姆妈帮我讲,前日在静安公园附近,看见你跟一个小姑娘荡马路,啥情况?”Y“啊”的一声,目光转向父亲,原以为他会和母亲一样发起猛烈的攻势,结果倒是老爷子帮忙灭火,只给了他一句建议:“记牢我的话,跟女朋友出去荡马路,要走在她的外侧。” …… 精彩全文请见《青年文学》202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