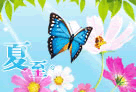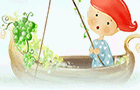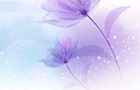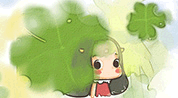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小编说 都说红颜祸水。村里最漂亮的女人沙大美被她老公一刀捅死了,可接到报案的派出所民警张光荣却下意识地让两个最不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字脱口而出:“活该!”这女人到底有多不招人待见,才能让一个老警察说出这样的话?祸从口出,张光荣的麻烦也随之而来,沙大美的老爹从此跟他杠上了。夏天悄悄过去,杀人凶手依然在逃,张光荣和沙家的恩恩怨怨又该如何了结? 夏天悄悄过去 - 张军 - 一 墙角那块被众多屁股打磨过的磨盘石从“大角水塔”阴影里走了出来,暴露在午后两点多钟暴戾的日光之下。洳口小镇仿佛恹恹入睡,四下阒静无声,到处弥漫着北方乡间夏季午后常有的慵懒气息。 小镇的一处神经末梢忽然被触动,准确位置是庙儿街一号——从“大角水塔”朝前数,第三横街,右首第一家院落。洳口镇最热闹的地方不过是两条十字交叉的老街,老百姓管两条街的交会点叫“大角”,“大角”一隅矗立着一座缠满爬山虎的老水塔。这处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水塔高出周边所有建筑和树梢,雄 视着整个小镇,因此成为小镇地标性建筑。 由这个院落引出的骚动和不安源自沙老汉慌乱奔忙的脚步声。爬山虎织成的绿毯挂到了水塔脖颈,它俯瞰着这个张皇失措的老人。老人踉跄到“大角”,一个趔趄撞翻了把角的菜摊儿,一个挂满白霜、矮墩墩的冬瓜滚到了滚烫的柏油路面上。一方蓝色无纺布凉棚被热风鼓荡得展开四翼,像一只欲冲天而起的大鸟。凉棚之下,从瞌睡中惊醒的女摊主愣愣地看着这个倒地的老人。 那一刻,镇卫生院的救护车哎呦哎呦叫着,屁股卷着一团尘土,从他身边疾驰而过。 “快跑啊!快啊,快啊,晚一会儿我闺女恐怕就不行啦!”他从地上划拉到跌下鼻梁的眼镜,往脸上胡乱一扣,忙不迭跪在地上,朝着慌慌张张的车屁股连连作揖。 闺女沙大美垂在他臂弯时,脸已经是接近死亡的铁青色,这种脸色让人害怕。一个核桃般大的血窟窿开在她胸口月白色罩衫之上。那个恐怖的窟窿像个小鱼嘴儿,噗噗向外吐着细密的血泡。他抱着闺女感觉像抱着一块冰。现在,那种冰凉的感觉仍一捏一捏揪着他的心,让他在太阳底下疯狂地打着摆子。 外孙棍儿跑进院子时,戏匣子里正播着单田芳的评书《水浒传》。棍儿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向他报告:“姥爷!我妈和我爸又打起来啦!”沙老汉将音量拧小了些,刚听清,又调了回去。 他们两口子打架还不是家常便饭!他总是沉一会儿才趿拉着鞋,穿过一条窄窄的胡同,赶到他们那个院子。每次,宋春生总是秤砣一样蹲在地上,而闺女,洗脸盆、胰子盒、炉子盖……但凡能弄出响声的东西她都要搞出点儿动静,来向宋春生示威:脸盆子摔在地上,宋春生一哆嗦;茶缸盖子啪地合上,宋春生又一哆嗦。他去,还是不去;去得早,还是去得晚,都不是紧要的事。 棍儿对姥爷的无动于衷表示不满:“您去看看吧,我看见我爸杵我妈的妈妈儿了。”宋春生打的当然不是孩子的姥姥,孩子姥姥早已过世,渔阳方言管乳房叫“妈妈儿”。棍儿不知道左乳底下就是要命的心脏,只知道那儿是自己小时候吮奶的“妈妈儿”。棍儿还没有看到,爹手里握着一把刃不是很长、但足够锋利的宰羊刀。他只看见妈妈紧跑了两步,然后突然重重地摔倒在门口。 离大老远,沙老汉就听见了姑爷的哭声,这哭不是好哭,他的心忽然沉了底。宋春生在院门内抱着闺女软丢丢的身子,大美一头散乱的头发垂在地上,向后扯着她那张惨白的脸。宋春生拍着她的脸,大美大美急切地叫着。 “你怎么她啦?啊?”宋春生没回答老丈人的问话,甚至根本没注意他的到来,抹了一把脸,将沙大美放到了地上。 闺女一到自己怀里咋就不行了?宋春生就是在他绝望又慌张的一刻跑走的。 你这个白眼狼!他没想到入赘的姑爷竟然对闺女动了刀子。他带着脑中仅存的一个念头,离开了那个乱哄哄的现场。 沙大美当然也没料到宋春生敢对她动刀子。要不,她不可能挺着胸脯向他身上凑,还反手抽了他一个嘴巴。那巴掌力道十足,让宋春生捂着脸在地上蹲了半天。他呸呸往外吐着血唾沫时,沙大美嘴角还撇着一抹冷笑,她以为这个男人又草鸡了。宋春生蓦地从地上窜起时,沙大美见到了一张陌生的、恐怖的脸。 即使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宋春生也没喊出半句话,这只红了眼的“公羊”低头撞向大门口——门口过道的墙缝里插着一把宰羊刀。 事后,八岁的棍儿作为唯一的目击者,以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该有的镇静先后回答了警察的提问:“我妈不要我和爸爸了。”说完这句话,棍儿撇撇嘴要哭,“我妈让我爸宰羊,我爸不去,他们就吵了起来……我看见我爸杵我妈的妈妈儿……”棍儿向蹲在他身边的警察叙述这个过程时,不知所措地抱着一只黑山羊的脖颈。 二 距派出所不足千米的一段路程,沙老汉感觉像是走过了一个世纪。他顾不上回答女摊主关切的询问,慌乱过了“大角水塔”,又向北走出几十米远,终于到了洳口派出所已经被晒得发白的两扇蓝色大铁门前。 老人一个前扑,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贴在了门上,随着铁门被擂响,他一路含混在嘴里的声音终于喊了出来:“救人啊!杀人啦!”铁门波浪般起伏,隆隆的声响像从天际滚来的一串串闷雷。 两扇铁门嘎嘎叫着从里面拉开,开门的是联防队员谢总管。老人见到谢总管,铆足力气朝他喊道:“宋春生把我闺女给捅啦!跑啦!你们快去抓人啊!” 此时,张光荣一脸迷瞪出了宿舍,趴水池子上冲脸,这一嗓子让他打了一个怔,他瞪圆了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问:“啥?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老人似乎已将全身的力气耗尽,有气无力地又重复了一遍。张光荣往自己黑胖的脸上又泼了一捧水,下巴上浓密的胡茬滑稽地挂了一层水珠。 “你是哪个村的,你闺女叫啥?” “我就是街上的,我闺女叫沙大美。” 洳口镇政府设在洳口村,村镇合一,本村人都说自己是“街上的”。张光荣双手又掬了一捧冰凉的自来水,往脸上一撩,又一抹,嘴里咕哝:“我说呢,咋看着有些面熟。” “啥?你说啥?”老人没听清,对他的自言自语很不满意。 张光荣不屑向他重复,脱口而出一句自己也没想到的话:“死了活该!” 这句话分量十足,一下就将这个可怜的老人揳在原地。 三 白净脸细高挑儿的米乐正斜倚着值班室的门框,看着院中的情景。“死了活该?”他以为自己听岔了音儿,吓得不觉站直了身子。他有些发蒙,连他这个刚入门的新警也觉出了师父对待百姓态度的不妥。这是多么大的仇啊?至于吗!要是他崇拜的毕波师父在场——尽管毕波不是所里为自己指定的师父,他也喊毕波师父,对自己的师父张光荣,他反而叫不出口——定是跑不了的一通奚落:“瞧,又犯愣子了!” 沙老汉盯着这个警察一张黑胖的脸,愣怔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你叫什么?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告诉我!告诉我!”他绕过水池子,向水龙头前的张光荣扑来。 米乐见事不好,跨步上前,一把扶住老人,朝身后喊:“谢总管!谢总管!快找挎子钥匙。”谢总管如梦方醒,跑回值班室,转眼拿着车钥匙又跑回院子。 张光荣下巴挂着水珠,跨上挎子,米乐骑在他的身后,谢总管扑通跳进挎斗。马达在院内轰响。溜了嘴的张光荣不置一词,挎子屁股后头冒着黑烟,迅猛蹿出派出所大门,过了“大角水塔”一路向南。 张光荣在车上板着脸,甩头说:“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出儿,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好像在为自己开脱。他眯缝着眼睛,头发全部向后倒伏,露着齐刷刷的发根,钻进警服上衣的风将他后背鼓荡成了一面风帆。米乐和谢总管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只有挎斗上松了螺母的备胎呱嗒、呱嗒回应着他无力的解释。 围观群众闪开了一条路,张光荣瞟了一眼镇卫生院大夫敷衍的动作就知道人已经不行了。群众纷纷向警察指着洳口后山:“宋春生跑了,朝山里跑了!”米乐回望,他们所指的方向是燕山余脉连绵不断的群山。 米乐往院里挤的时候,后背将贴在门上的一张福字蹭了下来,他将耷拉下三个角的福字一掌又拍了回去,待看清这张褪了颜色的福字时,猛然发觉:这个院子他来过!大概三个月前,还是春天时节,他和张光荣一起来过。 那是一个月黑天。那天傍晚,洳口村治保主任马大嘴频率很快地倒换着两条长腿,跑到了派出所。他神情紧张地对张光荣说:“沙大美和拐子姚刚跑了,我拦不住,这会儿恐怕已经到了县汽车站。” 张光荣瞧着他,不说话,那吊儿郎当的神情分明在说:这种事和派出所有啥关系? 马大嘴看他心不在焉,明白自己该说重点:“姚拐子可是在取保候审期间呢!” 这话一下就和张光荣挂上了钩,他警觉了一下,马上又塌下了眼皮:“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姚刚的保证人,这事你得负责。” “老天爷!我不是跟你说闲话呢,我是跟你报告呢。谁也不是吓大的,别指着我负啥责任!” 张光荣白了他一眼,拉上米乐,三人骑着一辆挎子奔县城。他们搜寻了长途汽车站的角角落落也没见到人影。候到末班车离场,张光荣大手一挥,三人打道回府。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期间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居住地。等他回来再跟他算账。 马大嘴一路唠叨:“宋春生这个活王八还不知道呢。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出事!不行,你们得出面……” 张光荣不客气地戳穿他:“你哪儿是关心姚刚跑不跑,你是怕宋春生奓刺,把你和沙大美的事给捎上吧?” 马大嘴急了:“你可别瞎说!我哪儿得罪你了?尽把臭狗屎往我身上抹!” 张光荣针锋相对:“那你让我们出面是啥意思?又给我整一头瞎驴骑!告诉你,只要没发生案件,就与我们无关!” ...... (未完待续,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啄木鸟》202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