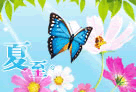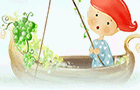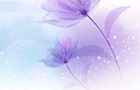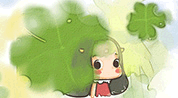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四) 清华文学社是学生组织的团体。志摩在硖石收到的邀请演讲的信件,是梁实秋托梁思成转寄的。 清华学校高等科的小礼堂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足有好几百之多,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学生。志摩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上缀数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蹬一双黑缎皂鞋,飘然而至。 登台之后,他从怀里取出一卷用打字机打好的稿纸,接着坐了下来。他扶了扶近视镜架,解释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 and Life——,我将按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 志摩受英国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太深,他满以为这种"牛津式"的演讲会博得大家的惊讶、钦佩和欢迎;却不料听众并没有准备听英语演讲,更不习惯于聆听照章宣读式的讲演,他们希望的是轻松有趣连珠妙语,所以,志摩讲了不久,后排座位上的听众便陆续离去了。 这次演讲是失败的。 第二天,志摩就倚在南归的火车窗口,看着无边无际的荒凉。 原野,向着家乡进发了。 几间茅舍、枯黄的屋顶,弯弯曲曲的小河,古老的木桥、松林。 丛竹、红叶,风掣电驰般地向后退去。一条瘦骨高隆的老牛拖着体犁,在原野上翻出一道褐色的深痕。从汉朝起就这样耕耘了吧。 漫长的岁月飞逝而去了,一代代人辛勤一世,无声地倒下,长眠在泥土里。然而,天地、山川、原野,什么都没有变。历史也在这种求生方式里凝固了。 他的心绪,已经渐趋平静。他知道,在伦敦开始的梦,现在是真正结束了。大海固然常常有汹涛滔天,但大海却是深厚的,庄重的,雄伟的;波浪翻滚只是它瞬息万变的表情而已,它自有其岿然不动的内蕴。最终的谜底一旦解开,求索的迷相便烟稍云散。志摩未必甘心以宿命现自慰,但他看得出趋势之必然,他无意去作徒然的拼斗。他对徽音的爱中一开始便包含着莫大的尊重,这种尊重化做强有力的理智,以无可违逆的说服力遏止了爱中的非理性成份。何况他还带着一个默契而去。这默契是一种担保:徽音与他之间的心灵、精神上的契合已经完成,它不会中断和受损;排除了婚姻的动机,这种契合和沟通将更无障碍地扩展。那么,他还冀求什么?他还缺憾什么? 繁忙的活动和勤奋的工作充实了他的生活。不管怎样,他不会抛开诗、文学,不会抛开交际、友谊,不会抛开从自己的实感出发的社会正义感。 噩耗突然从劳丹勃罗传来:年仅三十四岁的、志摩素深景仰和神往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遽尔辞世。半年前还曾亲切一见的旷世才女,倏忽间香销玉陨,志摩悲不自胜。他怎不感叹人生的多舛和短促,怎不哀伤红颜的命薄!凄怆的情怀化做诗句,他挥泪写下了《哀曼殊斐尔》又到文友会作了《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殊斐尔的印象》的演讲。未见北京大学学溯又起,校长蔡子民(元培)因罗文斡案对教育总长彭允彝不满而宣布辞职,北大学生涌到众议院请愿,北京学生联合宣言驱逐彭氏,要求惩办议长吴景流。志摩情绪激愤,在《努力周刊》发表《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痛斥军阀政府:"……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时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拉开地狱之门的精神!" 他的诗作从笔端奔涌而出:《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希望一的埋葬》、《情死》、《听瓦格纳乐剧》、《康桥,再会罢》、《夏日田间即景》、《青年杂咏》、《月下待杜鹃不来》、《小花篮送卫礼贤先生》、《幻想》……暑期中,他去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两星期的《英国近代文学和未来派的诗》,又去天津绿波社讲演,八月去北戴河避暑,又去游角山栖贤寺,登长城……他创作,他翻译,他会友,他演讲,他游览;爱之希望,情之幻灭,时局形势。民间疾苦,友情温暖,山川美景,天地神秀,在他心里交融渗化,形成了他的倾向、爱憎和无穷无尽的感触…… 祖母病危的电报来了。志摩立刻从北戴河搭车回家。 八十四岁的老人,六十年来一直是他们全家精神上、生活上的支柱。勉以她的慈爱和恩泽,前庇着全家老幼,维持着特有的伦常与秩序,如今,在病榻上缠绵了十一天,终于瞑目长逝了。 志摩初次遭逢亲人的大故,是不满六岁时祖父的去世;那时蒙昧未开,谈不上什么惨痛的体验。而这次与至亲至爱的祖母的永诀,却是与其说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毋宁说使他的心灵发生了一种奇妙的、重要的变化。他开始自问:我们对于人生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亲近的人情的经验,究竟把握了多少,究竟有多少深微的了解?眼看着有病的祖母打滚痛恸,一家长幼的涕泪涝沱,耳中充满了狂沸似的呼呛号叫,志摩非但没有共鸣的反应,没有流泪,却反而达到了一个超感情的、静定的、幽妙的意境。在想象中,他似乎看见祖母脱离了躯壳与人间,穿着雪白的长袍,冉冉的升天而去,他只想默默地跪在尘埃,赞美她一生的功德,赞美她安宁的圆寂…… 未曾经历过精神或心灵的重大变故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在生命的户外徘徊。也许偶尔猜想到墙内的几分动静,但总是浮浅的,不切实际的,甚至完全是隔膜的。这次祖母的辞世,给了志摩不少静下心来深自反省的机会。他不敢自认为因此感悟了人生的真谛,或是得到了什么智慧;但他确切地感到自此与实际的生活更深了一层接触与贴近,愈益激发了他对于人生种种好奇的探讨,愈益使他谅讶这谜一般的大奥秘的玄妙。不但死是神奇的现象,不但生命与呼吸是神奇的现象,就连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乃至迷信,也好像放射着异样的光彩,不容人们简单地擅用一两个形容词来概括…… 志摩难抑心中强烈而鲜明的感想,他急于把积愫向一个最能同情的好友倾吐。他给陈西滢写了一封信。但是,那封信最终没有写完和寄出。 (五) 志摩不是一个沉湎在俗世的哀乐繁缛中不能自拔的人。除了爱情之外,他渴求友谊,寻找共鸣。他与回国后才结识的好友胡适一起畅游西湖,与陈衡哲、朱经农、汪精卫、胡适、马君武、陶行知等兴致勃勃地去海宁现潮,后来又去上海。在这期间,他与瞿秋白、杨仲甫、常云湄、张东苏、徐振飞、陆志韦、郑振择等常来常往,过从密切。——一群青年文人,学识丰富,各具文采,胸怀大志,又自有建树,能不一见如故吗? 一天,志摩去沧州别墅胡适那里闲谈。胡适拿出他的《烟霞杂诗》,志摩读了一遍,问:"就这些?还有藏着没拿出来的吗?" 胡适赧然一笑,说:"有……是还有几首……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正说话间,瞿秋白来了。苍白、消瘦,厚厚的近视眼镜片后面的双眼,似乎凹陷得更深了,两个肩膀耸得高高的,一件旧薄呢西装像挂在衣架子上。他坐下后,随手翻看桌上的《烟霞杂诗》。茶送上来了,秋白把杯子端在手里,一阵剧烈的咳嗽使杯中的水都洒泼出来了。"听说……"他掏出手帕擦去裤管上的茶水,"你们的《努力周刊》要停版了?" "嗯……"胡适点点头,"我们想改组一下,大体上把它办成像《新青年》的样子。" "也好,也好。这个刊物,在学生中间影响是不小的,你们一定要坚持办下去……"又咳嗽了。 "秋白,你,身体似乎不大好?去看过医生了吗?我认识一位医生,德国人,很有学问的……"志摩关心地问道。 秋白一边咳嗽一边点头,脸都涨红了。"看……过了。看过了。医生说,肺病是毫无疑问的……" "啊,肺病?"志摩从椅子上直跳起来,"那,你不能再这样拚命译书写文章了!这样下去会送命的!肺病,一定要静歇、补养,才能慢慢好起来。秋白,这样,"志摩走到他的面前,"过一阵,你随我到硖石去吧,到我家或东山庙里去住一阵,那里空气好,对肺病最有益了……" "不,谢谢你,志摩,"秋白摇摇头,"我不能不工作呀。我……你也知道的。" "暂时的生活,我来负担好啦。" "秋白,志摩的提议,值得接受,"胡适也说,"有这么多朋友,你暂时养病期间的生活,完全不必担心。你要从长计议呀。" "不,不,谢谢你们的好意……"秋白说,"我目前还不能离开上海,以后视情况再说吧。我们这些穷文人,一天不写字,一天就没有饭吃;不像你们是阔少爷出身,十年八年不做事也不要紧的。" "唉!"志摩朝胡适看了一眼,说不出话来了。 "沫若目前的情况也很困苦。"秋白又说。 "是吗?"志摩听到提起沫若,马上叫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如何?" 志摩跟沫若,是他回国后由中学同班同学郁达夫介绍认识的。 以志摩的文艺观点和气质习性而言,他自然而然地与高举"为艺术而艺术"大旗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惺惺相借。他在清华学校所作的《艺术与人生》的讲词被《创造季刊》接受刊出,就表明他与创造社诸人关系之亲密。其中,他对郭沫若尤为推崇。他曾给成仿吾写信说:"……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读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棕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 但是,不久,便起风波了。 志摩是个率直的人,他缺乏世故的复杂头脑。他写了一篇《杂记》,投寄给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文中随意地谈到郭沫若诗句中"泪浪滔滔"一词之欠妥;成仿吾闻讯大怒,在《创造季刊》上将志摩以前给他的那封信及自己批驳志摩的一信全文刊出,斥责志摩表面上虚与周旋,暗中向他们射冷箭,指谪志摩"污辱沫若的人格";"人之虚伪,一至于此!"志摩对此,既难过,又气愤,写了一封答成仿吾的公开信发表在《晨报副刊》,坦诚地表示自己毫无寻衅的用意,反复解释对"泪浪滔滔"的批评完全是艺术上的见解,真诚地希望"此后彼此严自审验,有过共认共谅,有功共标共赏,消除成见的暴戾与专慢;在真文艺精神的温热里互感彼此心灵之密切。 所以,一听说沫若的处境不佳,志摩便坐不住了。 "我……上次随达夫去过一回的。但是,糊里糊涂跟在后面走,什么地方记不得了。"胡适说。 "他住在民厚里一百二十一号。今天我去不成了,还有一点事,你们去吧,他反正是在家里的。"秋白说。 秋白告辞离去,志摩跟在后面喊:"秋白!自己身体千万当心啊!" 志摩与胡适出门约了朱经农一起步行到了民厚里。 那是一条狭小的里弄,房屋交杂间混,门牌号码也零落不全,三人兜了几圈,问了两个人,才摸到一百二十一号的门前。 志摩伸手敲门,过了好一会,门开了。郭沫若赤脚穿一双拖鞋,手抱一个襁褓小儿,旧学生装衣襟敞着,头发乱蓬蓬的。看到三位来客,他先是一怔,但随即朗然而笑。"喔,贵客到!请进吧。唉,家里寒酸得不成体统,三位不要见笑了……" "哪里的话!"志摩笑着说,"怀里抱的是公子还是小姐?" 室内果然乱作一团。小小的一间,大概卧室和客室均在其中了。一张大床占去了三分之一地盘,被子没有叠齐,洗净晾干的和未洗过的脏衣服散乱地扔满一床;一根绳子斜悬在半空,晾满了尿布。一架竹书架旁边是一张小小的粗木写字台,台上书本、纸张、茶杯、烟缸、药瓶、奶罐、玩具,狼藉不堪。房间当中有一只竹摇篮,摇篮周围有几把各式各样的椅子,有的已经坏了。 屋内已坐着几个客人。志摩等进门,已经没有插足的地方了。 见有新客进门,先到的客人站了起来。"你们坐吧,我们告辞了。" "坐下一起谈谈吧。"胡适说。 "不啦,不啦,我们已经坐了好一会儿了,"一位抱着孩子的长脸男子向大家点点头,就出去了。这位,好面熟呀,他……"志摩指着那人的背影说。 "他就是寿昌呀。"胡适笑着说,"你不认识?" "噢,田汉!"志摩手拍后脑懊丧地喊道,"真是失之交臂了。我见过他一面,只记住他那一张狭长脸……" "你的险又何尝不狭长?"胡适打趣地说。 "那……他比我狭长得多了!" 沫若招呼大家坐下,又拖着小儿去找茶杯。志摩挡住他,"别倒茶。刚才已在适之那里灌胀了。秋白来坐了一会,说起你的情况,我们就来看看你,你也坐下。" 几个小男孩在屋子中间事来窜去,大声叫着,笑逐着,嘴里嚷的是日本话。一会儿,一个孩子跌倒了,放声大哭起来。沫若只得把手里的孩子放在摇篮里,走去搀扶他。"好,好,不哭啦,勇敢一点!瞧,再哭,这几个伯伯要骂啦。"他随手从摇篮边上拉了一块皱巴巴的布片替孩子擦去眼泪鼻涕。这个孩子刚站好,摇篮里的娃儿又哭了。沫若又转身把他抱起来。 "夫人呢?"胡适问。 "她在厨下忙呢。一家几口,买菜、烧饭、洗涮都靠她……" 沫若摇摇头苦笑着说。 志摩听到厨房里"劈劈啪啪"的木辰声,料想一定就是沫若的日本夫人了。 "唉,沫若,你的生活环境太不如意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要维持几个刊物,真难为了你。" "有什么办法?"沫若耸耸肩膀,"这就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呀。" "孩子又都这么小……"志摩也说。 "我是一天到晚穷于应付。"沫若说,"我这个人,快要被生活活埋掉了!" "以后……会好起来的。"志摩感到很郁闷,只好安慰他。 一个孩子向前一冲,额头撞在书桌上,又哭了。沫若一手扶着小儿,起身想去扶他,志摩连忙抢先把孩子抱起来,"哦!好汉不哭,哭的不是好汉!"又伸直双臂,把孩子举向空中,"来,让我们到天上去!到天上去喽!"孩子破涕为笑了。 朱经农望望胡适,没有作声。显然他感到颇为尴尬。 几个孩子又大声嘻笑了,他们从地上翻到床上,扭成一团。 楼上下来一个人,走到门口看了看。 沫若朝他一点头:"仿吾,进来谈谈吧。适之、志摩和经农来了。 三人都站起来,胡适道:"仿吾兄近来可好?" 仿吾迟疑了一下,向大家点了点头,走进来在床边上坐下,绷着脸,身子挺得直直的。 "刚才,我把你的一首新作给志摩看了。"胡适对沫若说。 一个男孩走来爬上沫若的膝盖,一把抓下他的眼镜,沫若忙说:"怎么抓我的眼镜?去,到那边去玩,不许捣乱!"又转过,头去说:"志摩兄有什么见教?" "这个……"志摩沉吟着,向仿吾瞟了一眼,"我实话实说。我感到,陈义、体格、词采俱不见佳……不如《女神》远甚了。这也难怪。在小把戏的包围袭击之下,诗之灵感恐怕早就给吓跑了。" 沫若哈哈大笑。"说得对,说得对。看来,须得一个好的书斋,我才能写出好诗来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客人们坐不住了,沫若也没有挽留。三人走在路上,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感慨着秋白、沫若在如此艰困的境况下苦苦奋斗,真是不易。 第二天,沫若带着他的大儿子去回访志摩。志摩拿出水果、花生等招待小客人,并和他玩了一会。这一次,气氛就自然了,谈话也很顾畅。 "……我想写一封信给西滢。他评了我译的《茵梦湖》,我向他谈点我的看法。"沫若说。 "好极!西滢是很热心的,他一定会回你一封长长的信"志摩高兴地说。 "谈起西滢,我想起上次有一位友人说,他疑心'西滢'就是徐志摩的化名…""真的吗?"志摩抚掌大笑,"何以见得?" "他说,凡见署名'西滢'的文字,笔调跟徐志摩的文字像极了。" "这倒有趣,难道我们留英学生的腔调真有共同之处,跟别人有别吗?"志摩剥了一个桔子给孩子,又递了一个给沫若,"不过,西滢是西滢,志摩是志摩。我敢说西滢决写不出《我所知道的康桥》,我也决没有本事写他的那种《闲话》。" "那当然。别人的感觉,只是一种表面的印象罢了。"沫若说着 从怀里取出一本书递给志摩,"志摩兄,赠你一本我选译的《诗经》,题目取自《卷耳篇》,就叫做《卷耳集》。请你指教了。" "别客气!我是一个浮浅夹杂的人,我自知旧学底子是远远不能望见你的项背的。而且,我也无法像你那样下苦功下力气去研究《诗经》。" 这番赞语,使沫若兴奋了,他点点头说:"关于《诗经》,我倒是下了点功夫的。我讨厌朱熹的注释。他的眼光太偏狭了。 我对其中每一篇每一句都反复玩味,有自己的见解。不怕你老兄笑话,即使孔子复生,他看了这本《卷耳集》,也定会说:'启予者沫若也!'哈哈!我把这句话写进序言里去了,你不感到太狂妄吗?" "我们这班人,如若没有了这点'狂妄',这点自信,能创建成中国的新文学来吗?" 沫若大笑点头:"我是一向以狂生、叛逆自居的……" "沫若,你的环境太差了。这样下去,女神转眼就会变成老丑婆的,你无论如何得想法子……" "是的,你说得不错。上海的生活我厌恶透了。满城铜臭兮居室陋,女神女神兮离我去!我想明年到四川红十字医院去做事。我是学医的。" "这,也好。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我倒没有这个宏愿,只是聊以糊口罢了。文学我是不放弃的。" "这当然!中国的新诗,你是开山老祖之一。论气魄,你是第一。适之的《尝试集》虽然早;可惜旧诗味道还太浓……" "对《尝试集》你也这么看?我早就感觉到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我当面也对他这么说的,弄得他现在不敢拿诗给我看了,只怕我又要讲他'新瓶子装老陈酒'!" 友谊给志摩以温暖,志摩也把真诚给予朋友。他喜欢与朋友长谈,谈诗,谈人生,谈友情,谈爱,谈天谈地,谈书中的美丽故事,谈人间的不平……大家看到一个匆匆忙忙、亢奋勇进的志摩。只有他自己知道,心底里还是空落落的一片。 前妻张幼仪自德国的来信,又加重了他的这种空落落一片的感觉。她说,她在德国学幼儿教育学,归国后,打算办幼稚院,先从狭石人手……她在信中问起志摩的起居生活情况。志摩提笔给她回信,告诉她,自己仍是孓然一身,虽然忙碌,却很孤寂;又说,跟她的大哥君励常在一起游乐,仍是好朋友,好兄弟…… 是呀,他寂寞,他忧郁。他独自乘船去西湖,月下凝视孤残的雷峰塔凄凉而神秘地在南屏晚钟声里将影子落在静溢的波心…… 他去常州天宁寺听僧徒礼赞,蹑手蹑脚走进大殿。钟声、磐声、鼓声、木鱼声、佛号声汇成宁静的和谐。浓馥的檀香,青色的氤氲,上腾到三世佛的眉宇前。一种庄严、肃静、静定的境界。他感到自己化作磐声,化作青烟,在佛殿里缭绕、升华、散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