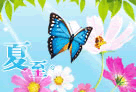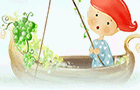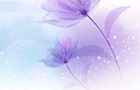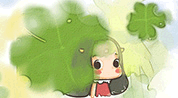|
温亚军,1967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岐山县,1984年底入伍,曾在新疆服役16年,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西风烈》《伪生活》等7部,出版小说集20多部。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柳青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字。 导 读 现如今,如何关爱老年生活已经成了重大问题,而面对此种问题的人,往往都已人到中年。小说中,那对中年姐弟如何在丧母之后,照顾腿有伤病却“春心萌动”的父亲?在养老这部难念的经中,作家似乎找到了中国式的美学深沉。 时间前面 温亚军 一 从百湘居出来,关小阳的喉咙火烧火燎,他不停地“咝咝”吸气,以减轻灼疼感。胃反应得慢,目前还风平浪静。可他心里却翻江倒海,情绪极难平静。望着远处高耸的电视塔,他高声大气对关小月说:“这个女人哪儿像妈妈了?眼睛、鼻子、嘴巴?还有她对人的态度,没一处能与妈妈沾上边。” “你较这劲干吗?”关小月明白弟弟的火气从哪儿来,她也一肚子气没处撒呢,“她像不像妈,爸说了算。关小阳你给我记好了,这事由不得你,当然也由不得我。” 中午的阳光比百湘居饭菜的劲道还要足,从电视塔玻璃幕墙折射过来,投进昆玉河里,像撒了一河的刀子,刺得关小阳眼睛火辣辣地疼,他闭着眼睛缓解了一下,再睁开眼却被这火红的阳光给闪得有些晕乎。他狠狠地吸了吸鼻子,接过姐姐递来的纸巾,打量了好一会儿,像要从纸巾中寻出什么端倪似的,末了,却揉着纸巾去擦抹额头沁出的汗水,边擦边嘀咕:“我看就是老糊涂了,什么眼神啊,瞅那女的破态度,居然说长得像我妈。咱妈能那样?”纸巾被额头上的汗洇湿成一团,压根儿再无力光顾吸溜有声的鼻子。关小阳没意识到,他鼻子的吸溜声磨搓得旁人的耳朵受不了。 关小月听得心烦意乱,火了:“有完没完了?”看着关小阳诧异的神色,才觉出自己有些小题大做,便抓住弟弟的胳膊,由F调迅疾降至D调,“不是非要强迫你吃辣,这是湘菜馆,无辣不湘。咱是一个妈生的,我也吃不了辣呀,可为了咱爸,这个险得冒。这不,通过吃饭时间接触了,知道她与咱妈各方面都不在一个频道,咱心里有底了不是?记住,回去了多喝水,半天辣劲儿就过去了。” 姐姐的话听上去没毛病,可没戳准问题的关键。关小阳知道,姐姐这是避重就轻,没法像以前那样一针见血,当然自有她的难处。最近,她儿子正在闹离婚,儿媳妇把没满月的孙子甩给她回了娘家,这阵子姐姐的心里比吃湘菜还要火辣,那是喝啥都不管用,降不了火的。为了自己的父亲,她压抑内心的焦躁,撇下孙子,能陪他来吃湘菜观察宋妮娜,够意思了吧。关小阳为自己刚才的言语冒失心怀歉疚,到了姐姐家门口停住车,他迅速下车绕到副驾驶这边,帮姐姐打开车门,搀扶她下来。关小月有点意外,拿眼神上上下下看了关小阳一遍,抿了抿唇,推开他的手:“一边去,又不是七老八十,谁要你扶了。”话是这么说,心里却舒坦,脸上神情微微松了些,下意识地拢了拢头发,让染过的上半截黑发盖住头顶窜出来的白发根。其实根本遮盖不住,白发理直气壮地与染过的发色在头顶平分山河。只是关小月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发色对比鲜明的不堪。姐姐的白发比太阳光刺眼,关小阳心里难受,拒绝姐姐的邀请上楼,丢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百湘居的臭鳜鱼,味道的确不错,除过辣之外。”迅速返回车里,启动车子跑开。 在此之前,关小阳根本没在意父亲话里的意思,母亲去世七年,父亲独自生活了七年,对子女从未提出过任何要求,他的生活,更像是一株自生自长的植物,无须过多的关注,只要沾点阳光雨露,便一味向上,虽然并不蓬勃。但姐弟俩不能不关照父亲,这是一种亲情血缘的本能。姐弟俩也曾劝过父亲找个老伴,既能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又排遣了独自一人面对清冷时光的孤独。怎么说,有个人在跟前说说话,聊一聊日常,寻些人间烟火浓稠的事儿,比一个人看着日出便寻摸着日落的样子强吧。刚开始,父亲避开这个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却也绝无明确反对,态度模糊,一点都不明朗。正是这种模糊让姐弟俩有所误解,以为对这事父亲是有想法的,只是碍于脸面,不好对子女说罢了。于是,他们决定主动出击,善解人意总好过空洞的关怀。关小月毕竟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办事效率极高,通过邻居很快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对象,定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才给父亲说了。原以为父亲至少不会推辞这番心意,岂知父亲没等听完,便勃然大怒,顺手抓起拐杖照着关小月挥了过来。一旁察言观色的关小阳反应得快,一把将姐姐推开,父亲举起来的拐杖落了空,在地板上磕出巨大响声。关小阳吓呆了,以父亲这力道,他要不推关小月一把,她那天不头破血流,就是拐杖落到肩膀胳膊不折,肯定也得疼上好多天。看父亲那架势,真不是玩虚的。 父亲退休前从副局长调成正局待遇,脾气也跟着涨了一级,那是他一辈子的高光时刻,容不得任何人亵渎他的这份殊荣。那时关小月的儿子刚结婚没多久,家里一切貌似风调雨顺,正春风得意,就算被父亲挥了一拐杖,她没挨着倒也无所谓,也不惧父亲的恼怒,仍往父亲跟前凑,而且正色道:“续弦找老伴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您害哪门子羞?这咋能成不正经了?”父亲越发生气,抡着拐杖咆哮:“你们是我亲生的吗?我好歹也是正局级退休,非得把我推入那些蝇营狗苟的人堆里去,与那些心怀不轨的女人吵吵闹闹,分财产分房子,弄得我晚节不保!这算啥事儿?是我脸上写着要寻老伴,还是我生活太平静让你们难受?非让我折腾你们,才算是尽孝心吗?” 父亲气得嘴唇颤抖,握着拐杖的手摇晃个不停。 电视网络上老年人再婚后的种种荒唐事,每天不重样地播放,父亲头脑清醒着哩,他对人世百态、人情世故洞若观火,他才不屑进入那种俗套、纷乱的纠葛里,染指那些烦恼,让别人看他笑话的,他宁愿孤独终老。何况,他还有个正局级待遇的光环罩着,每月万把块钱的退休进项,医疗除种牙自费外,其他医药费全报销。父亲总有先见之明,走在时间前面,退休之前已将松动的三颗牙逐一种上,早已享受了他这个级别免费医疗的阳光雨露。退休后,父亲几乎没有后顾之忧,他才不想滑入普通人再婚的泥潭,沾两腿泥事小,惹一身骚,那就得不偿失喽。他以为自己的儿女怎么着也能明白他的心思,人至桑榆,能有寻常、平静的日子不就很好嘛!难道非要有人在跟前叽叽喳喳,才算生活得有情有调、有滋有味? 关小月姐弟俩当然不是非要父亲有个老伴才算安心,见父亲无意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也就不刻意为之了。 时间在父亲那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方法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延长,根本用不着其他人打断或者收起。哪怕是子女。可宋妮娜出现了。 关小阳第一次听到宋妮娜这个名字,还在半年前,关小月悄悄告诉他的,距离关小月给父亲物色对象那次还不到六个月。因为父亲发怒差点用拐杖打到关小月,所以她把那个日子记得很清楚,不时翻出来计算一下,倒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到她这个年龄,竟然还能让父亲挥起拐杖,想来也不知是该失笑还是难过。不管怎么说,她这也是为父亲操过心的,总不能为此记父亲的仇吧。 姐弟俩密谈宋妮娜时,关小月在心里计算着时间,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五个月零九天。话一出口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原来她把时间计算得这么精确,与突然冒出来的宋妮娜有什么关系呢?她有些不好意思,脱口而出的时间很能说明她对上次的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这就显得她肚量是小的。担心关小阳抢白,关小月想着怎么补救,或者假装刚才是灵光乍现,心虚地瞅了一眼弟弟。谁知关小阳一点都不惊讶,顺着她的话说:“姐,难道你上次的自作主张,激活爸爸的脑神经啦?他竟然用了五个多月的缓冲期。”关小月对弟弟话里的意思能理解,可她接受不了他语气上的不恭,那可是父亲啊,容不得调侃。关小阳不以为然,事实如此,还怕说呀。他差点脱口而出,父亲是明修栈道,却在暗度陈仓。明明之前他们姐弟俩巴心巴肺地想让父亲有个度桑榆晚的老伴,他却拒绝得气势如虹,结果呢?这才过去多久。关小月苦笑道:“管它多久,又能怎么样,还是商量怎么办吧。” 这事很难商量出结果,父亲的意思是表明出来了,说那么多回了——或者说暗示他们那么多回了,可他就是不明确说出真正的想法,难道是要把这个决定权给他们姐弟?可他们真的有这个决定权吗?五个月零九天前的那个教训,还明晃晃地挂在父亲的拐杖上——那道裂痕并没有影响父亲什么,可父亲有时无意识提起来的时候,姐弟俩总是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偶尔,关小阳还会背过脸偷着做鬼脸。吸取上次的教训,在父亲没有明确表态之前,姐弟俩谁也不敢直接问。但仅仅依赖于他们背后的揣测,又难免重蹈上一次的覆辙。关小月说:“我可不想被爸爸用拐杖再打一次了。”关小阳说:“我也不打算体验。” 那只能等了。 二 父亲的右腿关节半月板磨损由来已久,他还没退休时右腿关节疼痛,核磁共振作出的结论,打过不少医生推荐的进口“阿尔治”玻璃酸钠,却没得到任何改善,后来偶尔听其他病友说,吃葡立胶囊效果不错。父亲相信医生,咨询了几个医院的骨科专家,有的说可以吃,有的说不能吃,还有专家让他做手术换一个人工半月板。父亲选择了试吃葡立胶囊。三个月后,效果出来了,他的右腿关节不再那么疼痛,他坚持吃了半年,平时注意腿部保养,不爬山跑步,更不做剧烈运动,直到退休后几年,右腿关节病一直再没犯过。母亲患病去世后,父亲一个人在家独处着寂寞,他不愿与院子里的那帮老头打牌下棋,更不爱凑热闹扎堆说是非,便一个人去周边的公园小跑或者走动,他觉得这样的运动才是生命质量的体现,不是有那句听过无数回的话:“生命在于运动”吗?不管怎么说,运动总是没错的。当然,父亲的愿望很好,想法也没错,可惜他忘了还有个“物极必反”,无论他是走还是跑,都该有个度才对,父亲正是放宽了这个度,过多的运动量让他的右腿关节重新不适起来,时不时地疼那么一下,持续时间倒也不长,像开启的报警装置。因为有以前的成功经验,父亲没把右腿关节的警报当回事,疼得厉害时再吃药就是了,反正不用自费。只能说父亲太过轻敌,他不是从前的体质,强做蛮干唬不了病痛,倒把自己越练越伤。岁月饶过谁?葡立胶囊不是万能药,父亲断断续续地吃,右腿断断续续地疼,直到不再那么疼痛了,右腿却无力迈动,像是药物的反噬,最后走几步路得靠拐杖支撑。 关小阳从网上给父亲找了第一个保姆,来自安徽,有名的保姆省份,为此还拍过电影。这个保姆在京务工近二十年,现年四十七岁,主要是人长得憨厚老实。这是关小阳老婆顾玉兰给把的关,说这种长相缺乏色诱的先天条件,能很好地预防以色相骗取老爷子财产的可能。顾玉兰说得义正词严,关小阳听完没忍住“扑哧”笑了,以父亲极高的警惕性,他对色诱骗财的防范可比一般的老年人厉害,若不然,姐姐关小月又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挨那么虚空的一拐杖?顾玉兰严肃起来,看着关小阳说:“那可不一样,你别忘了‘日久生情’这个词,没有什么情感是时间改变不了的,你以为的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不由自主地成为可能。” 父亲再不是一株自生自长的植株,不能如常地行走制约了他的自如生活,他没理由拒绝儿子给他找的保姆。只是,这个保姆不像介绍的那样做了近二十年保姆的老手,似在工地上搬砖头的,她的举止很不自然,胳膊硬邦邦的,谦虚温和、曲意迎合一看就是装给包工头看的。这不是重点,用顾玉兰的话说,不管她逢迎给谁看,只要能把父亲照顾到位就行。这话说得没错,但到不到位得父亲说了算。父亲确实不挑人。关键是这个保姆的饭菜做得实在不敢恭维,和她的人一样粗手大脚,全靠各种酱料提色提味,口味极重。父亲说,以前跟母亲吃得清淡,后来他一个人又吃惯了简餐,难以下咽这些色素煨熟的大鱼大肉。 得,换一个吧。 第二个保姆是关小阳和老婆顾玉兰一起去家政公司现场挑选的。本来关小阳想叫上关小月一起去的,可姐姐的儿子那阵子正在闹婚外恋,她正焦头烂额想保住儿子的婚姻,一打电话关小阳还没开口,关小月就唉声叹气开始,连哭带骂地结尾,根本不给弟弟说话说事的机会。关小阳也感叹姐姐的命运,知道这会儿就算能把关小月拉扯上一起商量,她也是无心其他,索性不给她说了。关小阳只能与顾玉兰一起去把关。基本方针不能变,这是顾玉兰定的铁律,关小阳只能把目光对准那些年龄大点,长相普通——面善的女人。当然,也得问清来自何方,安徽的不敢找了,连带着只要是南方的都免谈——这次得把好厨艺关,北方人的口味大同小异,肯定能对上父亲的胃口。 这样的保姆在家政公司不难找,很快辞退了第一个保姆,第二个粉墨登场。第二个保姆的确是“粉墨”,她不光脸长得黑,手也黑,连眼圈也是黑的,可她除过皮肤黑,长得倒挺端正,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灵光人,关键她是河北张家口的,纯正的北方人。只是她太年轻,才三十出头。关小阳有些犹豫,觉得太年轻的保姆肯定不在顾玉兰的铁律范围之内,在他看来,最多能算个擦边球——她年轻却黑得彻底。顾玉兰却一眼相中,坚持要选这个,理由是——健康。回到家后,顾玉兰才告诉关小阳,年轻点腿脚灵便,不然整天这儿疼那儿疼,谁照顾谁呢,咱花钱可得值当不是?知道你担忧的是啥,可别忘了咱老爷子是啥人?正局级退休干部,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他绝不会让类似于非洲人的保姆,占了他老巢的。关小阳挺佩服老婆的,啥话她说出来都能自圆其说。 关小月来父亲家第一次看见这个保姆,竟然吓了一跳,以为是外国人,认真瞅了好几眼才辨出来。为掩饰自己的失态,赔着笑问她的姓名。确实没人告诉过保姆的姓名,一直说的都是保姆,最多也就说第二个保姆。她的牙其实不是太白,可让她的皮肤衬托出了白,笑起来牙显得真白,从那些白牙的空隙里飘出两个字:黑妹。连名字也是黑的。关小阳心想,这名字起得倒有自知之明。 黑妹的确腿脚灵便,她把父亲带到百湘居,见到了宋妮娜。 老爷子是能吃点辣的,黑妹更是无辣不欢,她展示的厨艺中,除了辣,别的味也尝不出来。这让关小阳有点怀疑,当时黑妹是不是隐瞒了什么,她其实更像是南方人。吃了半个月,老爷子的味蕾抗议了,像他这样一定级别出身的人,不会太直接,尤其是看到黑妹在厨房被辣椒呛得咳嗽不止,一边擦汗一边挥动铲子为他做饭的情景,老爷子也不忍心怪她。辞退就更不可能,一个月不到辞退两个保姆,就为了口腹之欲,那他成什么了?这么难伺候。还正局级,太官僚,太不知人间疾苦了。他不可能这么做,又不忍打击黑妹在厨房为他挥汗如雨的积极性,那只能婉转一点,慢慢来改造黑妹了。他提出来,偶尔去饭馆吃一顿,换个口味,也可以学学人家做菜的方法,是不是?黑妹很爽快,推着老爷子,不辞辛苦走了五六里地,进了她最喜欢的百湘居。 不用说,老爷子觉得来对了地方。猛然抬头看见宋妮娜,老爷子居然一反常态,有些激动,像遇着哪个大明星似的,眼神跟着移动。黑妹还以为他们认识,结果一问,谁也不认识谁。老爷子却抖索着嘴唇说,这个女娃跟老伴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他一看就打心眼里亲切。后来只要一说起百湘居里的宋妮娜,老爷子就感慨不已,将黑妹所做的饭菜质量置之脑后,她做成什么样,他都吃得津津有味,辣味都显得不那么辣了。只是,时不时地让黑妹推着他,去百湘居吃一顿,每次都要招呼宋妮娜来点菜。至于点的什么菜,吃的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见到了宋妮娜。从她身上,能看到老伴的影子,他们年轻时候的往事,就伴着宋妮娜不时出现的身影,闪现出来,那些近在眼前又遥远缥缈的往事,翻腾在老爷子的心里,让他眼眶湿润、热血沸腾。 说得多了,宋妮娜似乎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只是这一员是个虚幻的现实影像,她是被父亲逼进了姐弟俩的日常生活,却又随性自由,漠然地置身他们日常之外。 关小阳很郁闷,父亲这么积极地借助一个人来叙述母亲,到底是为了母亲还是被借助的那个人?父亲含糊不清的态度,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顾玉兰也专门去百湘园里看过那个宋妮娜,她不像关小阳姐弟俩那么傻,吃不了辣还要活受罪。她能吃辣,可这些年肠胃不好,不敢吃辣,她专门叫来宋妮娜给她服务,先点了杯花茶,然后仔仔细细地翻阅菜单,还让宋妮娜推荐一些跟辣无关的菜。宋妮娜开始还挺有耐心,推荐了好几个与辣不结缘的菜,却被顾玉兰瞬间毙掉,不是南方人,吃不了那么精细的菜,或者过于油腻,吃完会恶心。强行找些理由也是可以的,最终逼得宋妮娜不再开口。当然,顾玉兰一边翻着菜单,让宋妮娜推荐菜肴的时候,也以一个女人的眼光审视、打量着宋妮娜,她可不会顾此失彼,忘记她此番来的真正目的。 显然,顾玉兰与宋妮娜的见面很不愉快。碰到个进到饭馆只点一杯茶而最终以各种理由不点饭菜的人,哪个服务员能一直微笑到最后?宋妮娜肯定不能,脸越拉越长,到最后,几乎从顾玉兰手里夺过菜单,任怎么招呼,再不肯过来服务了。 这让顾玉兰的考察算不得成功,被饭馆的服务员给了脸色,她气不打一处来。所以,一回到家她就警告老公,宋妮娜可不是善茬,千万不能把她弄进老爷子家。 “谁说要把她弄进家了?”关小阳听着老婆的话就来气,“宋妮娜才二十多岁,比咱家揪揪大不了几岁,这是给咱爸找孙女呢,还是续弦?” 揪揪是他们的女儿,大四,正铆着劲准备考研呢。 这话让顾玉兰心里有些安慰,哈哈大笑道:“看来你没糊涂,就怕你闹下叫人笑掉大牙的蠢事。” 关小阳不再理会老婆,她心里想的是啥,他心里明镜似的。其实,他和老婆的想法一致,虽说他和关小月都主张给父亲找个老伴,但不如关小月那般心思纯粹,他想的是跟父亲年龄相当的,或者年龄差距不那么大的,更看重彼此相伴的生活,不至于有太多的弯弯绕。而过于年轻的女人,若没点盼头,人家凭啥找个能当父亲或爷爷的老头过日子?除了正局级待遇,父亲能让人惦记的就是他的那套房了。关小阳想的就是不能让外人把父亲的那套房卷走,那可是父母奋斗了一辈子才落下的,说什么也得给他们姐弟留个将来供奉父母牌位的地方不是? 可是,父亲那里怎么办?关小阳给姐姐打电话商量,关小月已经顾不上哭诉了,有气无力地说:“你是知道的,我这儿乱成了一团,如果是搬家或者清洗之类的体力活,你给我留着,我抽空去干。这种脑力活,就别指望我了,我理不顺呀。再顺的事情现在到我这里也会整成一团乱麻。”她叹了口气,像是纾解内心,又好像专程为叹给关小阳听。电话那头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关小阳知道姐姐把电话放下了,她的声音比刚才远了些,但依旧清晰,她抱起孩子时自顾自地埋怨着,还得“哦哦哦”地哄着哭闹的孩子。关小阳想着姐姐这会儿顾不上再跟他说话了,正要挂断电话,却听到关小月说,“小阳,有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既然今天你问到爸爸的事,我想还是说出来。不管咱爸现在到底有啥想法,我懒得问,也不去猜了,就一样,老爸的房子。房子是爸妈共同的,得有一半属于咱妈,不能她走了,就把她那一半给了别人,那咱妈在这世上就啥都没啦。” 大概是一边摇晃着怀里的孩子,关小月的声音带着颤,说完这些话,她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她的哭声比她孙子的要小,可比她孙子的哭声更叫关小阳揪心。更没想到的是,姐姐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由姐姐说出她的想法,他反而不知怎么去表达他的内心。能说什么呢?这会儿再说,倒像是姐弟俩早就开始预谋似的。他明白姐姐的家庭正处于兵荒马乱,她确实腾不出精力来理会更多。关小阳有点懊恼,自己不能帮到姐姐也就罢了,怎么还不断拿父亲的事来徒增她的烦恼呢?不知道怎么安慰姐姐,他只能沉默。 哭了一阵,关小月胸中的伤感释放出来一些,逐渐收起抽泣,平静了一会儿,她又说道:“小阳,姐刚才说的话,你不要多想,姐从没想过要那套房子,你也看到了我现在的情况,给这狼心狗肺的挣得再多,他照样给你心上捅刀子。姐都这个年纪了,什么都不图喽。只是,想起咱妈辛苦了一辈子,如果爸真的有啥不便跟咱们说的想法,那咱妈可真亏大了,生前她没享过几天福,这以后她的身后要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她就算白生咱姐弟俩了。” “姐啊,我明白,求你别说了,行吗?”关小阳既心疼又羞愧,姐姐大概是把他的沉默当成了对她的质疑。 在关小月那里讨不到办法,关小阳只能与老婆商量。他们时而愤怒,时而温和,争论了几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当然,双方都没想出既合情又合理的解决办法。 权宜之计就是拖。 三 以前,每到周末关小阳和姐姐都要上父亲家,陪父亲说说话、吃吃饭。现在,关小月脱不开身,十天半月也难得去一次。关小阳没借口不去看望父亲,像以往一样独自过去,又怕父亲扯来扯去又扯到宋妮娜,还是那些话,“咋看咋像***,看着就心里舒坦”“你们有时间也去看看,也跟人聊几句”“也是怪了,这辈子还能让我碰上两次***这样子的”……关小阳不知咋接父亲的话,直接说那个宋妮娜不像妈,那岂不是把父亲的念想一把扯掉掼到地上,他该是失落呢还是生气?反正,哪样负面的情绪他都不希望父亲有。不然,探探父亲口风,到底想让他们怎么办?可万一父亲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自己又该怎么办,是接还是拒? 关小阳越想头越大,左右都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也不是他一个人能承接下来做得了主的,他便叫上顾玉兰,让她一起去父亲家。有儿媳妇在,父亲只能把想法憋在心里。父亲没了想说的话,关小阳不敢随便说,顾玉兰也不想没话找话,一家人各自坐着,屋里倒安静得像没有人存在似的。 这时,黑妹从菜市场回来,带着一身秋天的清甜凉爽,将关家凝滞不动的气氛瞬间冲破了。一家人终于被惊醒了似的,围着黑妹采购回来的瓜果、菜蔬,展开了热烈的话题。顾玉兰拎起一串黑美人葡萄,问了价钱,啧啧夸赞黑妹的眼光,说这么新鲜诱人的葡萄,不赶紧洗了吃,实在对不住黑妹的有心之举,就往厨房去清洗葡萄。黑妹哪能让主家——尤其是把她选来的女主人,抢了她的活,她与顾玉兰在厨房拉扯时,客厅里的关家父子这才松弛了下来。关小阳给父亲茶杯里续上水,端起茶杯递给父亲说:“玉兰的眼光不错,这个黑妹算是选对了,人勤快,也懂事理。” 父亲抿口茶,没接儿子的话茬,却把茶杯重重地搁下,突然说道:“你姐家里闹成这样,简直不像话。你姐夫父子俩,没一个好东西,老的当个破科长整天喝得醉醺醺,家里的事一点不操心,一点担当精神都没有,算什么一家之长;小的更不是东西,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在外面胡搞,老婆刚生了儿子就闹离婚,应该告他重婚罪,判他小兔崽子坐几年牢,让他受点教训。” 关小阳赔着小心说:“爸,看您说的,壮壮是您亲外孙哪。” “我没这样的外孙。”父亲抓过拐杖,在地板上捣得惊天动地,关小阳担心有一丝裂缝的拐杖被捣折了。父亲痛心疾首地说,“丢人啊,你姐怎么养下这么个不肖儿子。连我这张老脸都没处搁。” 顾玉兰和黑妹听到动静赶紧跑到客厅。黑妹端着洗好的葡萄,顾玉兰挑了串晶亮的葡萄往老爷子手里塞:“爸,咱有事说事,您不能生气啊!” 黑妹赶紧拦住她:“顾姨顾姨,爷爷不能这样吃葡萄,他最近血糖过线了,我给他榨汁脱糖后再喝,您自己吃吧。” “哟,黑妹真是的,我们老爷子有福气喽。” “屁的福气,气都气死了。”父亲一点儿不顾及顾玉兰和黑妹讪讪的样子,把拐杖往墙根一丢,冲着关小阳发泄,“你别整天吊儿郎当的不管事,你姐这么大烂摊子不帮着收拾,让你姐靠谁去?我走不动了,就是能走,我从位子上退下来这么多年,你姐夫那个狗东西,还有壮壮,他们还能听我的?” “爸,他们也不会听我的呀。” “别给我找借口。”父亲喘着粗气说,“要是***活着,能让这两个狗东西欺负你姐?你看看你姐每次来这儿,那个疲惫样儿,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就跟没吃饭没睡觉似的。这阵子她来得少,电话打得勤,我也听得出来,她说话的声音都不对劲,有气无力的,那可不就是叫那爷俩给气得?唉,想到你姐,我难受得睡不着觉,当初***不同意你姐嫁给这狗东西,是我硬扛着促成的,看看我都煮下的什么醋呀。” 顾玉兰接过来说:“爸爸您别难受了,姐姐家的事怎么能怪您呢,一家都有一家的事,不是这事就是那事儿,哪有一直风平浪静的。您也不要责怪小阳,他也操心着姐姐呢,一直帮着姐姐跑前跑后,可壮壮那孩子像他爹一样,是啥来着?” “下三滥。”关小阳没打一点磕巴,脱口而出。 父亲抡起拐杖,差点打到关小阳的头:“就你损,我们家的人什么时候用上这种词儿了。” 黑妹赶紧凑过来,抓住拐杖说:“爷爷,您别生这么大气,伤身子。叔叔也是说漏了嘴。我算是看清楚了,咱家都是知情知理,清一色的文明人。” 顾玉兰给关小阳使个眼色,拉上黑妹要去准备午饭,黑妹轻轻地摇摇头,却对老爷子说:“爷爷,您要还觉得堵得慌,我推您出去,刚好叔叔阿姨来了,咱去百湘居换换口味?” 还是顾玉兰清醒,她抢过黑妹的手,抓紧了说:“听爸说,你做的饭菜比饭店的好吃,我还没尝过呢。走,我给你打下手。” 父亲的话提醒了关小阳,姐姐家的事处在最难缠时期,他本来的想法是,不瞎掺和,免得自寻烦恼,可经父亲这么一说,他如果再采取躲避,也是不担当,关小月是自己的亲姐姐,哪有亲人遇到困难不帮一把的道理。可怎么帮?从哪儿着手,关小阳没个头绪。与顾玉兰商量,她也无从下手,只丢下一句“你姐家的破事真是难缠”,就高高挂起了。只要不牵涉到她自己的利益受损,与她没关的,才懒得管呢。 四 天气逐渐转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比闪电还快,呜呜吼叫的北风使屋内的气温迅速下降,往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会提前供暖,今年却不见一点动静,网络上的各种猜测流言乱飞,却抵御不了寒冷。关小阳打电话,交代黑妹将空调打开,别让父亲挨冷受冻。黑妹说,爷爷不让开,说是冷点不怕啥,关键要遵守规则。 “这哪儿跟哪儿,开空调不就多花些电费,没那么多臭规矩。你只管开空调,电费由我出。这天儿冷了,他真要受了寒,生病了,费的力气更大,就不只是这点电费的事儿了。” 黑妹妹很为难:“我也是这样说的,可爷爷说,不是电费的事,是原则问题。我也不知道这跟原则有啥关系。不过咱还是别开空调,惹爷爷不高兴。您放心,晚上我偷偷插着电热器呢,爷爷冻不着。” 这个黑妹是选对了,关小阳能省下不少心。可省下来的心,在姐姐家全用上都不够。他给姐夫打电话约他谈谈,人家说哪有时间啊,整天给人服务,不是请吃就是吃请,安排满满当当;他再给壮壮打电话,这外甥一点面子都不给,根本不接听,打的次数多了,壮壮能在一秒钟内摁掉。关小阳被摁得憋气,却不能把这对父子的态度告诉姐姐,凭空给她多添一份堵,只能开导姐姐。劝说了一大堆,道理谁都懂,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谁的罪,谁受。 这天,父亲打电话,要关小阳去趟医院,黑妹病了,需要人陪。关小阳苦笑,心想他什么时候成一块砖了,哪里需要哪里搬。正想找理由推托,父亲怒了,高声叫道:“我要能走动,还会叫你去?赶紧的,黑妹一大早就去医院排队挂号了。”关小阳本来还想问一下黑妹生了啥病,能自己去医院,看来不需要人陪。怕父亲生气又跟他喊叫,不敢再怠慢,请上假开车赶到父亲交代的电力医院。早晨看病的人真多,地库门口排起长队,他给黑妹打电话,问清楚楼层。待他把车慢慢挪进地库停好,找到黑妹所在的妇产科,她已在手术室门口引颈张望无数回了。关小阳救星一般出现,黑妹扒着手术室门框,兴奋地叫起来:“来了来了!”没顾上与关小阳说句完整话,被等得不耐烦的麻醉师扯进手术室。一个护士把关小阳带到一边,让他在几页纸上签字。 “这是什么?” “手术风险评估书。” “手术?”关小阳心里紧张了,难怪父亲一定要让他来陪着,“她得做手术?” 护士懒得回答,指了指签字的地方。关小阳仔细看上面的字,每条都与死和后遗症有关,他握着纸的手有些抖,不敢下笔。他想看清楚是什么手术,可最关键的内容是手写的,蚂蚁爪子似的,根本不认识。他问护士,黑妹做什么手术? “你能不知道?”护士语气很硬,“自己做下的事,装什么糊涂。” 关小阳一脸茫然。护士冲他翻了翻白眼,不耐烦地扔下两个字:“堕胎!” 这两字击中了关小阳的命门,他顿时喘不过气来。天呐!这是什么事啊?他张大嘴深吸了几口气,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拿着护士递过来的笔,他的手抖动得厉害,他双手相握,假装搓手以控制手的颤抖。什么都别说了,在护士的催促下,他只能签上自己的名字。只要这名字签下去,世上就不会多出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突如其来的打击,关小阳知道自己脸色很难看,心里更是堵得慌。手术后,他把黑妹送到父亲楼下,他不想跟着一起上去。他怕见到父亲。怕父亲易暴怒却每每显得很坦然的神情。忽然间他想到,父亲有阵子没提宋妮娜了,那个在父亲眼中长得像妈妈的服务员,是父亲心血来潮,还是黑妹许久没推他去百湘居了?他想不透。回到单位,他谎称加班,回不了家。他怕见顾玉兰。她要是从他身上嗅出异样,他该怎么回答?实话实说,她会闹得天翻地覆。编谎言骗她,能骗到什么时候? 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实在难以入睡,关小阳早已关掉了空调,他体内的烈火足以使他燃烧,再冷的天气他也抵御得了。几次,他都拨出了姐姐的手机号,即将接通的那一刻,他又摁掉。姐姐够烦了,不能再给她添烦了。关小阳把一切都装在心底,在办公室住了两天,内心的波涛终于不再那么汹涌,才强作笑颜地回家。好在,顾玉兰的观察力没上线,压根儿没看出他心里的一团乱麻。 这个周末,关小阳硬着头皮去了父亲家。一切都风平浪静,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父亲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发上看谍战剧,对儿子的到来不冷不热。黑妹的脸苍白了一些,身子弱的缘故吧,可她热情不减,给他迅速倒了杯茶,张嘴急于想说些什么,被他用手势强行制止了。他很想听父亲说点什么,可父亲对谍战剧的专注程度远甚于他。 好吧,既然父亲不想说,他更无话可说。关小阳只能选择走了。父亲竟然劝他吃过午饭再走,他冷冰冰地说:“饱了——早上吃多了。”后半句是他临时改变口风加上去的,对于老人不能太过残忍。事有事在,语气再冲也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加深相互之间的仇视。黑妹追上来送他,列出一大堆中午要吃的菜名,关小阳听着喉咙里都有灼疼感,胃里冒起一股酸水,但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你做得太辣,我吃不了。”黑妹说:“爷爷喜欢吃,我以为你也喜欢哩。” 关小阳回头看了眼父亲,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父亲,留下一脸蒙傻的黑妹,走了。 得不到任何解释的愤慨,冲击着关小阳的大脑。他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又心如止水。想不通时,他越钻牛角尖,心里越发难受。他太想找个人诉说了,但这种事,除过姐姐,他能给谁说?如果装在他一个人心里,他会憋死的。 拨通姐姐的电话,正如父亲所说的,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带着疲惫,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发出音似的。关小阳听着关小月那边没有哭声,难得的清净,他觉得这个时间点选对了,赶紧切入正题。他没有把事情说得多么严重,就事论事,尽量叙述得心平气和,不想让姐姐揪心,认为后果有多么严重。他确实做到了。关小月除了略微的诧异外,情绪的变化没他想象的那么大,至少她的语气里听不出愤怒,更没有痛心疾首。她似乎对此事不感兴趣,抑或是她再不能承受新事件的纠缠,很快将话题转移,扯到壮壮离婚的财产分割上。这回,壮壮的损失可大了,因为是他的错,不光是失去一套房子那么简单,可能还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女方现在坚持要孩子,孩子还在哺乳期,到判的时候,法律会偏向弱者。 关小阳能给姐姐说什么?他说损失这么大那就别离婚了,谁听得进去?壮壮连他的电话都懒得接,就是不想听他没用的陈词滥调。他只能说言不由衷的话,糊弄姐姐,也糊弄自己。 是谁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能想到,过去半个多月了,关小月不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竟然给父亲打电话,质问黑妹打胎的事儿。 这时候,关小阳的心绪似逐渐退潮的海水,还有波澜,却掀不起大风大浪了。却接到黑妹告诉他父亲突发疾病的电话,他喉头发紧,竟无言以对。黑妹说,她已经打过120,只是不知爷爷犯的什么急病,她六神无主。关小阳这才反应过来,劝黑妹不要哭,也不要乱动爷爷,等120来了采取救治措施。 他顾不上请假,跑步到车库。刚把车开上路,黑妹来电话,让他不要去家里,120已接上爷爷正往第三医院赶,让他直接过去。第三医院在中关村附近,关小阳边掉头,边改写导航。 路上堵车在所难免,关小阳心急如焚却强迫自己冷静,毕竟父亲已上了120,采取急救措施了。等他赶到第三医院,父亲已进急诊室救治,黑妹在门外乱转,见关小阳来了,眼泪夺眶而出:“医生说爷爷是心阻塞,不知会怎样?” 关小阳左冲右突,想找个医护人员问一下父亲的状况,可他们个个冷若冰霜,连听他一个字都不耐烦。黑妹拉住他说:“别问了,他们也不知道。”她把他拉到边上,免得被乱闯的人撞着。她扯住他的胳膊,才说:“小月阿姨是怎么了?她问爷爷我打胎的事,爷爷当时气得大呼小叫。叔叔,爷爷给你说过了呀,我被同乡骗了,来爷爷家之前就怀上了。爷爷为了我,如果他有个……”黑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关小阳把黑妹搂进怀里,拍着她的背安抚。得知关小月还不知道父亲的情况,他给姐姐打电话,简单说了下情况,没提一句父亲的病因。他让姐姐快往医院赶,却给黑妹说自己有个紧急事得离开一会儿。在黑妹疑惑的目光中,关小阳跑下楼,开车来到百湘居。 正是午后的空闲时光,百湘居里空无一人,服务员大多躲在包间里休息。关小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躲在卫生间玩手机的厨师,问他宋妮娜在哪儿。 厨师说,宋妮娜上个月就辞职不干了,至于去了哪儿,谁知道呢?人家去了什么地方可不会搁他这儿打招呼。不过,厨师把宋妮娜的手机号给了关小阳。顾不得多想,关小阳立即拨打宋妮娜的手机,里面传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